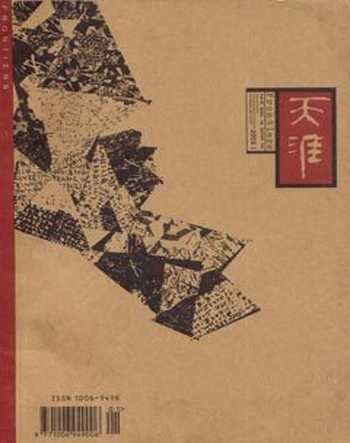对一只羊的怀念
我小学毕业那年,“文革”尚未结束。由于家庭出身方面有些障碍,父亲拿不准我是否还能继续读书,便从集上给我买回来一只羊,让我一边放羊一边等学校的入学通知。如果等不来通知,那么放羊就是我成为正式劳力之前的职业了。
其实我对读书并无好感,读书让我感到一种被束缚的烦闷;再说读书的意义也不大,读多少书,到头来总免不了种地。因此,当父亲把那只羊牵进家来的时候,我立即就喜欢上了它。
它是一只刚刚成年的羊,仪态优雅,遍体洁白。不过在十二岁的我看来,它似乎羸弱了些,就像曾经遭受过虐待似的;它还有些拘谨和羞涩,它躲在父亲身后,以戒备的眼神儿打量着我。看着它瘦骨伶仃、风尘仆仆而又忐忑不安的样子,除了兴奋之外,我对它还有了一点儿同情。
我执着于自己的同情,做了能够做的一切:几乎是死乞白赖地央求父亲把羊的栖息地由露天改在装粮食的厢房里,并在每天晚饭前把这块栖息地弄得干爽,母亲安排的打扫院子的任务反而常常被耽搁了,为此母亲可没少数落和训斥我;给羊洗嘴巴和蹄子——当然这得悄悄地干,在人的生计都难以维持的乡村,这种行为一旦暴露,必被视为病态的和不可理喻的;把拴羊的绳索留得尽可能地长,以给羊最大的活动空间。连我自己都意识到对羊的照料是如此精心,我从未如此热情、如此负责任地干过其它任何一件事情,我好像突然患上了一种狂热综合症,所有的行为都带上了过度谨慎和敏感的色彩,比如说,我从未强硬地拽过羊的绳索,我担心绳索会勒疼羊纤细的脖子,当希望羊有所动作的时候,我总是拍拍它的脊背。
然而问题恰恰就出在我的同情上。我的同情是以无知为前提的,我不明白刚刚成年的羊都是那样一副奇崛精干的样子,即使到最强壮的时候,它们的骨骼仍然鲜明突出,它们永远都不会像猪那样满身囊膪。我缺乏这样的基本常识,我断定我的羊是饥饿的,并且营养不良。我无知而又自信,结果是滥用了自己的同情——如果说上面提到的种种做法对于羊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话,那么我在羊的饮食问题上表现出的同情就是十分荒唐和愚蠢的了,我“推己及羊”、“强羊所难”,使羊真正地遭受了虐待。
那时候,生活中充满了匮乏和贫瘠,我不免时常感到饥饿。饥饿带来的痛苦可以算得上一个少年最大的痛苦了。我以为羊跟人并无区别,也有永远难以满足的欲望。我总是担心它吃不饱,担心它和我一样遭受饥饿带来的痛苦,于是我每天都带它去野外青草最茂密、树叶最鲜嫩的地方,直到它吃得肚皮滚瓜溜圆才让它回家。同时我还要弄回满满一篮子青草和树叶,作为它夜间的加餐。我留心观察和捕捉它在厢房里的动静,只要它不是老老实实地待着,而是弄出一些声响,或者有所动作,我都会认为它发出了要求进食的信号,我的回应就是迅速把青草或树叶送到它嘴边。记得一天夜里风雨大作,准备睡觉的时候又听到了它的嘶叫,我立即跳下炕,顶着风雨冲进黑暗的厢房,摸索盛青草和树叶篮子的时候,突然一道闪电照亮了厢房,我在惶恐中看见了羊惊悚的样子,我感到它是多么地孤苦无依,而我又是来得多么及时,我必须帮助它,为它做点儿什么,我抓过篮子,把青草和树叶全部倒在了它面前。就像吃能让我忘掉所有的不愉快一样,我相信,吃也能让羊获得最大的安宁和满足。我十分放心地离开了厢房。
我总是怀着愉快的心情看羊咀嚼。羊咀嚼的样子简直就是一个绅士,快而灵活,但不露出牙齿,也不像猪和一些人那样巴唧嘴,制造一种令人讨厌的声响。只要它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我就会感到如释重负般的轻松,这时我才会有兴致欣赏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细密羊毛,有时禁不住伸出手去抚摸它,偶尔我会感到羊轻微地抖动一下,但它不会避开,它只是抬起头注视我几秒钟,像在询问什么似的,随后又咀嚼起来,看它着迷和坦然的样子,我以为它已经得到了满意的答案。我继续抚摸,粗而光滑、略有些硬和凉的羊毛,使我的手掌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清爽。我以为羊是快乐的,它会因为充足的饮食而快乐,就像我也是快乐的一样。
然而羊吃得太多了。它不停地咀嚼,它那尚未发育健全的肠胃受到了伤害,使它来不及领略世间美味便逐渐失去了对于食物的兴趣,它的体型没有丰腴起来,也许它真的变成羸弱的了。但我丝毫没有觉察,仍然沉浸于同情之中不能自拔,认为它也像家境贫寒的我一样从来没有吃饱过。在我的照料下,羊每天都腆着大肚子从野外归来,有时候它不得不叉开两条后腿走路。可怜的羊,它得了消化不良症。
我的同情成了羊的负担。事实上羊并不需要同情,它是卑微的,也是清高的,它谦逊地活着,需要的只是少量的青草、树叶,和一碗干净的水而已。这些,就足以能使它活得很好,使它长得健壮。它不像人那样贪得无厌,有各种各样的要求。但我的羊不会长得健壮了,因为我像对待人一样对待它,我不知道,人与羊,根本就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啊。
假如我早一些从同情中醒悟的话,应该能够从羊的眼神和嘶叫中辨别出婉拒的意思。我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似乎受到了某种蛊惑,被自己的同情遮蔽了双眼,以至于等到羊变得烦躁起来,并经常发出一些奇怪的声响时,仍然把它们看作羊要求进食的信号,继续给羊盛宴般的款待。倒霉的羊,它真的是在劫难逃了。
羊渐渐地表现出厌倦、疲惫和沮丧,它的咀嚼也变得艰难而缓慢了,有时候它干脆对着青草和树叶发起呆来;对于我,它也恢复了刚刚见面时那种拘谨和戒备的神情,每天当我靠近它准备带它到野外觅食的时候,它总是惊惶失措地往后退去,使劲儿地挣脱着绳索,我看见绳索深深地勒进它的脖子里;走在路上,它也不像以前那样喜欢靠在我身边、蹭着我的身子了,而是无精打采地跟在我的身后。直到有一天,羊的嘶叫变成了呜咽和哀鸣,我才注意到它的眼睛里满是恐惧和绝望,它死死地盯着地面,一副遭受了奇耻大辱的样子。我猛地惊觉,进而发现它全身的骨头都已经支楞起来,尤其是肩胛骨,高而尖利地隆起,简直就像两把锥子,加上它不停地颤抖,看上去它们仿佛随时会从皮肤里面穿出来似的。相比之下,羊那个鼓胀的肚子就更清楚地显现出病态了。总而言之,它已经如此地衰老而丑陋,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父亲从村里的兽医那儿弄来一些药给羊灌了下去。此后羊一连在厢房里趴了几天,除了间或喝点儿水外,它已经吃不下任何东西了。它像死去一样趴着,偶尔发出一声呻吟,这种呻吟萦绕在我耳边,使我感到生命正在逝去的恐惧和悲伤,我痛悔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几天之后,羊的肚子不那么鼓胀了,它开始动弹身子,甚至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我感到它也许还有救,便试探着把一束青草送到它嘴边,我以为它应该吃一点儿了,然而它却十分淡漠地闭上了眼睛。
羊慢慢地恢复了一些生机。但直到离开我家之前,它再也没有恢复到我刚见它时的样子。它每天只吃很少的一点儿,神情总是倦怠而忧郁,经常在燠热的天气之下打着寒颤,有时候它大半天地趴在青草丛中昏昏欲睡,或者呆立在一排野槐树前,头深深地垂下去,像一个被命运打垮了的人似的。总而言之,在经历了一场使它元气大伤的灾难之后,它的生存欲望和意志都被严重地削弱了。
我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造成的错误像一块坚硬的巨石似的无法改变。也许它还在扩大和恶化。我只能寄希望于奇迹出现了。然而,这个世界平庸无奈,奇迹永远也不会出现,我一整天一整天地带着羊待在野外,我期望它能够得到更多阳光的温暖,并且能够多吃一些。但羊恢复得极其缓慢。有时候我几乎都要绝望了。在那个漫长的夏季,所有的生命都在热烈地生长,连知了、蛐蛐儿也不甘示弱地起劲儿叫着,只有我的羊,身心俱疲,形销骨立,仿佛进入了生命的冬季。
八月底,我突然接到了学校发来的入学通知书。父亲看完通知书后当即决定把羊卖掉。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带着羊赶集去了。我目送着羊出门,可怜的羊,已是如此地麻木和茫然,对于再一次的命运转折毫无觉察,它只是在跨过门槛之后,呻吟般地嘶叫了几声,低低的几声,然而听上去它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我甚至感到它连自己的嗓子都撕裂了。
许多年之后,我才能理解羊这几声嘶叫里包含的凄凉和悲伤。它心怀敬畏来到这个世界,谦卑、荏弱,然而无论它是怎样地委曲求全、与人为善,它总不能摆脱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命运。我无数次回想起它,一只无辜的羊,真正称得上安分守己,与世无争,然而它过不了人这一关。人往往自以为高贵,自以为秉持了最高的智慧和灵性,但当人将这种智慧和灵性肆无忌惮地布施于天下的时候,却往往使其它生命遭受到粗暴的践踏和褫夺。
赵军泰,职员,现居济南,曾发表散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