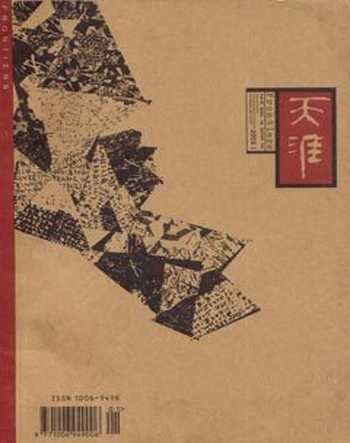沿途札记(散文)
夜里我听见有声音在我耳畔说:“聋哑的人啊,你说话吧;”过一会儿,又说:“盲瞽者啊,你不想开眼一见么?”
我惊得汗出来。我披被坐着,迎候天明的时间到来。
夜里手和手指尖一挨,信息就通了。
握紧着不要撒手,亲人啊,失散得真是太久了。
遇合在暗中,将凭本有的机秘。
午后,我在屋后的院子里盘腿坐着,阳光把院子里落满了,冬春之交的树影淡泻在地,枝柯清晰中显一些迷离。这是一个好时刻。我即使闭住眼睛,所见的黑暗也不深。
我听到在游走中断续的风声,听到一片枯叶的声响,听到山坡上乌鸦的鸣声,还有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羊叫声。
一切声音似乎都与这断续的风有关,一会儿风把它们轻轻遮住,一会儿风把它们悄悄显露。
我心泰和,一再想到神这个名字。
闭口藏舌。我更愿意从宗教的角度去知解这几个字。而且似乎愈是在深夜之际,我愈能领会其中寓藏的奥义。
暗诵着这几个字,连舌头也不动,我觉得我就像捧一罐真金的人,在博深的暗夜里,凭借微弱的星光,悄悄寻找着一个可以把它埋起来的地方。
是一对残疾的夫妻从路上走过来,聋哑的丈夫搀着看不见的妻子。
我们就躲到墙后面去,等他们走过后才出来。
他指着他们的背影说:“你怜悯他们了么?”
我没有说话。
他说:“其实他们比我们带有更多的使命,可惜他们和我们都忽略了。”
我们向他求教让一粒行将死灭的火星复燃的办法。
他说,拿一粒快要燃成败烬的炭来举例子吧,第一要迅速清除它周围的灰烬,第二要准备一些饱含生机的易燃的炭粒在它周围,切忌炭粒过大,将它压灭——它正值微弱,本来就是想死的,另外将炭粒围拢在它的四周时,不可挤靠太近,使它难于承受,也不可稍有间隔,使它们无法互传凉热,第三不能使之闭塞,要迅速通风。总之非常时期,这是一件需要十分小心的事情,最好让有经验者和谨慎者来做吧。
末后他又说:“我只是将我知道的说与你们,一定还有我所不知的方法。
骑马的人对牵马的人说,累了么?累了我们歇歇。
却从不会说你也上马来坐坐的话。
但仅是那样的一句问话,也足以让牵马的人连声说不累了。他果然更为大步地走了起来。
到最后,马都累了,牵马的人犹提出不需要休息的要求。
骑马者要找的,正是这样的牵马者。
我们常说“怕处有鬼。”
为什么不说“敬处有神?”
他说:“孤独就是呼吸和啜饮。”
我们让他说明白些。
他说:“人只在孤独的时候,才能一闻自己的呼吸。”
我们说,这有什么意思呢?
他说,你们以为无意思就无意思吧。但贤者说:“你们要看守你们的呼吸并凭着你们的呼吸做参想呢。”
我们说,讲讲“啜饮”吧。
他说:“人群聚时容易忘形,因此会大吃大嚼,孤独时一般不会这样,比如一瓶酒或一杯茶,一个人坐着、想着、品着,总是要在很长时间里才能把它喝完。”
我们说,这有什么意思呢?
他说,你们以为无意思就无意思吧。
一条海里的鱼和一条河里的鱼都被猎获到一只小篮子里了。刚开始两个都不说话,后来也就说起来了。
河里的鱼说:“你在海里也没有躲过么?”
海里的鱼说:“虽然你我同被猎获了,但还是有不一样之处,你是他们无意撞上的,我是他们辛辛苦苦寻到的。”
河里的鱼想了想海的博大和深奥,就有些相信同难者的话了。
它说:“我要在海里就躲得让他们找也找不见,到处是逃生之路,到处是藏身之处啊。”
海里的鱼没有说话。它觉得自己的话要比河里的鱼少许多才对。
河里的鱼说:“可怜我们都要死了,不过荣幸的是我还可以跟您死在一起。”
海里的鱼忍不住说:“也许你我的死将会相同,然而生却完全是不一样的,真有见识者只比较生,不比较死。”
河里的鱼便不知道说什么,它轻轻叹一口气。篮子里那么小,它尽量缩紧着自己,多容一点地方给海里的鱼。
一会儿它们就被拎到厨房里,刀子刮起它们的鳞片来,鳞片纷溅着。海里的鱼拼命扭了一下身子,它讨厌那条鱼的鳞片溅到自己身上来。
为了让同难者内心多一点镇静,河里的鱼大睁双眼,紧咬牙关,忍受剧痛,一声不吭。
又一轮大火后,我们开始清除灰烬。
他说,因为临近着,我就给你讲讲灰烬,过后又忘了。
于是说:
大火知道如若燃下去必成为灰烬,但还是尽情地燃烧到最后;
火的燃烧,其目的不是为了得到灰烬;
灰烬是火的穷途,却非新生,人无法把希望投在灰烬里面,因此之故,火便烧出种种形式来;
灰烬是火之死;
是火的一种反思形式。
我愿望火只能暖我的双手就可以了,像从壶里倒出的清茶一样安宁和长远,但我的火容易骤现,更易暴躁,很快就将我焚为灰烬。
我恨我的火,并不是因为使我提前成了灰烬。
我抱定一棵大树,然后将目光透过高远的树冠祈祷说:“主啊,我所见的人都张皇失措,焦头烂额,换一样人生给我们吧。”
“主啊,人们在地上仓皇行走,每个人都背着一口黑锅,换一样人生给我们吧。”
树冠掉出几片树叶,很久了才落到地上,我捡起看,没有看出比树叶更多的东西。
此外也就没有任何声音。
我死的时候,要把我一生穿过的衣服都拿出来,尽数排开,从我刚落生时裹我的那片布到我死后同我入墓的那片布,都依序排开,一件也不遗漏。
比一比,我们谁穿的衣服多了;
比一比,我们谁的一生只穿了很少的几件;
从这些衣裳就比出难辛来了;
从这些衣裳就比出虚妄来了。
送我入土的人啊,一个人的一生都在这里了,我已解脱,请勿惊挠,如若你们愿意,就对着我脱下的这一大片难辛和虚妄哭一场吧。
我再次来时,守门的人却不认识我了。
“我来过的。”我小心且诚恳地说。
他细细将我端详,但还是摇头了。
我就说:“我还记得你的,上次来时,也是你在这里,对我点头,然后引我进去。”我说得小心而诚恳,来到这里时,我总是不打诳语。
他就神秘地笑一笑。
“那么你下一次再来吧,或许你再来,我就认出你了。”他和气地说。
夜里我不敢挪去井口的石块,地太深了。
夜里我可以看天之高,却不敢看地之深。
夜真是黑,我们像落在井里,一起步便四面碰壁。
我们就惶悚地站住。
求告说:“我们是跟着天上的星斗走呢还是跟着地上提灯笼的人走呢?”
我们的两只耳朵没有一只听到回答。
我们就暂且跟提灯笼的人走着。
老实人向聪明人问路,聪明人随手指了一个相反的方向。
但是老实人却顺此走到了一个令聪明人十分意外和震惊的地方。
他对往来的人宣谕说:“他走到那里,全凭着我的一指。”
他看我的舌,摸我的前额,说:“是什么病呢,竟把一个年青人弄成了这样?”
我说:“就是心里慌,不得安宁,其余倒没什么。”
他又给我细细把脉,两只腕子都把了。
我说:“可以看看么?可以看看的话就看看,我倒是很想吃药的,食物太无味了,还老耽误我。”
他用两只大耳朵静听我说话,接着沉思,接着说:“比这更重的病我都可以医的,但这病太轻微了,倒使我无可措手。”
我早就料到了。便不为难他,放他一径走了。
石舒清,作家,现居银川。主要著作有小说集《苦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