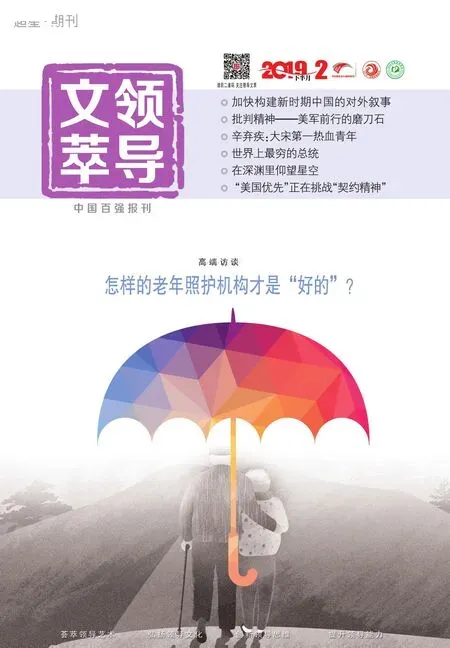“官场另类”的意义
邓 科
去年上半年以来,媒体对吕日周的关注几乎没有间断过。这是因为他和一般的官员太不一样。
他把市房管局副局长开会时打瞌睡的照片登在了报纸上;他把几千名市直机关的干部赶到农村去挨冻;他把市委常委会的内容向全市公开;他逼着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到广场与群众对话;他在报纸上点名批评分管教育的副市长;他把警告黄旗挂在了分管卫生的副市长办公室;他把市委市政府的大门拆掉,让这个地方对百姓不再设防;他引来了叫好声,也引来了攻击他的大字报。
有人说:"长治这么多年,新来一个市委书记,一般是自己去适应大家,吕日周则相反,他老想让大家来适应自己。"吕日周在长治三年,归结起来就是在做一件事:试图改变官场的一些规则,改变官员的一些习惯。
客观地说,吕日周是官场的"另类"。这一点,引来了颇多的争议,也引来了普遍的关注。
有人这样说:诚然,吕日周的所作所为大多暗合了人们对官员的某种期望。关注他,显示了媒体和社会的某种价值取向。但想一想,在目前的现实条件下,吕日周这样的官员有多少?难道经过媒体报道后,就会有官员主动向他学习,多出几个这样的官员?吕日周现象就目前来看是不可复制、缺乏推广的土壤的,不具有普遍意义。他是官场的"另类"、是"个别",媒体对他的关注只是迎合社会的某种期望罢了,对现实没什么改变。
按照这种说法,难道对吕日周的关注现实意义真的很有限?问题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吕日周异于官场常规的做法目前确实难以推广,他试图改变既有规则的努力也遇到了重重阻力,但正是通过他这一连串的经历,官场运行规则最真实的一面才展现在我们面前。
就像灾难才能检验出一个民族的性格,绝境才能展现出一个人的价值一样,很多东西在异于寻常的条件下、在强烈的刺激下才能充分显露出来。
吕日周的"另类"举动就像一根针,他把官场中的疼痛和问题都刺了出来。他的经历,他的处境,他和旧规则的冲突和交锋,他改革能进行到哪一步,他最后的归宿是什么,都像一面镜子,清晰地折射出了官场的现实。
吕日周就像一块试金石,他的命运可以让我们对改革的环境和官场的现实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因此关注吕日周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关注来关注我们的改革环境,关注改革可能达到的程度,关注改革的阻力和障碍在哪里。
实际上,吕日周从原平改革到长治试验的19年经历就充分反映了改革环境和官场规则的一些变化。
在长治的几年,尽管有流言蜚语,有大字报匿名信,有同级官员的不理解,但在吕日周看来,这与原平改革时遇到的阻力相比,只能算是"小菜-碟"。
1983年开始的原平改革给吕日周带来了极大的声誉。《新星》中的改革者形象---"李向南",吕日周即是原型之一。而全国各地20多个省市6万余人拥向原平参观,更是一时成为一个壮观的景象。
但是随后他改革的方向和措施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引来了对他前后6次长达500多天的调查。有一次在查了100多天后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便给他盖了顶"官瘾很大"的帽子---"上面查你100多天,你每天还坚持工作,也不病倒,这不是官瘾大么?"
在80年代改革起步时,山西的保守思想还比较严重,而对吕日周改革持保留态度的也包括省里的一些领导。
相比之下,在长治的几年,吕日周没遭受什么大规模的调查,公开站出来反对改革的也极少。"毕竟经过十几年,改革已形成了氛围。"吕日周说。
事实上,目前的政策空间也大了很多,用吕日周的话说:"没有自己的东西,只不过是扎扎实实地落实了中央的精神。比如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缓解干群矛盾、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要发展民营经济等等,都是中央提出来了的。"
现在对吕日周的攻击不太可能指向改革方向和改革措施了,与十几年前相似的是,也有人给他扣了顶"官瘾很大"的帽子,说他骑自行车下基层是"作秀"、"谋求政治资本","这些行为明显是为了升迁"。
对此,吕日周的说法是:"那你们也一年骑自行车1000多里啊,也早晨6点去上党课啊。"
一位山西省人大前主要领导也对记者表示:"如果我们的官员都搞这样的'形式',那就是件好事。"
对于"官场"中的所谓游戏规则,吕日周感到的是无奈和愤慨:"就因为你与他们一些人不同,你没有遵守某些实际规则,你就被称为'异类',被称为'有争议',而在现实中,有争议往往就是一种否定。'太平官'什么事都不干,反而往往能够升迁,这岂非咄咄怪事?"
从原平改革的公开受阻到长治试验的反对暗流,我们看到了时代的一些进步,更看到了依然存在的痼疾。正因为这些痼疾的存在,所以不少人在了解了吕日周的情况后都会问:他的改革到底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