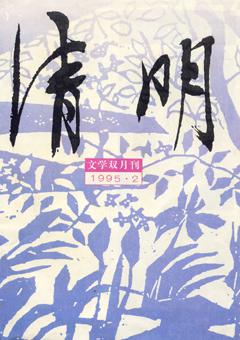狐
毛 强
在与我专业上的启蒙老师金一老先生相处的日子里,我最喜欢听他说“过去的事情”。他,一位年过八旬的老翁,最喜欢的是回忆,每当他一开口提起“俺那当小孩的时候……”我便忙不迭地将自己的座椅移得离他更近些,坐定后,便盯紧他一张一合的嘴。
在他讲的许多故事中,我记住了这个与狐有关的故事。
金一老师讲述的速度很慢,边讲,边迟疑地在记忆里搜寻着什么。像是夏日里晒衣的妇人从箱笼深处寻出了旧时的嫁衣,一边叹着,一边将衣上的锦绣指给旁人看。口气里,有怀旧的热情,对往日辉煌的炫耀,也有对时光流逝的感叹。老人迟缓、凝重的语调似拍打在锦衣上的巴掌,随着拍打声的起落,我似能嗅到这堆锦绣丛散发的丝丝尘屑与陈年的薰香。
二、三十年代的生活,在老人的叙述中,总是那样和美,怡人。那时的C城,不似这般吵闹、脏乱,也没有这样多的人。小城有石板路,小店铺,草屋,瓦房,小院,木格,窗;城四周,有高高的城墙,城门楼;城内有城隍庙大戏台,夫子庙、武道庙;热闹的日子是正月的灯节,二月的庙会,四月里的赛驴。城不大,人不多,抬头不见低头见,叙来叙去都串成了亲戚。那时,城里的人家极少有钟表,每入夜便能听到报更人的梆声。天麻亮,城墙内外的大公鸡此起彼伏地啼叫,需要早起的人们不会因没有钟表的指点而误事。更早起采的,有卖豆浆、油条、糖糕、包子、大饼、油馍的小生意人。大户人家,自有自家的厨子,买点小吃,只为尝个新鲜;穿长衫的读书人,挑担子的生意人,买起小吃来,总有几份豪气,一买许多.用油纸托着,边走边吃;有那等带孩子的妇人或自己拿几个小钱的孩童,数着手中的一个个铜板,仔细地挑拣着小吃摊上的货色……
一天的生活便由此开始了。
这C城城西的一隅,有一处颇有模样的宅子,宅院的大门两旁,端坐着两尊怒目圆睁的石狮子——一看便是户殷实人家,这家的一位小姐,便是金老先生当年的新娘,既然是岳丈家,金先生自然常前往探视走动,久之,对岳丈家上下人等。便熟稔了。
看院门的是位亲戚,岳文的表弟,金先生便唤他为表叔了。北人因度日艰难,自乡下来投在表兄门下,表兄略一沉吟,便将表弟留下来看院门。表叔是位鳏夫,一生相伴的只有一件爱物——一支箫。这箫被抚摸成了暗褐色,并发着幽幽的光。白日,箫套在一青色的洋布套中,静静躺在表叔居室内的枕边。忙完了一天,每日晚饭后,表叔并不掌灯,摸黑进屋,便将箫从枕边的套中取出,摩挲一番,便倚此盘腿坐于床上,开始吹箫。
现在的年青人很少听到箫声了,他们更热衷于摇滚,打击乐和电声乐器,对于传统乐器西洋的知道有钢琴。小提琴、小号等,对于民乐,除却二胡笛子,其它便不甚了然了。
说到此,金一老师转而问我“听过箫吗?”我轻点点头,我曾在收音机里听过箫声。虽不清楚吹的是什么曲子,而那恍如隔世的声音却使我难忘。我想:箫的发现者,定是一个幽怨的女人。这女人又必有几分书卷气,箫声给人的联想,是月光下激滟的湖波,远远的山廓,在纸窗上轻轻摇颤的竹影;一点点滴入古井中的泉。那箫声.在静夜里听去,像一个痴情怨女的魂魄,飘飘忽忽,在月色朦胧的人问寻觅着什么……。
宅子里及周围的人家,渐渐习惯了这每夜必有的箫声。听着这箫声,在油灯下低头作女红的妇人会停下手,静静地听一阵,出会子神,轻轻叹一下。重又埋下头去;挑灯夜读的书生,会掩卷静坐,盛起身踱步推窗,望一阵屋外的夜;宅子里,堂屋的麻将桌上,老爷夫人们的嘻嘻哈哈,掩去了这阵阵箫声,偶而静下来,听得一两声,也会笑骂一句:“这老头子,想啥呢?”
老人闭着眼,在黑暗中倚枕吹着,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一年又一年……
有这么一个雪夜,老人依旧模黑进屋,上了床,将被卷扯散盖住腿,将手揣在袖里焐一焐,又放在唇边哈哈气,搓一搓,便掏出套中的箫,上下摩挲一番,将箫置于唇边。
箫声飘然而出,涤去了窗外寒风中的肃杀之气,和着悠悠的雪花,在空中旋着;风,又把箫声传至更远……
不知过了多久,周围人家的灯,相继熄了,寒夜里,远远传来了一两声狗吠。
老人吹着,似乎要永远这样吹下去。
两行清泪,无声地滑过了苍老的脸,晶亮亮地挂在嘴角边。
入夜,有梆声敲过。
原本插了的门,“吱口丑”响了一下,闪了条缝,似有什么东西无声地窜了进来,并带进了冬夜的寒气。
老人没有觉察,依然吹着。
那小小的、毛茸茸冰凉凉软塌塌的小东西灵活地窜到床上,傲在老人身旁卧着,不一会又爬上了老人的肩。
老人睁开了眼,肩上的小东西,竟温柔地将一只毛茸茸的小蹄搭在老人的颈上,伸出暖暖的小舌,添去了老人腮上的泪。
老人一惊,箫声住了。那小东西迷迷地从老人肩上窜下,半蹲在床上,与老人对视着。黑暗中,老人辨不出是什么,可他感觉到那小东西也在看他,直接的反应,是拿起枕向它砸去,那小东西出溜一窜出了门,老人追至门口,只见晶莹的雪地上,有一串小小的蹄印。
“那是狐哇!”第二天.表叔向宅子里的人讲述着这雪夜里的造访者。
宅子里的人为之惊动了。妇人们窃窃地低语声,更使此事显得神秘。有来访的老爷的朋友们,也兴致盎然地打听着这只狐:
“没有看见别的啥嘛?”
穿着锦缎马褂,胸前挂着金灿灿表链的老爷们总如此一问,又总叹息着结束了自己的发问。他们最感遗憾的是没见狐女、鬼魅类的显形。看厌了家里的妻妾,总希望有什么奇女子出现。此时,那怕再荒诞不经的故事,对于他们,也是一种感官上的满足。
对于这等发问者,表叔以沉默对之。而在与金一先生对饮时,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感慨了,他颤声说:“这小畜牲,它是冲我的箫来的,它能听懂啊!”
金一老师长叹一声,打住了自己的故事。
微风拂过金家小院,竹摇,花颤,草动,大花猫“嗖”一下窜上了屋顶。
“没啦?!”我傻傻地问,感到故事结束的太突兀。
“这世上……这世上有多少小东西,都有灵气,这狐是最有灵性的……这小狗小猫喂好了,都才贴心哟。”金一老自顾自地说。
我呆呆地坐着.痴想着那只小狐,想着那位长夜吹箫的老人。
一个尖尖脸,毛茸茸的小生灵,在冰天雪地的夜,艰难地趙趄前行着,找寻着牵动了它心扉的乐声。
一个一生以箫为伴的老人,用这夜夜箫声倾诉了他生活中的多少艰辛和心中的悲琢,道出了多少他对人,生的真情!
然而可叹,老人一生吹箫,最终面对的。竟只是一个无语的知音。
从那以后我懂了:这世上的二一切。不仅仅属于人。
责任编辑孙民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