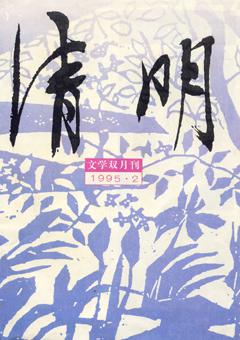独自一人
范小天
l
马天然闭了一下眼睛,眼睛里有一些又干又酸的感觉,没有眼泪,甚至没有一丁点儿湿润。他把眼睛转向窗外,想寻找一些绿色。
让人感到透不过气来的铅色天空下,是布满了灰尘的高高矮矮的屋顶。法国梧桐干枯的枝丫从矮小平房的间隙中挤出来,顺着摩天高楼间的窄缝,向上仰望,似乎想从铅灰色的天空中寻见一丝温暖的阳光。
阳光是没有的,灯光却是三三两两地忽闪起来。
绿色自然也是不会有了。
马天然咧咧嘴,苦笑一下,收回了目光。
稿件上的字已经看不清了。其实,看得清和看不清,对他马天然来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当然,这事儿只有他马天然自己心里有数。
编辑部的人是每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来转转,十一点钟多一些就回家。回家看稿。当然,细心一点的人,很容易发现,从来没有人会傻乎乎地真把稿件带回家去看。大部分的编辑,能在某个值班的节假日,一天处理完三五个月里累积下来的一千万字或者两千万字或者更多字数的稿件。
马天然是整个编辑部唯一显得异常古怪的人。
马天然的审稿能力,从表面上看,和他的具有现代庞统才能的同僚们相比,可谓相去甚远。
马天然每天上午比同僚们来得还要晚些。中午,和同僚们一起下班。当然,稍稍不同的是,他只是装出一种回家的样子,然后在附近的一家个体户摊上吃碗牛肉拉面,就回编辑部来看稿件。一看一个下午,不到天黑不回家。
马天然从来不希望别人了解或者理解自己的行踪和思想。
在马天然看来,人如果能够理解别人,那么人和畜生不是就能区分开来了么?
在过去的一些岁月里,每当有人提出诸如“理解万岁”、“××精神”以及“奉献一片爱心”之类的口号,马天然就觉得好笑。马天然知道,每当人类提倡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他们发现这类东西最匮乏最欠缺的时候。马天然觉得好笑的是,人类想把自己的某种观点强加给别人的时候,恰恰会忽视最最基本的问题。比如说人类不可能真正具有的某种品质,比如说人类不可能真正具有的某种能力,马天然有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在他看来,在古代历史上,最最怕死的皇帝就最最喜欢听人家喊“万岁”、祝“万寿无疆”,而把生命的有限性有意无意地放在了视觉的盲点上。
这是人类的悲哀。
当然,人类的悲哀远远不止这些。
马天然在下午开始独自上班后,几乎隔三差五的就有人拿着不知用什么手法搞来的钥匙,偷偷打开隔壁主编室的门,打直拨长途。
有的是给出差的老婆汇报家务,有的是交流各种型号的钢材或者水泥的各地差价;当然了,也有打本埠电话的,比如一下午给三五个或者更多的女性打“温情”电话;比如和某个出版社的某位编辑商量倒卖书号以及利润分成的问题……
每当这个时候,马天然真是如坐针毡。他想咳嗽一下,提醒别人隔墙有耳,可又不敢咳嗽,怕人家说他心理阴暗有窥私癖好。
后来,也不知道该从哪一天算起,下午就再也没人来打电话了。
上午主编室没人的时候,马天然悄悄地溜进去过几回,试试是不是电话坏了。
电话照例健康。
有那么一段日子,马天然像是偷了什么东西,惶惶不可终日。
同事们的脸上却没有什么恼怒或者鄙夷,只是人们对他的称呼。由似乎很亲切的很熟稔的“天然”,恢复为很尊敬很客气的“马天然同志”。
马天然自然知道人在隐秘泄露以后的心态。在马天然的记忆里,他念大学的时候,每当他的一位好朋友把自己内心的痛苦的隐秘告诉他,寻求他的帮助之后,好朋友就会渐渐地离他远去。
可是到了年底,省级机关评劳模的时候,马天然意外地发现自己居然榜上有名。
这莫非是应了人眼是秤那句古话?
马天然突然又觉得好笑,他知道自己每天下午坐在编辑部里,从来没有看过一篇稿件。他只是呆呆地盯着稿件,想一些遥远的旧事。在马天然的记忆里,他呆呆地盯着那红榜,看了很长时间自己的名字之后,又疑疑惑惑地看了很久别人的名字。他不知道别的劳模是不是和他如出一辙。
马天然合起自己眼前摊开的稿件,咧咧嘴苦笑了一下。
2
马天然下了楼,在昏昏的暮色中寻找自己的那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
玻璃橱窗前空落落的,没有一辆自行车。人行道上停车线内也已没了任何车子。
在马天然的记忆里,他是把车子停在玻璃橱窗前的,早晨天就铅色得厉害,像是有雨雪的样子。他的车子——遭雨淋,就像个长满疥疮的乞丐,浑身上下淌黄水。
顺着玻璃橱窗向上数六层,好歹有尺把宽的一线屋檐可以挡挡雨。
当然,玻璃橱窗的主人总是不太愿意。自行车就经常列队转移到人行道上的灰白色的停车线内。
一旦遇上雨雪天,那些变速跑车、山地车的主人们就怒不可遏地冲着玻璃橱窗里嚷嚷起来:
“搞得不得了了,搞到我们头上来了!”
“我这车子八百多块钱买的!”
“要求经济赔偿!”
“搞搞清楚,这地方到底是哪个的?!”
橱窗里的人不以为然地抱起胳膊:
“是要搞搞清楚,这地方到底是哪个的!”
“你们这破房子的房租价格都涨到三万块钱一年了!”
“把我们的生意搞掉了,还不晓得哪个赔哪个呢!”
在马天然的记忆里,有一次他的自行车链条咔咔咔咔咔咔卖在转不起来了,他扶着自行车,站在人堆里嘀咕了一声:
“我这车子实在不能遭雨淋了么!”
橱窗里的人看看马天然,又看看马天然的车,噗哧一声笑了,说:
“啊呀,怎么瘸腿驴子也赶进城来了?!”
橱窗里橱窗外的人都跟着笑了起来,不知为什么,人的气也跟着消了。
在马天然的记忆里,橱窗里的人后来还说了一些有趣的话:你的车子我们保证不往雨里推;扶贫救灾是我们每个公民的神圣义务……
每说一句,都能换来一阵欢乐的笑声。
可是这会儿,他的瘸腿驴子自己跑到哪里去了么?
橱窗里腰包粗肥的老板们总不至于像小人一样言而无信吧?
马天然目光犹豫地转向了橱窗。
3
橱窗里有个姑娘正甜甜地冲着马天然这个方向笑。
马天然没想到这么晚了,身边还会有别的男人和他一样站在橱窗前犯呆。他有点儿羡慕又有点儿嫉妒地朝自己的左边看看,左边没有人,又往右边看看,右边没有人,他又转过身朝自己身后看看,身后也没有人。
马天然这就又一次疑疑惑惑地向橱窗里看去。
那个姑娘还是甜甜地冲着他这个方向笑。
马天然很久没有见到别人这么友好和甜美地冲着自己笑了,一种久违了的温情和感动涌上了他的心头。
马天然充满了感激地向着那姑娘努力地笑了笑。
橱窗里的姑娘依然那么甜甜地笑着,没
有说话,没有招手,只是似乎有了一些羞涩的样子。
马天然在橱窗玻璃的反光中看见一张布满了孤独悲哀苍老衰迈的网纹的梧桐枯叶悬在玻璃橱窗里的某个空间。他又一次努力地笑了笑,那枯叶上就添了一些凄凉。
漂亮姑娘怎么可能冲这么一张凄凉的枯叶甜甜地笑呢?
马天然再一次回头看看自己的左右和身后,他的左右和身后照旧空落落的没有人影。
莫非这个姑娘曾经认识他马天然?
马天然疑疑惑惑地走进商店,弯一弯身子,冲那姑娘笑笑。
噗哧,马天然听见了姑娘喷出的笑声,但那姑娘脸上的笑容却没有一丝的变化。
马天然继续努力地冲那姑娘笑笑。当然,这时候他终于发现,那是一个穿着丝绸时装的假可乱真的塑料模特。
“可我明明听见她笑的。”马天然满腹狐疑地嘀咕了一句。
噗哧,又有了姑娘的笑声。
马天然这才发现,站着的塑料模特旁边。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坐在一张小方凳上。
“哦。”马天然尴尬地笑了笑,说,“我还以为假人也会说话呢。”
“假人当然会说话啦。”小姑娘指指柜台上的一个花枝招展的翘起一条腿的洋娃娃,抿嘴一笑,说,“你看好啊。”
小姑娘拍了一下手。
那洋娃娃突然身子一震,边唱歌,边跳起舞来。
洋娃娃唱的是叶倩文演唱的香港歌曲《潇洒走一回》:
天地悠悠,
过客匆匆,
潮起又潮落,
恩恩怨怨,
生死白头,
几人能看透,
……
洋娃娃旁边有几只鸡蛋,伴随着跳舞女孩的歌声,摇晃着身子,叽呀叽呀地欢叫起来。
“买一个吧,叔叔。”小姑娘仰脸望着马天然,说:“多好玩呀,保证你玩得开心。”
像是从很遥远很遥远的天边飘来了一片轻柔的云彩,这一声“叔叔”,让马天然觉得心里有一些阔别已久的温情在悄悄地涌动,他摸了摸口袋里刚发的二百五十块钱薪水,笑了笑,问:“几块钱一个?”
小姑娘一愣,但很快就转过神来了,说:“不贵不贵,一点儿也不贵,我们只卖五十五块钱一个。”
马天然吓了一跳,他没想到现在连玩具都这么贵了,在他的记忆里,七八年前,他给女儿买玩具,一两块钱的就算很贵的了。
“叔叔,这种声控玩具,南京就我们有,是进口的,上海都要卖到一百多块钱一个呢!您买一个吧,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哪个没有……”
马天然突然一阵揪心疼。他想起了自己那可爱的女儿,他不知道自己的女儿现在长成什么样了,也不知道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泪水顿时盈满了马天然干枯已久的眼睛。
“叔叔……我……”小姑娘脸上充满了同情和怜悯。
马天然觉得自己的心被这种孩子对大人的同情和怜悯揉碎了。他赶紧扭过了脸,往朦朦胧胧的夜色里看,他的手急忙地伸进口袋,掏出钱来递给小姑娘,说:“哦,哦,我买一个,买一个。”
“叔叔,您心里很、很苦罢……我看见您的脸,就想起那些让人心里难过的歌。那些歌星唱的时候,都假得很,装成很痛苦的样子,可是,可是我一看见你的脸,就觉得你的心里面很孤独很悲伤的……”
“哦,不不,不不不,”马天然不知怎么,突然就觉得这小姑娘似乎就是他幻想中的女儿,当然了,未来的女儿,很多年以后的女儿,或许会像她这么好罢,他于是轻轻地问了一声,“哦,小姑娘,你姓什么呀?”
小姑娘愣了一下,看看马天然的脸,才轻声地说;“姓龙。”说着,又看了看马天然的脸,说:“叔叔,你还没吃饭吧,我哥哥就在隔壁红灯酒家当经理,他心肠特别好,你跟他说说话,心情肯定会好一点的,哦,我介绍你去,可以八折优惠的。”
马天然觉得,有一只温柔的小手,轻轻地抚着他破碎的心,热泪又一次涌满了他的眼睛,他有点儿哽咽地说:“小姑娘,你真好。”
4
红灯酒店里几乎没有客人。
马天然温存而感激的眼光,依依不舍地望着那小姑娘跚跚离去的纤弱的背影,背影终于消失在酒店门口了。
马天然叹息了一声,找了暗角处的一张小方桌,坐了下来。
“要点什么?”小姑娘的哥哥弯下身子,十分和气地问。他的身材颀长,面容清秀而白晰。显然是个下海经商的翩翩书生。
马天然看了一会菜谱,要了一碟凉拌西红柿,一碟海蜇,一盘炒鸡丁,一盘鱼香肉丝。
菜端上来的时候,马天然习惯地用筷子指指热腾腾的菜盘,习惯地抬头看了看小方桌的对面。
小方桌对面空落落的,没有人影。
马天然尴尬地咧了咧嘴。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她看起来只比刚刚离去的小姑娘大一点儿。还不到十八岁罢。苗条纤弱的身子,甜甜的天真的笑。她居然会爱上他,他当然非常喜欢她,却没有敢想过爱。那似乎是十分荒唐的事。那原本就是一个荒唐的年代留下的荒唐景况,他几乎可以做她的叔叔,他插队时教过的学生都比她大,他如今却和她在一个教室里念书。他第一次吻她的时候,她还不懂得接吻,他当然也不会接吻,他和她二起从心底深处发出了快意的笑声。十八岁的纯洁的她,三十二岁的纯洁的他,那是一个珍视纯洁的年代。
“嗳,你怎么不吃呀?不对胃口?”小姑娘的哥哥问。
“哦,对、对胃口,这是她最喜欢的几个菜。”马天然说着,慌慌忙忙地挟了一筷子菜塞进了嘴里。
噗哧,她一看见他吃菜的样子,就抿嘴笑。
那是插队时饿出来的穷相和馋相。
她知道他吃过很多很多苦,她经常眼泪汪汪地听他说他的过去。
那时候,要是我在你身边就好了。
这一生,不管你去哪里,不管你的命运怎样,我都永远永远在你身边。
她说这些的时候,总是泪流满面。
每当这时候,他觉得他的心都要碎了,他于是紧紧抱住她.疯狂地吻她,吻得她发出幸福的呻吟。
他喜欢听幸福的欢乐的声音,沉重的苦难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相信中国人民绝对不会允许再出一个“四人帮”了。
可是,可是,社会前进了,人却不知怎么变得都像不认识了……
马天然叹了口气,这就有了想喝酒的念头,他看看坐在柜台前的小姑娘的哥哥,说:“哦,请;请问,我该,该怎么称呼您……
“哦,我姓龚,是这里的经理,当然了,你叫我小龚就行了。”小姑娘的哥哥很亲切地笑了笑,说。
“小龚?”马天然疑惑地看了看他的脸,说:“可是你妹妹怎么姓龙呀?”
“我妹妹?我有妹妹?”小龚经珲笑了起来。
“你不用瞒我了,”马天然笑了笑说,“就是刚才带我来这里的小姑娘呀,她已经告诉我了。”
“哦,对对,”小龚经理阅透了世事似的笑了笑,说:“其实姓这个玩艺儿,又不能换钱,文不能换官帽,有什么用呢?所以姓什么都没
关系,是么?哈哈哈……”
马天然疑惑地看看小龚经理,脑子里就有点乱了,难道人的姓氏,也可以像人的脸一样,为了钱,为了要做官,为了嫉妒,为了其他种种种种,可以说变就变的?马天然的心里就又涌起了要喝酒的欲望,他看了看小姑娘的哥哥——或许是小龚经理或许是小龙经理——的书生气很浓的白晰清秀的脸,笑了笑,说;“小龚……小龙……经理,真不好意思,请给我来点酒,好吗。”
“好,您喝什么酒?”
马天然愣了愣,他真不知道该喝什么酒。
插队的时候,有一个冬天,要下河,喝过小半瓶土烧酒,后来把早晨吃的山芋糊全给吐得精光。
结婚的时候,喝的是红葡萄酒,大概有七八小杯,后来,就当着众人,搂着妻淌眼泪,从心底里淌出了感激的幸福的眼泪。
马天然这一生,就喝过两次酒,却两次都让别人笑痛了肚皮。
“什么,什么酒不容易醉?”马天然有点不好意思地问。
“啤酒。”
“哦,我,我要二两吧。”
“白酒?”
“啤酒。”
“啤酒最少买一罐。”
“哦,就买一罐。多少钱?”
“您放心喝,我这里是全市最便宜的,那丫——”小龙或者小龚经理稍稍停了一下,古怪地笑了笑,说,“哦,只要是我妹妹介绍来的,还可以享受八折优惠。”
“哦。”马天然活了这四十多年,还不知道啤酒是个什么味道,看来自己离开这个世界太有一点儿久远了。他喝了一口苦涩的啤酒,抬起头想和小龚小龙经理说些什么,小龚小龙经理已经回到柜台前去了。
红灯酒店弥漫着红色的光雾。
这是喜庆时的光雾,婚礼时的红色光雾。妻和女儿走了以后,马天然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通宵了,眼睁睁地望着天花上白炽的日光灯,任痛苦肆意地咬啮他孤寂的心灵。后来,他把屋里的灯全换成了红色的。这就有了婚礼和蜜月时的许许多多幸福温馨的梦幻一般的回忆……
当然,梦幻毕竟是延续不了多少时间的。
马天然轻轻地叹息了一声,把目光转向了桌上的跳舞女孩。
或许这个跳舞女孩会给他孤寂无侣的生活带来一些活的气息?
5
马天然头痛得像是有十几个或者几十个脑科医生.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各自为政地给他的头颅开刀。那是遥远了又遥远的感觉了,当老师的爸爸妈妈,不知道被自称为毛主席的红卫兵的人关到哪里去了,他独自一人到了农村,那是初冬,气温也不算太低,风却像刀子一样钻进衣服里面,人冷得发抖,后来就头痛,痛得浑身冒冷汗,痛得浑身抽筋,当然。最后,痛得不醒人事了……
马天然费力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身子趴着他们编辑部楼下的玻璃橱窗。脑子里又疼痛又晕乎,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天色早就暗下来了,昏黄的灯光朦胧而迷离,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
马天然疑惑地抬起头来看看,这就隐隐约约地看见玻璃橱窗里站着一个女人,女人两眼深情地凝望着他,羞涩地微笑着。
马天然也努力地礼貌地朝她笑了笑。在马天然的记忆里,他的笑容尚未消失的时候,就已经想起橱窗里是一个身穿丝绸时装的塑料模特儿了。他于是又费力地支起身子,往模特儿身边的小方凳上看,他记得那地方坐着一个纯真无瑕的或许姓龙或许姓龚的小姑娘。
橱窗里的灯早就关了,方凳上也已空落落的没有任何人影。
显然是早已过了下班的时间了,马天然看了看手表,表上的时针.还停留在七点上.那是他走进红灯酒店的时间,他轻轻地叹了口气。
在马天然的记忆里,就是这个时候,他意外地看见那个可爱的小姑娘从橱窗里向他走来……
“你,你在等,等我么,我没,没事,没,没关系,能回去的……”马天然努力地站直了身子,挥了挥手说。
小姑娘没有吭声,一边用她的两只温情无比的眼睛,默默地看着他,一边继续向他走来,渐渐地近了,他又意外地发现小姑娘这时候戴着一只硕大的白口罩。
“你,你,天气还不至于这么冷啊。”马天然有点儿纳闷地说。
小姑娘还是没吭声,不知道为什么,她走到了玻璃里的那个有着梧桐枯叶一般凄凉的灰黄脸色的马天然身边,身子微微地倚着他,和他一起看着橱窗外的马天然。
“我真,真羡慕你……”马天然痴痴地对橱窗玻璃里的马天然说。
橱窗里的马天然嘴巴动了动,从口型上看,似乎也说了这么一句。
马天然疑惑地扭头看看,他这就惊愕地张大了嘴巴。
戴着大口罩的纯真无瑕的小姑娘,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下子就已经从玻璃里走了出来,站在他马天然的身边,她那披着黑亮长发的脑袋,微微地斜倚在他马天然的肩头。
“你,你怎么能从,从玻璃橱窗里走出来的呢?你知道,我,我过去是不相信特异功能的。”马天然惊愕地说。
小姑娘的眼睛笑了,笑得非常美丽动人,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马天然觉得,小姑娘美丽动人眼睛里,也有着隐隐约约的凄凉和哀伤。
当然,马天然这时候已经明白,她显然不是先前的那位小姑娘。
姑娘大约已有二十多岁了,黑色油亮的长发如瀑布般披在肩上,她的眼睛漂亮得让马天然不敢正视。
马天然疑惑她是认错人了,他尴尬地笑笑,说:“我,我,你,你,怕是认错人了……”
姑娘的眼睛甜甜地笑了,说:“我找的就是你呀。”
姑娘的声音揉碎了马天然的心,这瞬间,他忽然想伸手把姑娘紧紧搂在怀里,或者把自己的头深深地埋进姑娘怀里。当然,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倒不是怕姑娘突然扯开嗓子尖利地发出强奸啦抢劫啦什么呼救声,他只是觉得,他不能在一个姑娘喝多了酒时,或者深陷在失恋的痛苦中,趁虚而入。
马天然轻轻地晃了晃姑娘的肩,说:“姑娘,你知道,我想告诉你,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
姑娘目光迷离地看看马天然说:“不认识,是啊,是不认识,可是,你想想,你在这个世界上认识谁么?”
马天然很惊讶地看了姑娘一眼,他没想到这位美丽的姑娘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在马天然的记忆里,他过去认识的人,常常因了升迁发财什么的,突然就不认识他了,这不足为怪;让他弄不明白的是,他自己常常觉得认识一个人已经认识了很多很多年后,不知怎么,突然就会觉得又不认识那个人了。他为此去查过许许多多的字典,字典上千篇一律地说:认识:一、能够确定某一人或事物是这个人或事物而不是别的;二、经过观察、概括、分析、判断、推理等步骤在人的意识里反映客观现实。在马天然的意识里,如果用认识的第二层意思来理解,那么凭他马天然的智力,是无法弄清楚人的真正的客观现实是怎么一回事的,换一句通俗易懂的话来说,也就是,他马天然真是一个人都不认识的,一个人都不可能认识的。
他苦笑了一下,说:“我,我也,也是觉得,我,我是一个人也不认识的……可是,可是,
别人因此就说我,说我的脑子有毛病……”
姑娘凄婉地笑了笑,说:“我也一样,他们也说我有毛病,我们……同病相怜罢……”
6
马天然开门的时候,屋里的风铃就先先后后地响起来了:
风凛凛……
风凛凛……
“你也是挂了很多很多风铃么?”姑娘柔声地问。
“是啊,几乎所有过风的地方。我都挂上了,还有许许多多的风车啦,飞鸟啦……门窗开关能够牵动的不倒翁啦圣诞老人啦……你知道,我是独自一人……哦,我想起来了,我今天还买了一个跳舞女孩,你一拍手,她就会唱起歌跳起舞……”
“哦,我也想买过的……二十多块钱一个呢……”姑娘说。
“不,五十五块钱一个的,一拍手就会跳舞唱歌的那种玩具,你知道那是什么原因么?那是声控玩具……我拿给你看……”
“别开灯——”姑娘突然很惊慌地说。
马天然愣一愣,但他很快就理解了,笑一笑说:“好的。”然后,关上门,又拧上了保险,摸着黑,从包里拿出他的声控玩具,一一摆在桌上,然后拍了一下手,跳舞女孩就在黑暗中微微一笑,在那几只鸡蛋叽呀叽呀的伴唱声中,欢乐地跳起舞来。
红尘呀滚滚,
痴痴呀情深,
聚散终有时,
留一半清醒,
留一半醉,
至少梦里有你追随。
……
7
姑娘这就依偎到了马天然的胸前,她的硕大的口罩已经摘下。她的脸轻轻贴在了马天然的脸上,她的柔软的嘴,贴住了马天然干枯了许久许久的唇。
马天然悄悄地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了皮夹,皮夹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空了,只有两张薄薄的纸。他记得一张是买那个跳舞女孩时的发票。那另一张,显然就是吃饭的收据了。那剩下来的钱呢?马天然摸了摸其它的衣服口袋,没有钱,他又摸了摸裤兜,裤兜里也没钱,他这就有些糊涂了。在他的记忆里,今天是领了二百五十块钱工资的。
“你在干嘛呢?”姑娘在黑暗中仰起脸问。
“我,我想找钱……”马天然窘迫地说。
“这时候找钱干什么呢?”姑娘问。
马天然苦笑了一下,说:“给你呀……”
“我,我怎么会要你的钱呢?”姑娘惊讶地说。
马天然就真的惊愕了,他结结愣愣地问:“你,你不是那、那种人?”
“你怎么可以把我看成那样的人呢?”姑娘轻轻地有点儿幽怨地说。
“那那那你怎么可能看得上我、我这样人呢?”
“孤独呀——”姑娘从心底深处叹息了一声。
“我也孤独呀——”马天然紧紧地拥抱住了姑娘,亲吻着她的脸。
姑娘的脸和脖子上早已满是泪水了,或许是泪水罢。
8
“我该回去了。”姑娘依偎在马天然的胸前轻轻地说。
“你还会来么?”马天然紧紧地搂住了姑娘赤裸着的温香如玉的身子,唯恐她会像梦中的妻一样,眨眼间如白云一般悠悠地飘走。
“会来的,会来的,只要你让我来,你知道,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么幸福过了。真的,真的……我没想到你这么好,这么好……”姑娘轻轻地呜咽起来。
“我也是,这和你也是很有关系的,真的,真的呀……你出了好多汗罢,你身上好多地方,都出汗了,肩啦,背啦,腿啦,都出汗了……”马天然说。
“我,我,可能是太、太激动了……”姑娘结结巴巴地说。
“我也是很激动的,你知道,我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够这么好……”马天然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你知道,自从我独自一人后,人都喜欢探听我有没有女人,没有,你知道,没有,谁会喜欢像我这样的穷书生呢,人于是就都嘲笑我,笑我四十多岁了,还靠手淫熬日子,其实,你知道,我不会,不会手淫,真的不会,我过一段时间,睡觉时就会遗精的,像少年人一样,我知道那很滑稽,他们知道了,又会笑的,会笑痛肚皮的……”
“我不会笑你的,我会对你好的……一直,一直到……到我们死去,死去……”姑娘轻轻地呢喃着。
“你真的,真的会到死都这么,这么对我……好?我,我知道的,你对我好,你真的对我好,你知道,我真是好久好久没有这么幸福过了……”马天然的眼泪流了下来。
姑娘把马天然的头紧紧地搂在了自己柔软的胸口,让马天然像孩子一样衔住她的乳头。
马天然的泪水弄湿了姑娘的胸,他喃喃地说:“我,我只有一个要求,一个要求,你能答应我么,你答应我好么?”
姑娘又把自己的乳头移到了马天然的嘴里,柔声地说:“你说吧,我只要能做到的……”
“我,我想看看你。看看你的脸,看看你的美丽的身子……我保证不告诉任何人,保证不说出你是谁……”马天然这就伸手拉开了电灯的开关。
啊呀——
姑娘撕碎了肺腑地尖叫了一声,抓起床单,要包裹住自己完全赤裸的身子。
马天然在这短短的一瞬间,愣住了,他看见姑娘的脸上,脖子,胸乳之间,腰腿之间,布满了斑斑点点的暗红色和黄褐色的痂,有粘糊糊的脓液,从那斑斑点点的疮痂上渗出……
“红,红斑狼疮?是,是么……”
姑娘的眼睛里顿时噙满了泪,嘴里喃喃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9
跳舞女孩无缘无故地扭动身子,唱了起来:
我拿青春赌明天,
你用真情换此生,
岁月不知人间,
多少的悠伤,
何不潇洒走一回,
……
责任编辑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