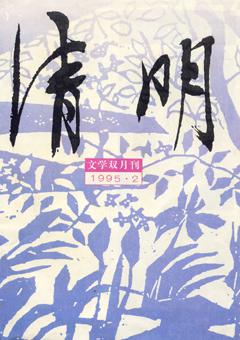这种事好像不由人
马 丁
巴宗与巴平在桥东一带非常出名。出名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巴宗与巴平是孪生兄弟。孪生兄弟属于先天因素,后天因素则是巴宗用形象缔造的。
长相一模一样的孪生兄弟,使人无法辨认哪个是巴宗哪个是巴平。在巴宗与巴平十四岁以前,他俩的父亲巴心武曾无数次把巴平认作巴宗,把巴宗当成巴平。真正没有出过差错的是他俩的母亲何秀珍。何秀珍为他俩歇了七年劳保,直到他俩背起相同颜色的书包,步入石岗实验小学。那段时间的何秀珍,眼角时常挂着白米粒似的眵目糊,头发干涩零乱,衣衫样式陈旧不整。在巴宗与巴平疯狂生长的岁月,何秀珍漂亮的容颜出现衰老的迹象。巴心武忧心忡忡地说,怎么就是双胞胎呢?晾晒尿布的何秀珍说,怨我吗?巴心武叹口气,怨就怨老天爷吧。
巴心武经常在黄昏时分牵拽着巴宗或巴平在大街上迢达。这幅亲情画面曾经是平正里大街最动人的风景。
巴师傅,领的是巴平还是巴宗?有人问。
巴心武端详着怀里这个前额宽阔饱满,眼睛漆黑明亮,一头细软的黑发呈卷发状的男孩,说,是操蛋鬼巴宗吧。巴心武说着踌躇满志地把巴宗举到头顶,然后又使劲往空中一抛,接住,又一抛。巴宗非常喜欢这种带点冒险的游戏。巴宗被抛起的一瞬间要咯咯疯笑。然而巴心武这回没有听见咯咯疯笑,却招来一阵惊天动地的哭嚎声。哭嚎声没断,又洒下一泡尿水。巴心武一面擦试着头上的尿水一面说,错了,错了,不是巴宗是巴平。
经常遇见好事者询问巴宗与巴平谁大?何秀珍一手抚摸着一个,娇柔无比地说,那时候疼得要死要活,不记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巴心武插话说,让巴宗当哥吧,巴宗厉害,厉害不受人欺!何秀珍斜睨着巴心武说,我喜欢安稳的巴平做哥哥。哥哥要有个哥哥样,你们说对吧?何秀珍最后一句是问那些好事者的。大人们只顾说话,忘了巴宗与巴平。巴宗吃完桔子,伸手去抢巴平的,巴平不给,巴宗就学大人吓唬小孩的模样去摸巴平的鸡鸡。巴平被吓哭了。听见哭声何秀珍弯腰打了巴宗一掌,没有惧怕感的巴宗翻着黑眼睛盯视着何秀珍又伸手摸了巴平的鸡鸡一下。何秀珍喝斥着又要打巴宗,巴宗突然两手抠着嘴哇哇哭叫起来。何秀珍脸色苍白地抱起巴宗问,你怎么啦?巴宗指着自个的嘴巴说,我把桔子籽咽进肚里啦!何秀珍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说,咽下去没关系,不要哭啦。巴宗用手按住肚子,蹲在地上说,桔子籽会在我肚里发芽的,会从我嘴里长出桔子树。他最后说,那时候我就不能吃饭了,我会被饿死的。大人们先是愣愣地听,后来就哈哈大笑起来。
这就是巴宗与巴平最初留给人们的印象。
操蛋鬼巴宗从来不叫巴平哥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巴平处处都表现出哥哥的姿态。譬如,吃水果时,巴平挑小的吃。譬如,有天早晨起床后,巴平发现自个的鞋穿在了巴宗的脚下,便说,穿错啦,我的鞋干净,你的鞋脏。巴宗笑着说,嫌脏就刷一刷。巴平真的就拎着巴宗脱下的又脏又臭的鞋出了屋。巴宗不喜欢逻辑思维严谨的数学,他喜欢美术与自然。巴宗的数学作业经常是照抄巴平的。巴平没有办法不让巴宗抄。
巴宗喜欢玩游戏机,他口袋只要有钱就掏给了游戏机。巴宗没钱又实在想玩就向巴平借,他拽住巴平肩上的书包带说,借我点钱!巴平扭头望着巴宗说,你上次借我的钱还没给我。巴宗粗暴地把巴平的书包扔在地上。他推搡着眼泪汪汪的巴平说,你喊什么?喊也没用,家里就咱俩。巴平极不情愿地掏出了钱。巴平跑出门框的阴影又走在明亮的阳光下。他站在阳光下愤怒地挥舞着拳头喊,你休想让我给你请假!巴宗在门框的阴影下做了个要追的动作。他说,不用你管,我有的是办法。
巴宗倚着他家院门口那根电线杆,双肘交叉在胸前,蜷起右腿蹬着身后的电线杆,两眼直视着蓝天。他经常以这种姿式出现在这儿。巴宗没有等着同年级的刘小英。他把手里那张伪造的病假条撕碎,然后走进街口的杂货店。开杂货店的老刘笑眯眯地说,巴子,买什么?巴宗摆摆手说,打电话。老刘从柜台下面搬出部公共收费电话。
请给我叫一下卢老师。巴宗模仿着巴心武的声音说。啊,卢老师,巴宗有点不舒服,让我给他请个假。那面听电话的卢老师怎么听怎么觉得不对劲,忍不住问,你是谁?巴宗最怕受到怀疑,一受到怀疑他的自信心就没了,他结结巴巴地说,是我爸给你打的电话。说完他就挂了电话。
老刘章灾乐祸地说,巴子,你暴露了,你不如让我充当你爸一下。
暴露我也不怕。巴宗说。
老刘堵在门口示意巴宗交电话费。巴宗无奈地掏出两块钱。老刘换零钱时,巴宗顺手把一块小圆镜装进了口袋。他走出杂货店后,摸出小圆镜对老刘晃了晃,老刘,你店里的日用品全是次品,明天你要把这面镜钱退给我,它的质量实在不好,照不见人影。怒容满面的老刘蹿出杂货店。巴宗一面后退一面用镜子的反光照老刘。企图做出强烈反应的老刘被迫停下追赶。他用手保护住眼睛,说,快还给我,要不我就告诉你爸。巴宗嬉笑着说,财迷的老刘,等我玩够了会还你的。
巴宗把口袋里的钱全部塞进游戏机的肚子里。他对牛气十足的老板说,借两个币。老板叼着香烟说,借可以,但要把钢笔押下。巴宗拍拍手说,今天没带书包。他从口袋掏出那面镜子,镜子值两个币的钱吧?老板拒绝了镜子。他说,给你一个币吧,什么也不用押。老板神情傲慢地让巴宗伸出手等待他的恩赐。巴宗气哼哼地走出了游戏机房。
巴宗在回家的路上幻想着自个开个游戏机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沉缅在幻想中的巴宗推开家门,发现卢老师坐在沙发上喝茶,巴平陪坐在另一个沙发上。巴宗怪叫一声把卢老师的喊声关在屋里。他跑出平正里大街,爬上了大石桥。大石桥是这座城市两个区的自然分界线。他站在桥上,透过树枝、屋顶遥望百米之外的平正里大街,猜测他爸会怎样对待他这次逃学事件。他还望见红彤彤的落日,希望它永远挂在天上,那样卢老师屁股坐疼了就该走了。落日彻底从视线消失后,他明白他爸他妈该回家了。他把手插进口袋,悲伤地望着西天最后一抹彩云。他后来掏出了那面小圆镜,并把它高高举起。巴宗幼稚的举动是想让手中的镜子充当不落的太阳。
那天何秀珍没有按时回家。她和同事们跳舞去了,晚上十点钟才进家。处于兴奋状态的何秀珍把小坤包扔进沙发,然后两只脚互相磕了一下,两只高跟鞋便从脚上飞走,一只向东一只向西,丑陋地躺在那儿。她穿着丝袜走在洁净的地板砖上感到非常舒心。她甩手搭在巴心武的脖子上,一面轻轻揉搓着巴心武粗壮的脖子一面柔情蜜意地问,怎么还不睡觉?何秀珍这个动作其实是他俩夫妻间一种性生活的暗示,但没有得到巴心武的反应。
我在等巴宗。巴心武说。
他这么晚不回来你怎么不找找他?
巴心武转了个身,桌上的台灯光映照在他的左脸颊,使他的脸呈现出几块不规侧的阴影。他说,我找他时你在哪里?
自知理亏的何秀珍脸颊绯红走进套间。躺着听收音机的巴平说,妈,我现在知道巴宗藏在什么地方。他一定在大石桥上。
何秀珍与巴平走向套间门口时,巴宗推开家门跨进了屋。怒火重新点燃了巴心武,他吼叫着扑向巴宗。对巴宗的痛打,何秀珍不予理睬。她一心一意地卸装,后来从梳妆镜里观察到巴心武下手非常狠。便生气地把梳头的大刷子摔在地上说,巴宗不就是晚回来一会儿,你为什么往死里打他?巴心武喘息说,你问问他,我这样打他是不是轻的?因跳舞晚回来的何秀珍却另有想法。她冲到巴心武面前.你要有气冲我撒吧!巴心武说,我真的不是冲你!巴宗被横陈在另一张沙发上,那被打成紫红色的屁股毫无廉耻地露在两个吵架人中间。他很快发现报复他爸的方式。他小心翼翼地把他爸两只脚上的鞋带系在了一起。他一想到他爸一起身被摔倒的情形禁不住要笑。他又想到他爸爬起来后该怎么对他呢?巴心武推了他一下,记住,别再找揍!巴宗突然说,别动!爸,你的鞋带开了,我给你系上。巴宗跪在地上解鞋带。
所有的一切被倚靠在套间门口的巴平看在眼里。他突然开口说,爸,你的鞋带没开,是巴宗把两只鞋上的鞋带系在一起,他想把你摔倒。巴心武疑惑地看一眼跪在地上的巴宗,又扭头看一眼巴平,你说什么?巴心武没有看清巴平脸上的表情,因为巴宗站了起来,拎着拳头,一步步逼向巴平。巴宗没有打巴平,他因愤怒而声音嘶哑地吼道,巴平,早晚我要结结实实打你一巴掌!
巴心武低头看看鞋上的鞋带,没有发现什么破绽。他甚至还抬腿原地迈踏了几步,最后挥舞着有气无力的手说,巴宗,你睡吧。
我饿,我还没有吃晚上饭。巴宗说。
从小学到高中,巴宗在漫长而又短暂的学生时代惹下了许多祸事。他把当代城市少年的坏毛病全部感染了。没人注意巴平。巴平像墙根下一棵小草悄悄生长,而巴宗却更像棵野蒺藜疯狂生长。在青春的标签悄然贴在巴宗身体的各个部位后,谁也没法预测巴宗的未来该是一副什么模样。
在高中时代,巴宗经常光顾老刘的杂货店。多嘴多舌的老刘对买烟的巴宗说,你爸不吸甲级烟,他喜欢吸乙级烟里的这个牌子!巴宗望着包装粗糙的香烟壳笑着说,老刘呀老刘,你快赶上事儿妈啦!告诉你。我买烟是自个吸。巴宗光顾杂货店还有一个目的,是想见见刘小英。老刘的老闺女刘小英有时替老刘看看店。
一个炎热的午后,巴宗走进了又阴又暗的杂货店。他发现靠门那儿添置了一台霄化牌冰柜。刘小英穿着领口又浅又大的花衬衫神情专注地看小说。梳洗干净的浓发从她头上垂挂着,根根清爽并透出点微黄。她袒露在花衬衫外面温润细嫩的肌肤,让巴宗感到这美丽的人体下血液的流动,嗅出它散发的馥郁的芳香。巴宗在听见自个粗重的呼吸后吓了一跳。刘小英扔下书生气地说,巴宗,你看什么?巴宗不好意思地抓抓自个天生带点卷曲的头发说。想看看你读什么书。他拣起书看了看。我不喜欢台湾娘们写的书,她们光知道赚取少男少女的眼泪。刘小英讥讽地说,你好像是个成熟的男子汉啦。巴宗解释说,你误会了,我只是对书的内容做个笼统评论。巴宗一面说一面从口袋里摸出烟盒,从里头拽出最后一颗香烟。刘小英发现巴宗抽烟的姿式十分漂亮而且有点与众不同。巴宗手里的香烟散开的烟雾如午后斜射进店门口的阳光把巴宗幻化成非常虚幻却又非常实际真实的小男人。十七岁的少女就是在这一瞬间对巴宗发生了质的变化,她口气温柔地说,巴子,你吸烟不怕家里人发现?巴宗把一口烟喷吐在她的脸上,她羞红的脸很快被烟雾裹缠住。她一面挥手赶着烟雾一面轻轻咳嗽着说,你这人真讨厌!巴宗笑着说,这是早晚的事,我不怕发现。他把一只手搭在刘小英的肩上又说.你要肯供应我香烟,将来我会加倍偿还你。刘小英被胆大妄为的巴宗征服了。她从柜台里摸出盒香烟说,你想得美,到那一天谁知道你吸了我多少盒烟。巴宗机敏地说,到那时候也许就不用算帐啦。
一天下午,刘小英走进巴家发现巴宗不在。赤背看书的巴平穿上背心招呼刘小英坐。刘小英坐下感觉屁股硌得慌。她从屁股下摸出一支圆珠笔,把笔递给巴平说.谁的书?巴平翻翻书说,朱迪恩·盖斯特的普通人,她是美国女作家。刘小英说,我不喜欢外国人的书,读起来费劲,尤其人名难记。那你喜欢中国作家谁的书?巴平说着把掉在额上的一绺头发抹上去,手很优雅地落在椅扶手板上。他微笑着等待刘小英的回答。刘小英眨动着眼睛天真地说,能读下去的书都是我喜欢的。巴平呵呵笑了几声,抬手指着靠墙而立的两个书柜说,这柜里有你喜欢的书吗?刘小英望着排列整齐的花花绿绿的书籍说,你俩真伟大,有这么多书看。巴平幽默地说,伟大的是我一个人。他抚摸书柜说,巴宗对书没兴趣,他喜欢经商。刘小英拍着手掌说,经商同样伟大!
刘小英后来走到书柜前,认真地看着一排排书籍上的书名。她看见书柜的隔层上有个有机玻璃盒,便问,这是什么?
巴平拉开书柜的玻璃扇,探手拿出漂亮的有机玻璃盒,掀开盒盖说,金壳怀表,我爷爷留给我爸的。
刘小英从衬着玫瑰色天鹅绒的盒里拿起怀表,表的正面雕着精致的罗马数字,表壳的做工非常精巧。她用手轻轻捋着闪着金光的怀表链说,这表链好像也是金子的吧?这么贵重的东西摆在这儿不怕丢吗?
巴平透着得意的笑容说,我爸说了,谁考上大学,谁就是这块怀表的主人。
刘小英盖上盒盖用一种肯定的口气说,巴宗不会是这块表的主人,你是这块表的主人!刘小英看见巴平游移不定的目光想捕捉住什么,便及时地把脸转向书柜。
巴宗倚靠着他家门口那根电线杆,对满脸愁云的刘小英说,现在不要后悔哪门没考好,后悔是一种无能的表现。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继续上学,一条是跟我练摊。
我的事不用你管,我知道该怎么办。刘小英说到这儿脸上出现了笑容,巴宗,明天我们去公园照相玩吧,我好久不去公园啦。
巴宗从朋友那儿借了架康泰克斯牌相机,他没有玩过这种需要调光与测距的相机,他要演练演练。免得在公园弄出笑话。刘小英被巴宗推到他家院里那棵石榴树下。她摆出一种姿式,巴宗退后几步端着相机看了看,又走上前纠正她的姿式。
巴平就在这个时候从外面回来了。他说,在院里照是不是浪费胶卷呀?
多嘴的刘小英说,我们是要去公园照。
我也去吧?巴平说,我有两年没去公园了。
巴宗当然不会说什么。
八月的公园景色宜人。仨人在湖边柳树下、花丛假山前互相拍照。拍到快完时,刘小英提议,咱们仁人来张合影吧,要不巴平考上大学走了想照也照不上。仨人挑选了一个满意的背景,然后期待着一个会照相的人帮忙。终于等着个背相机的中年人。中年人很乐意帮他们合影。巴平在左,巴宗在右,刘小英在中间,中年人端好相机,说声照啦。中年人还给他们相机说,胶卷完啦。巴宗递给中年人一
根烟,请人家帮忙把相机里的胶卷取出。找到家个体照相馆冲洗胶卷,仨人便到附近一家冷饮店吃冷饮。大家吃着冷饮,说着些无关紧要的话,后来巴宗一人到个体照相馆取胶卷。
巴宗沮丧地拎着黑蛇似的胶卷往回走.远远望见白蓝相间的遮阳伞下坐着的巴平与刘小英很像一对情侣。刘小英艳美娇嫩,巴平朝气蓬勃。他俩用又细又长的白塑料管吸吮瓶中冷饮,吸一气停下说一阵话,然后又吸,透示出一种情调。一丝不快悄然爬上巴宗的脸上,但他走到遮阳伞下就把不快扔掉了。巴宗把胶卷扔向圆桌上说,全他妈照坏啦!巴平与刘小英制造的很有情调的气氛被巴宗破坏了。刘小英把胶卷挂在手上对着天空看,看到最后她说,就最后一张合影还能洗。巴平掏出块手绢擦着嘴说,这就证明,我们不会玩这种调光测距的复杂相机,如果是傻瓜相机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在回家的路上,刘小英在一家照相馆洗了最后那张底片。
取出照片是三天后的事情。
巴宗盘腿坐在床上端详照片。他觉得站在刘小英左边的巴平很不顺眼,便喊在外屋看电视的巴平递给他把剪刀。笑眯眯的巴平一下从刘小英身旁飘落而下。巴宗端详着剪好的但不成比例的照片哈哈大笑。
你笑什么?巴平从外间屋蹿了进来。
把你从我俩这儿开除啦。巴宗把剪下的照片递给巴平。巴平忧伤地看了眼手中照片,然后把照片夹在随手够着的一本书里。粗心的巴宗没有注意到巴平瞬间忧伤的神情,他把剪好的照片贴在穿衣镜前。
大学生巴平在八月底登上了北行列车。
在巴平临走那天黄昏,巴家的院子飘扬出阵阵欢歌笑语。路过巴家的人禁不住问,巴家怎么啦?回答说,巴平考上了大学。问的人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巴宗准没考上。
巴家的酒桌前没有巴宗的影子。巴宗在哪?巴宗与刘小英相互依偎着坐在大石桥上瞭望城市夜景,心情又澎湃又懊丧。刘小英指着座被灯火镂空的大厦说,我要去银座饭店工作。她扭过脸忧虑地望着巴宗,你呢?巴宗这时候开始吸烟,刘小英便无声地依偎到巴宗的怀里,汗叽叽的小手轻轻抚摸着巴宗的脸颊。巴宗扔掉香烟,捧起刘小英的头,望着一眼闪着兴奋一眼闪着惶恐的初恋少女说,我练摊!刘小英慢慢合上眼睛。合上眼睛的刘小英对巴宗是一种鼓励或暗示。巴宗俯下头,吻了吻刘小英涂着口红的嘴唇。
巴平走后,巴宗决定按自个的心愿布置房间。手拿抹布的刘小英发现贴在镜子上的照片,你怎么把巴平剪下了?巴宗整理着巴平留在床下的一箱乱书,霸道地说,我不许他站在你身旁!巴宗拿着本笔记本拍打着箱子上的浮尘。刘小英注意到一张照片从笔记本里滑落而下,她发现那是一张被巴平处理过的仨人合影。刘小英把照片递给巴宗,你俩真有意思,谁也不喜欢谁。巴宗用手指弹着照片说,这是巴平的风格!巴宗撕碎照片,然后对目瞪口呆的刘小英笑着说,这是巴宗的风格!
天黑后,在这座城市的几条主要大街上,会听见飘来荡去的舞乐。舞厅的诱惑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舞客乐此不疲。巴宗与刘小英就是一对乐此不疲的俊男靓女。
那天晚上,巴心武发现书柜里的有机玻璃盒空了。金壳怀表哪里去了?
巴宗跳到很晚才回家,他穿过院子时发现石榴树下站着一个人。谁?你爸!巴心武往前走了走说,问你件事。巴宗不知道要问他什么事,他满不在乎地说,让我进屋喝口水吧。巴心武拉住巴宗的胳膊问道,把金壳怀表鼓捣到哪啦?巴宗愣怔片刻说,记着你曾经说过,谁考上大学谁就是这块表的主人。巴心武说,我没有给巴平,巴平走时也没说过金壳怀表的事。巴宗挣脱他爸的手,临进屋门时他转身说,是不是放错地方啦?巴心武吼道,我他妈没有老糊涂!
巴宗夜里做了个奇怪的梦;他与巴平去佛寺许愿,一尼姑没头没脑对他说:“你不要再做坏事啦!”他问尼姑:“怎么说我像是做惯坏事的人?”尼姑两手合十,垂着眼皮说:“你的眉宇间飘荡着一股邪气。”烧完香的巴平正好从寺里走出。巴宗一把拽住巴平问尼姑:“他呢?”尼姑盯视巴平片刻说:“阿弥陀佛!”他气愤地推了尼姑一掌,尼姑一面倒退一面自语道:“果然应验!”
巴宗醒来看见何秀珍两眼红肿坐在床前。他翻身坐起来,妈,你哭什么?何秀珍擦着眼泪,小心翼翼地说,妈只是问问,是不是把表给了刘小英或者卖啦?巴宗穿衣蹬鞋的一系列动作迫使何秀珍闭上了嘴。巴宗气冲冲走到门口说,你们认为是我就算是我吧:
巴宗走在平正里大街,觉得家里发生的怀表事件有点麻烦。怀表真的被人偷了吗?知道书柜里有怀表的人除了他们一家人就是刘小英。难道是刘小英?这个念头一闪就被巴宗强制性压了下去。在那天早晨碰见巴宗的人发现他脸色苍白神情恍惚。
何秀珍没有上班,也没有像往日那样挎着菜篮上菜市场,而是走向刘家。刘家木门上挂着把生锈的铁锁。何秀珍又拐向刘家的杂货店。她站在店门口冲刘小英招招手,问刘小英见没见过他家的金壳怀表。刘小英简短地回忆了那次巴平让她看表的经过。何秀珍问,后来呢?刘小英说,没有后来!她坚定的态度使何秀珍不好再问。
巴宗在早点铺吃过早点去找刘小英。刘小英坐在店里生闷气,看见巴宗就问,你妈刚才来问怀表的事,这是怎么回事?巴宗耸耸肩摊开双手说,那只表不翼而飞。明白过来的刘小英怨气冲天地说。把我当成怀疑对象啦!不用解释,问我就是怀疑我。她突然捂住脸抽泣起来。巴宗生气地拍打着柜台喊,傻×,不是你你哭什么?刘小英停止哭泣,抬起泪水涟涟的脸说,别是你拿了吧?巴宗的脸色又突然苍白起来。
金壳怀表带来的灾难实在可怕,巴宗在无数个夜晚感受着一个快要步入成人的复杂心情。这是种既复杂又单纯,既悲伤又欢乐,既无奈又无怨的心情。
巴心武有一天说,我准备报案。巴宗说,为什么不问问巴平?巴心武说,巴平要是拿了会告诉我们的。巴宗无奈地说,只有依靠警察啦。巴心武带有威胁性地说,警察要是查出来,性质可就变啦!
平正里大街的街民很快知道巴家丢失了块金壳怀表。门窗没有被撬痕迹,家里什么东西也没丢失,唯独少了那块金壳怀表。懂点侦破知识的人应该清楚,怀表是家里的某个成员或是熟悉这家的人窃取的。
家贼是谁?熟人是谁?
街上的闲人见了巴宗问,案子破了吗?你爸够黑的,为块破表就想把你送入大牢。巴宗疑惑地问,为什么要把我送入大牢?人家故作神秘地说,你爸妈不会拿,巴平也不会拿。巴宗点着自个的鼻子用一种咄咄逼人的口气说,可事实上我没有拿呀!人家冷笑着说,别忘了你是操蛋鬼巴宗!
刘小英感受到了外界的压力,她不得不这样对巴宗说,巴宗呀巴宗,如果是你拿了就还给他们吧!巴宗吞咽着唾沫,尽可能使自个不再出声。他透过朦胧的泪眼望着刘小英。刘小英看见巴宗痛苦地闭上眼睛,两行泪水从他紧闭的眼里慢慢流出。
巴家丢失金壳怀表的消息像风一样漂荡
在桥东一带。巴宗没有想到还有件麻烦事等着他。巴宗收拾租下的房子准备做时装店,房子的男主人气势汹汹地阻止了他。巴宗放下手中的工具问。为什么?男主人说,等你家的金表案破了,我还让你租。巴宗气愤地说,我们有合同。男主人笑着说,合同没有公证没有法律效果。巴宗说,你要懂法律应该清楚金表与租房风马牛不相及。关系非常密切,我不想让我家丢失一针一线。说到此男主人粗暴地把巴宗推了出去。巴宗默默地站在石阶下,看着人家用一把象鼻牌铁锁扣上了门。
连续的几件事使巴宗的脸呈现出死灰相,不论谁和他讲话,他都懒得回答,目光呆滞滞的不知望向哪儿。他弄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一致认定丢表的事是他干的呢?他不明白什么叫习惯,习惯就是自然。
放寒假前,巴平给巴宗来了封信,信中写了他回家的日期与车次。巴平在信中叮嘱巴宗一定要去车站接他。为什么要我接站?心情恶劣到极点的巴宗把巴平那封信撕碎,并把它扬得如同雪花飘落般精彩。
天气寒冷阴暗,还刮着凛冽的风。太阳显示不出一点精神,挂在天上,像张剪圆的白纸片。巴宗面色阴郁地站在宽大的水泥月台上。他穿着件米黄色的佩肩风衣,腰带系得紧紧的,保持着一种挺直的姿式等待着北京方面开来的列车。巴宗在乱哄哄的人群中发现了巴平。巴平脖子上挂着条猩红色的羊毛围巾。他向巴宗走来时,围巾的流苏四散飘扬,透示着无限的青春气息。巴宗看见巴平一绺又黑又长的卷发飘荡在光洁的眉宇间,这使他平添了一种独特的气派。巴宗后来就看见巴平身后那个梳短发的女学生。女学生穿着件条绒棉猴,拎着个黑色皮箱。女学生冲着巴宗笑,巴宗发现她的嘴唇很性感,他猜测这个没擦口红的嘴唇被巴平吻过了。巴平温文尔雅地对巴宗介绍说,同班同学苏雅静,桥西住。苏雅静跨前一步,笑容灿烂地说,你比巴平老成,看着更像哥哥。巴宗无动于衷地说,我帮你拎皮箱。身后那列客车长鸣一声,把仁人都吓了一跳。巴宗知道是列车启动了。巴宗听见苏雅静问巴平,他显得很老相,他生活得很累吗?
巴平走出车站追上了巴宗,巴宗,你失恋了吗?巴宗见一辆计程车缓缓驶来,他高声喊叫着向计程车招手。
上了计程车,巴平从皮夹克内口袋掏出金壳怀表看了看.说,十分钟后就到家啦!巴宗怔怔地望着巴平手里金光灿烂的怀表说,你拿的什么?巴平拎起表链让巴宗看。巴宗抢过来说,你拿时怎么不给家里人说一声?巴平轻松地说,他们答应给我了,我自然把它看成是我自个的东西,没有必要再说。巴宗的脸就红了。他把手里的怀表倒了一下手,腾出的右手飞起给了巴平一掌。巴平捂着渐渐红肿的脸颊说,为什么打我?巴宗把怀表扔给巴平说,回家你就知道啦!巴宗说完摇下车窗玻.璃,趴在车窗口吹响了口哨.他吹的是美国乡村歌手约翰·丹佛的成名曲《飞机上告别》。司机警告他,过路口啦。巴宗就把头缩进了车厢。巴宗说,习惯就是自然。巴平问,你说什么?巴宗不说话。
责任编辑邹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