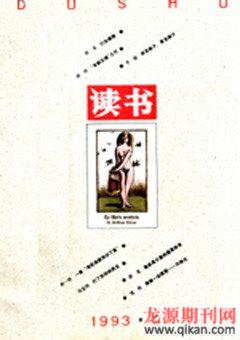“金杯”与“白刃”
卞东流
谢苍霖、万芳珍夫妇九阅寒暑,从二十五史和《资治通鉴》以及历代野史笔记中广泛搜寻“文祸史”材料,经过细致的爬梳、整理、分析、概括等工作,写出了一部四十多万字的《三千年文祸》。
本书所纂辑的“文祸”事件不下数百起,包括诗文著作之祸,疏谏之祸,以及科场案之类。所历时间自夏朝末年至清朝末年,合计是漫长的三千余年。其中有不少文祸有其特异性,但更多的是近于历史的重演,有很大的共同性。
笔者翻阅一过,觉得全书所述史事虽广泛,也自有其重点。这主要见于第三章《两汉君主“逆鳞”杀人》,记述了汉武帝时颜异死于“腹诽”,司马迁遭李陵案之冤。也记述了汉宣帝时诛戮直臣,有盖宽饶的自刭,杨恽的被腰斩等案。特别是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中有“田彼南山”一诗,被佞臣曲解,诬告,成为由诗文而引起的典型的文字狱,株连甚广,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不同于两汉文人因“逆鳞”受祸的是,第六章记述了魏晋南北朝文人言词“轻薄”之祸,这一章剖析了祢衡与孔融之被杀,嵇康为司马氏所诛的内因和外因。对谢灵运祖孙和颜延之父子的得祸,也作了符合实际的分析。
诗文之祸,盛于隋唐。隋代有司马幼之、薛道衡与王胄的案例。唐代文祸涉及许多知名之士,如戴令言、李白、顾况、刘禹锡、白居易、贾岛等,都曾因所作诗文遭谤或受迫害。其中尤以刘禹锡以《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绝句》两诗,一再被诬得祸,广为人知。当然,刘的被贬,主因还是由于他参与了顺宗时王
本书第十一章《北宋党争与文字狱》,详述乌台诗案以及苏轼后半生的诗文之祸,对权势者的倾陷嘴脸和文人的内心不屈,都写得恰如其分。
明太祖朱元璋不谙诗文之道。他在率军争夺天下之初,一度尊重儒士,善用刘基等人的良谋;但登上龙座以后,对士大夫颇多嫌忌,对他们的言行和诗文,好作毫无根据的揣测,更善于罗织罪名,因此他“钦定”的文字狱案特别多。著名诗人高启给苏州知府魏观写了篇《上梁文》,文中有“虎踞龙蟠”等套话,朱元璋诬称魏观想做“张士诚第二”,于是魏观被诛,高启被腰斩。本来,“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朱元璋要树立帝王的权威,常常强迫儒生出来做官。他曾对遇事敢于直谏的户部尚书茹太素一度有过好感,一日赐宴便殿,亲自赐给他一杯酒,赠诗云:“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和了两句:“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但就是这个茹太素,后来仍然无缘无故地得了重谴,终于死在狱中。看起来,朱元璋擅长一手执金杯,一手执白刃,对臣僚百姓的性命,常按一己的喜怒,任意处置。这种以金杯相诱,以白刃相胁的心态,是历代封建君主所共有的。本书对明清两代文字狱案例的记叙,占了五分之二的篇幅,剖析尤其详明,这是因为作者深觉明代愈近,发生的文祸对后世的影响也愈大之故。作为“文祸史”的通史看,这样“略古详近”,确是十分必要的。
清初发生于康熙年间的《南山集》案主角戴名世,是一位古文家,他爱读史、修史,对史家的才、学、识以及正史、野史的利弊得失,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感叹于南明史迹之日渐亡佚,曾在《与余生书》中说:“史事渐以灭没,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荡为清风,化为冷灰。日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他的话是针对南明史事而说的。不幸的是,他的有志于修南明史,触犯了新朝之大忌,被诬以“谋逆”罪,结局是凌迟处死。但后人细读他的《致余生书》,只觉得他的乐于修史,乐于为后世树立“史鉴”之心,是颇为可敬的。
通览《三千年文祸》,难免使人对封建专制政权统治下的许多文人的惨酷下场,深感不幸;尤其是对原本忠贞不贰,只因一二篇诗文引起“人主”误解或曲解而遭蒙横祸,这种由于君臣之间难以互通心曲导致的悲剧,更使后人兴起苍凉感。我在前文已经点明:朱元璋对于臣僚采取的两种手段:金杯与白刃,是深谙君主驾驭臣僚之道的,也可以说,这是历代“人主”对于臣僚所采取的共同手段。无数文祸,有的确是受祸者一方不甘于以暴主之心为心,不肯亦步亦趋,而要独呈己见,坚持自己的一点看法,于是遭受迫害,如汉代的司马迁、杨恽,宋代的苏轼等;但绝大多数文人之受祸,却并非在“金杯”与“白刃”两者之间有所抉择,只是或因卷入了政争、宫闱之争的漩涡,或因所作诗文被小人挟嫌诬告,或因出于忠心说了些帝王一时不太理解的话,于是不仅自己丧命,还株连了三族。说到底,敢于在“金杯”与“白刃”面前坚定地选择了“白刃”而九死无悔的蹈祸文人,毕竟是不多的。三千年文祸所产生的悲剧,可谓众矣,此中却又有多种多样的差别,由此可以得出什么启迪呢?这正是后人所应关心并探索的。
也正为此,我从戴名世深恐南明史亡佚一事生发开去,觉得历代文祸的始末,如不及早从大量史籍中寻踪,钩稽,并做些去伪存真的工作,这些史料也可能相继澌灭,化为尘灰。所以,谢、万两君以九年功力,写出这部《三千年文祸》来,他们的劳作是值得人们珍重的。
本书案例繁多,作者一一道其颠末,述其故实,是其优点。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书首缺乏一篇综述文祸起因之共性和特性的绪论;出末缺乏一篇剖析封建专制制度与惹成文祸之关系的后论。如果有了这两篇切中肯綮的综论,我想,本书当可更见精采。这只好寄希望于本书再版时的修订了。
(《三千年文祸》,谢苍霖、万芳珍著,江西高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版,9.20元)
品书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