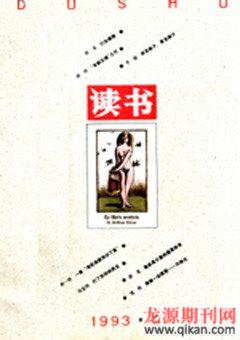现实秩序与诗的理想
来凤仪
一九二三年,二十四岁的闻一多,自费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红烛》。
《红烛》给“五四”以后的中国诗界带来了新的消息,一个充分艺术化的叛逆人格本身即是变革之兆,其影响几乎不亚于两年前郭沫若《女神》的问世。如果说《女神》是气势磅礴的回旋曲,是为封建主义送行的葬歌,那么《红烛》则是以感伤的生命激情谱写的一组无伴奏合唱,纯如肺腑之音,在风雨如磐的天穹下更具幽远、悲凉之意。跟《女神》一样,《红烛》也被人视为诗人的忏悔书和自叙传,它们都是那一时代的见证,同样展示着从封建主义家园出走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面对二十年代初的动乱之世,闻一多的诗情是沉重、悲抑的。其早期诗作尤其交织着希望与毁灭、挚爱与感伤的情绪。他是那种政治意识很强而艺术上又不肯稍让半分的诗人,而这种双重追求本身就构成了内在的冲突。几乎就在走上文坛的同时,他已经投入了政治活动。但诗人尽管曾尝试“唤起民众”,干预时政,但在艺术上他却并不随从民众的口味。铁的抬轿的一般程度”,他说他并不看轻打铁的抬轿的人格,但确信他们不是作好诗懂好诗的人。“诗是诗人作的,犹之乎铁是打铁的打的,轿是抬轿的抬的。”毫无疑问,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唯美主义性质。他在自己的创作中,自是如此一以贯之。《西岸》是他发表的第一首新诗,这首诗的题辞引用了济慈的诗句,其大意为:“这是一个充满欲望的春天,此时此刻,明晰的幻想把所有能吸收的美都吸收进来了。”这几乎可以看作他对诗歌艺术的理解和追求。
诗的境界与现实生活总是存在相当的距离。对于现实世界,追求艺术的诗人正有如偷食神药的嫦娥,置身于世外遥相观照。闻一多的诗歌虽说很少直接干预现实,但也总是曲折地感应着生活的风雨。他对生活的审美态度是冷静而疏远的。其实,诗人内心恰如一座封了口的火山,深处蕴藏着炽热的情感。他的第二本诗集《死水》尤其体现了这种特点,“死水”下面涌荡着激流与波涛。这给当时诗界带来了一种令人惊讶的风格。从理论上讲,闻一多主张感情的节制,控制主观情绪的泛滥,并非没有道理。三十年代以后,诗坛上大量出现以主观情绪拥抱现实的作品,以叫喊代替审美的口号诗、标语诗。那些作品之所以未能在文学园圃里生根,其原因不外乎将诗歌等同于标题新闻或政论文章。所以,感情节衡得当,对于调节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闻一多不主张直接将现实投入诗中,并不意味着他对世事置若罔闻。相反,他倒是把诗人比作一张唱片,随着生活的节律而转动。不过,这个比喻容易给人造成另一种误解,以为这是在提倡艺术中的机械反映论。其实,他试图说明的是,艺术只是被动的生命体,诗人对于现实,能够感应却无能为力。诚如他诗中所言:“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之内”(《闻一多先生的书桌》)。
事实上,现实秩序的确不在诗人的能力范围之内。面对北洋军阀的混乱世道,他愤怒过,也曾奋臂抗争;然而在一个充满癫狂的时代里,理性的思考总是一再被枪声炮声打断。为了保护自己的理性,诗人只好退到一旁,冷眼看世界。譬如,他的《天安门》一诗,为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惨案”所作,而诗中对段祺瑞政府枪杀请愿学生一事,只借用一个旁观者(车
其实,“为艺术而艺术”只是相对“为政治而艺术”或“为金钱而艺术”而言,或者说是诗人摆脱某种世俗价值,建立独立人格的前提。这种选择应当可以理解。这是许多成熟的诗人都遇到过的问题。许多诗人、作家都有过从“呐喊”到“彷徨”,从匆忙入世到驻足静观人生的转折。尤其像闻一多这等严肃诗人,对自己所曾扮演的社会角色不会不进行检讨。既然他们无法在世俗层面上跟恶势力抗争,更无法在政治活动中把握自己,则可考虑的便是借助艺术来确立自己的叛逆人格。
当然,闻一多终竟不只是一名艺术家,他还是一名坚韧的民主斗士。他可以长时间地沉默,不问世事,甚至连诗也不写了(一九二八年出版《死水》之后,他几乎就不再写诗),转而去研究唐诗,又从唐诗往上搞到《诗经》、《楚辞》、上古神话。然而,当时代真正需要他的时候,或者说他可以召唤世人的时候,他终于站出来大声疾呼,毅然决然。他不用诗歌召唤民众,而是直接了当向人们讲述民主。抑或民主也是闪光的诗行?民主大约跟诗具有同样的理想,只是多半写在血泊之中。是的,诗人做完最后一次讲演,便倒在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昆明。
如今,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带血的历史像风中的花瓣一样散去,留下了一段悲伤的记忆,也还留下一路的芬芳。回眸之际,书案上只是一册诗卷。诗人身后,那片荒芜的瓦砾场依然如故。
闻一多的诗并没有做完。
(《闻一多抒情诗》,林甄编选,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品书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