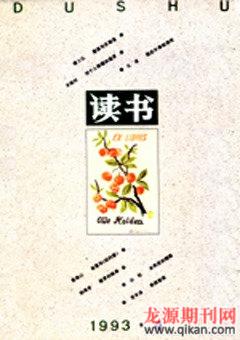悲悼《柳如是别传》
李 劼
悲剧《红楼梦》于非人世界拓出一片人性天地,《柳如是别传》从历史深渊推出一团人格光明。所谓人格光明,当类于马丁·海德格尔《Being and Time》之Being,或曰存在之敞开,或曰存在之关怀。窃以为,正是这种存在关怀意义上的人格主题而不是常人所云之爱国热情,使《柳如是别传》高出于其他相类题材之作,而足以与《红楼梦》媲美。
爱国热情乃一古老话题,几与女子的操守贞节相同。而恰恰又是女子最易被莫名其妙地视为亡国之祸根,一如她们也往往因被断言失身而蒙耻。其缘由或许是源于男权世界中的女子,历来身处弱者地位,王公贵族侵占其身体,文人学士审判其道德,既无肉体之自由,亦无灵魂之标扬。一句“商女不知亡国恨”已是千古定评。可诗人大概不曾想过,国家之兴亡,商女本无责。这个世界为男人掌权,男人操戈,成败兴亡,唯男人是问,何以感慨“商女不知”?与之相应,救国救民之光荣则总也落不到商女头上。当年夏衍先生的《赛金花》一剧似有此意,然因鲁迅先生一觉醒来发现“与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阵的赛金花也被奉为九天护国娘娘”而作罢。鲁迅的深刻自然远在杜牧之上,且不说对历史的洞察力,即便伦理观念,也有其早年的《我之节烈观》作证,然其晚年也偶尔难以免俗。可见女人尤其商女与亡国之关系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传统因袭,如激烈反对女人亡国说如鲁迅先生者,有时也会落入文化积习的圈套。
那么,陈寅恪先生作《柳如是别传》其意何在?难道仅意在言说商女更知亡国恨吗?
倘若仅此而已,《桃花扇》便足矣。
寅恪先生于《柳如是别传》述及河东君与钱牧斋事迹时,曾讲到柳如是的“三死”:
乙酉五月之变,君劝宗伯死,宗伯谢不能。君奋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
是秋宗伯北行,君留白下,宗伯寻谢病归。丁亥三月捕宗伯亟,君挚一囊,从刀头剑
宗伯薨,族子钱曾等为君求金,于六月十八日自缢死。
“三死”显然以柳如是为红花,以钱谦益为绿叶。然仅止于此,《别传》则与《桃花扇》无异。而我以为,《别传》高出于《桃花扇》之处,不在于对柳氏的讴歌,而在于对钱氏的理解。
寅恪先生固然不以宗伯行止为然,并于行文之中时有讽意,如评说钱氏被讥为两朝领袖的史料时说:
牧斋在明朝不得跻相位,降清复不得为“阁老”,虽称“两朝领袖”,终取笑于人,可哀也已。然统观全书所述,作者多有持平之论。同样为“劝死”的史料,至若《蘼芜纪闻》引《扫轨闲谈》云:
乙酉王师东下,南都旋亡。柳如是劝宗伯死,宗伯佯应之。于是载酒尚湖,遍语亲知,谓将效屈子沉渊之高节。及日暮,旁皇凝
尚湖西山皆在常熟,当南都倾覆时,钱柳皆在白下,时间地域,实相冲突。此妄人耳食之谈,不待详辨。
以寅恪先生之见,柳如是与钱谦益之间,虽然性格相异,“一诙谐勇敢,一迟疑怯懦”,于选择生死上也殊多差异,但两者的选择却同样严肃。何况钱氏留恋生活,并无卑劣之迹。《别传》曾连引数则史料,论述钱氏有关柳氏与他人往来一事之态度,如:
当谦益往北,柳氏与人通奸,子愤之,鸣官究惩。及归,怒骂其子,不容相见。谓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此言可谓平而恕矣。《别传》并不因为钱谦益的迟疑怯懦而一味痛斥,相反,作者于开卷缘起一章便点明: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而不能自已者焉。
自己“不降志,不辱身”,然亦不因此自觉高人一筹,贬诋他人。强者虽有强者之刚烈,弱者亦自有弱者之尊严。正是在这一点上,《柳如是别传》高出《桃花扇》一筹。《桃花扇》可列为历史上有关商女与亡国之关系的别一种说法。粗粗一看,这类作品似亦为商女伸张,如李香君之大义凛然。然深加细究,则可发现,此种爱国热情乃节妇烈女的同义语。中国历史上的统治之术有王道霸道之交互,中国人的相残则有暴力屠戮与道德谋杀之区分。大群凌迟乃阳光下的罪恶,人人所见;道德绞杀却是黑夜里的阴谋,难为人觉。《桃花扇》张扬商女爱国,意在贬斥书生汉奸。李香君形像之于侯方域宛如一把道德匕首,刀刃所至,一片血肉模糊,而有趣的是,刽子手又照样由文人孔尚任担当。由于书生与商女同属弱者之列,既无大权在握,又无金戈在手,故每每在兴亡关头要被责问忠烈名节。书生从戎如辛弃疾者固然英勇可嘉,文人赴死如文天祥者亦可谓汗青丹心,然而倘若其均为名节而去,不亦悲夫?试问,帝王将相且无以保护其臣民,平民百姓(包括书生商女)又何以应为前朝殉葬?即便就清兵入关而言,此乃崇祯皇帝及大顺皇帝之干系,何以历史往往不究皇帝问书生?如果问一问在大明、大顺、大清之间,凭什么说选择这个光荣选择那个可耻?当何以置答。按照一种惯例,只要主战,打败了也是英雄;谁想谈判,成功了也有卖国之嫌疑。同样的逻辑用于书生,则因为其手无寸铁,总免不了有沦落的危险,一如中国女子时常面临名节问题一样。人格的关怀,往往不是强者的逻辑,而是弱者的哲学。强者大多注重功利,欲主宰生存的权益;弱者往往关怀灵魂,只将写存在的历史。然而中国人历来倾向于强者的专制权力而无视弱者的生存权利,故伦理准则总是按强者的意志制定。杜牧“商女”一诗如是,《桃花扇》一剧如是,几乎所有的传奇故事戏曲小说都如是(如《水浒传》里宋江杀惜,武松杀嫂,总是杀得理直气壮),唯有《红楼梦》唱了反调,唯有《柳如是别传》写了相反的历史。
中国人有帝王将相的历史,有起义造反的历史,又有为民主科学奋斗的历史,唯独鲜有弱者的历史,灵魂的历史,或曰人格的历史。以中国文化之境况,由于个体的被忽略,群体的被夸大;强权的膨胀,弱者的萎缩,故本真的存在通常以人格形式向此在敞开,在生死关头,在兴亡年代。汉末有党锢之争,明末有社团风潮,即如建安七子,魏晋风度,亦不失为一种灵魂的高扬。总之,是此种对人格的关怀和张扬而不是其它任何主题,构成了《柳如是别传》最为意味深长之处,成为其主旨所在。寅恪先生乃以此“痛哭古人,留赠来者。”也
几十年过去,高山犹在,流水依旧,盲翁之余音,已无迹可寻,所幸尚有《柳如是别传》连同《红楼梦》默然立于寂寞的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