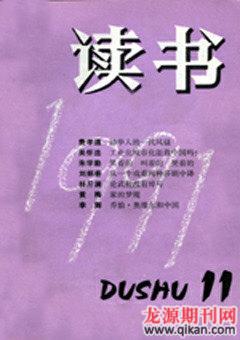战斗与爱情的统一
岳洪治
《哑歌人的自白》,是屠岸同志几十年来所作新诗的精选本。在这包括各类题材内容的一百几十首作品中,恋歌占有不小的比重。这些,诗人写于青年时期和进入老年之后的爱情诗,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屠岸同志,作为一个革命战士的本色,处处闪耀着战斗的理想光辉。
诗人青春期的恋歌,大部分收在了“慧眼”一辑中。《在我平静的时候》开头几句是这样的:“在我平静的时候,/请你不要出现/在我的眼前。/这原是无碍的,/但是我不愿看见/你走过我身边,/还回头/望我一眼,/扰乱了/我的心田。”分明是极想见到意中人,却又怕见到意中人。这里对内心平静的希求,恰恰说明了诗人内心的难以平静。作品以反衬的艺术手法,暗示了姑娘对诗人巨大的吸引力,把初恋的心理表现得很真实。在《阳光》一诗中,诗人写道:“有人教我对你骄傲些,/可是我不能够呵,姑娘!/因为你的无比的清纯/原只是为着要使我折服,哀伤!”在他眼里,这位“无比的清纯”的姑娘,就像“阳光”一样,不仅照耀着他,而且也以其光热,覆盖了他周围的人们。充分表现了诗人对姑娘无比深挚的爱情。《回答》一篇,则表现了诗人对爱情的执著与珍视:“你隔着黑色的篱笆投我以/严厉的不许接近的眼神,/我却只能够彻夜地伫立,/静静地依傍着你的窗棂”。而为了郑重地回答姑娘的邀请,他宁肯“无限期延伸”着相会的时辰。
在一个革命战士的人生旅程中,不仅要有出生入死的战斗,也应该有刻骨镂心的爱情的。写于一九四六年的《矫健的节奏》一诗,就生动地表现了一个年轻战士的爱情观。诗中唱道:“我也同样钟情于突起的风云;/暖巢不是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幸福是共同献身”。“我们的吻是我们的誓言:/让我们挽手汇入火炬的行列,/去达到最后的爱的完成”。在诗人的思情里,“爱人”,首先应是能够为着共同的理想而献身的同志;“幸福”,不是合力去营造一个小家庭的安乐窝——“暖巢”,而是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而以自己的“生命作燃料”,所进行的战斗。战斗并不排斥爱情。因为诗人既是为战而爱,同时也是为爱而战,二者拥有共同的目的。战斗的胜利,也就是爱的完成。
青春年少时的爱情,固然美好得像一朵带露的鲜花,而令人欣羡;但是,那不为岁月的迁移所磨损,不因红颜的衰老而消歇,能够始终不渝地将这份纯真保持下去的爱情,则尤为可贵。屠岸同志在花甲之年,因老伴住医院而写下的《龙潭湖的黎明》,和稍前几年写的《忧思》,所表现的就正是这样一种可贵的、感人至深的爱情。诗中写道:“我迷惘。仿佛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我翻开黄昏,它已经漶漫尘封。/仿佛有一丝笑影隐进了青灯,/然后是死寂。然而,会不会有夜风……”(《忧思》)晦暗、凄凉的意象,暗示出诗人对患病妻子的担忧,和沉重的心情。当病人终于转危为安,诗人才满怀欣喜地唱道:“缭乱中,我见到的不再是老人,是少女,/生命重新燃亮了美丽的双睛。/雪化了。黎明送来最初的春雨。”爱人身体的康复,也即是爱情的再生。巨大的欢愉,使诗人重又体会到了初恋时曾经有过的,那种既热烈又新鲜的爱情之波的冲击,因而,在他的眼中,才会又恍惚看到了,老伴当年那婷婷玉立的风姿。
屠岸同志的爱情诗,写得细腻委婉,具有一种内在的旋律和沉静之美。诗人对爱情那种真挚、热烈而又执著的态度,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展现了他真诚、善良、高尚的人格力量。而他写于青年时期的恋歌,不仅感情真挚、深沉,而且比较典型地表现了战斗与爱情在一个革命战士身上的完美统一,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的特征。
(《哑歌人的自白》,屠岸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年八月版,3.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