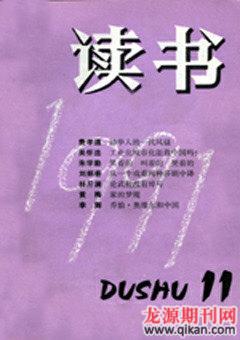残阳如血
桑 晔
文物也是书
今夕是何年?一九九一,大吉羊年。
过完上一个除夕,进入这一个三阳开泰,鄙人和大约一亿位中国人同样,开始了本命年,本命年又叫“再遇”,乃此轮回与彼轮回交接班儿的年头,应当老老实实地呆着,不可乱说乱动,最好能缠上条红丝线织的“腰令儿”。“腰令儿”是俗音讹记,本该是“腰里硬”,万一遇麻烦,可凭它抵挡一阵子。红丝带子再硬,也搪不住任何麻烦,老祖宗发明它,除去系裤子并使人挺直腰板作人,恐怕在于它能随时提醒你注意自律,别没事儿作死,吃饱了撑得捅马蜂窝。
更不应忘却,也不能忘却的是,现如今的这一个大吉羊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二十五周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于马年,去年即是它的“再遇”,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充分证明了《丙丁龟鉴》所揭示给宋理宗的规律已不再是中华运数的规律,后人演义的“红羊劫”,所谓“丙火未羊之岁,始乱生劫”之类,也很不一定准确。一九六六年的实践告诉当代的中国人,乱与不乱,跟天干地支没多少关系,真要生劫,不会等着“红羊”,始作俑者是顾不上查农历的。
二十五周年,时髦的词叫“四分之一世纪”,运动过四分之一人类的事儿,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了。不管别人咋说,我且替它写几行字儿。只是几行字儿,和读书没太大关系,原因明摆着——关于它的书不能算太少,真够上算本书的,看来却不多。比方《林立果和他的宫妃秘录》,虽然在书店里堂而皇之地卖着,您说它够叫书吗?
我要说的是我所收集的“文革文物”这种书。文物,其实也是书,无字的书,认真地用心看,未必不能看出个意思来。
所谓“文革文物”是我从“革命文物”这名目引伸转借来的。依有关单位的规定,自一八四○年以降,凡有纪念性或说明性的东西,由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文告到伟人挑米用过的扁担,甚或首长们开会坐了的椅子,都是革命文物,均在无偿征集和有偿收购之列。循此,把能反映“文化大革命”时代文明特质的物件称作“文革文物”似乎说得过去。当然也不妨把这些玩艺儿叫“文革垃圾”,我平日就如此叫的。
先说纪念章。
被称作“红像章”的纪念章是文革文物的一大项目。二十几年前,从咿呀学语的孩子到下葬入土的老人,胸前不戴至少一枚这东西,便很成问题。除去“黑五类”不配戴外,连进入大陆的洋人们也要戴的。
大规模制造像章的历史自一九六六年夏开始,至一九七一年夏结束,五年时光,据说造出了超过一万种,至少二十亿枚。我所收集到的像章有七千余种,就收藏量来说不是最多。四川有位老先生拥有一万三千余枚,大概是数量最多、收集时间最久的人——他从一九六六年开始攒这东西。可是,他的收藏是以枚数而非以种数计算,因此我猜不出他到底攒了多少种。我希望他在种数上也能比我多些,有这样一项专藏留存在中国,对于治疗“失忆症”很有用处。
至少有两个人曾在种数的收藏量上超过我。一位是顺群,她的收藏和她的人一道灰飞烟灭在一九七一年。在七十年代初,她保存着全国各地“敬献给林副统帅”的近一万种像章。据担任过林彪办公室秘书的人讲,当林彪见到自己的头像上了纪念章时,大发脾气,命令“毁掉,不许再做”。由于中国人做任何事都不会彻底的习惯,我在一九八九年春尚收集几种林彪像章。当时,半地下的北京“文革文物市场”已极难见到林彪像章的“真品”,有人推出赝品,叫价一百五十美元,而最常见的毛主席的像章只值人民币几角钱。
另一位是北京的某中学教员,他从大学时代开始,以全副精力和财力收集到大约八千种,集像章出了名。七十年代末,彻底否定“文革”,收走了他的全部收藏,投进炉中化铝。这位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因红卫兵将他自幼收集的上千种火柴盒付之一炬,所以收集像章的人,终于发现自己是什么也存不住的,于是什么也不收集了。
就是这种令人叹息的阴差阳错,使我这个在“后毛时代”才开始收集的后来者,莫名其不妙地成了像章的“收藏家”之一。
把我现今收集到的七千余种像章摊开,“红海洋”所泛起的不仅是某种疯狂,也是当时所能表现的重重约束。
设计者所受到的第一个约束是:形象必须严肃庄重;其次的约束现在看很可笑,当年却是必须遵从的——在早期制作铝制品时,除正面像,凡侧面像,人物的脸都朝左方。再次的约束自然还有,且不去说它了。
在七千余种像章中,唯一的一枚铝制品的“向右看”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出品,设计者因此获罪,蒙冤多年。若不是一位有心人在当即收缴的几千枚中拣出一枚保存下来,恐怕如今能和世人见面的铝牌牌儿都是左半边儿的了。进入八十年代,“向钱看”了,那位有心人狠狠地敲了我一笔,交易后却还以为他亏了,他相信只要是举世无双的东西,全能在外国拍卖至少一万美元。这种新时期的走火入魔,从正面说,确实给我创造了比较方便的收集环境,负面却真让人肉痛——镀金、纯银的像章要比照现时的首饰价翻几番出让。
“文化大革命”中,戴像章还成了佩戴者夸示自己所在的组织或单位,以及他本人的与众不同的工艺化的标志。正是因着这个,引无数英雄竟折腰,将一个人的形象设计成上万种不同的纪念章。有位集数种现代技术于一枚之上,设计并主持制造出在金属板上复制彩色像的朋友曾告诉我,他设计这种至今仍够精致的像章,是为了“盖过别人”。这种像章发行了上万枚,他自己却一枚也没有保存,“你留着这万分之一纪念我吧!”一九八九年春末,我离开北京之后,很长时间得不到关于他的准确消息,于是时常忆起他这句实在不吉的、当时的玩笑。
真够上大流行的像章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红地金像,当时售价仅七分人民币,至今人唤“七分钱”。另一种是总政制发的,金头嵌在五角星中,下有一横章,“为人民服务”,人称“军星儿”。这两种共赠发和出售了一亿枚。另外,各地又制作过一二百个常见的品种,总数又有亿枚以上。这些像章曾支撑着在一九八○年中期兴起的,以海外来华旅游者为对象的“像章市场”,爱好者能很方便地随处购到。
自一九六七年春,凡是有一点能力的工厂、学校都要做像章。这个“凡是”,偶然地保护了一位现今至少很有新闻价值的人——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蒋纬国在台北的孙中山纪念会上说:当年在黄埔,孙先生以“经纬安定”替三位重要助手的孩子命名,如今,蒋经国和戴安国已去世,金定国却杳无音讯。六十年前的童年伙伴,现在哪里?北京的新闻媒体报导了这则消息后,黄埔同学会、金氏故里的地方志办公室和别的有关单位们,开始寻找这位金定国。原来,刑满释放后留在安徽,人已退休、伴着老妻和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活着。金定国和蒋家王朝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揭露,而他能逃过这一劫的原因,是他已被改造成电镀高手,成为安徽省制造像章不可或缺的人材。十年动乱,金定国在军队、地方二十余个单位,亲手电镀及现场指导制造的像章,不下二百万枚……
大潮刚刚涌来时,不免缺少些章法,出一点趣事,比如广东出品的一款,背面竟有“版权所有,不得复制”。革命得天地翻覆了,还有人想着版权。再比方上海的几款“精神原子弹”,把领袖和核子云设计于一,居然不怕受沾染。
一九六七年春末到一九六九年夏,像章的黄金时代到来了,品种如过江之鲫。依制造材料分,有铝、铜、钢、银、瓷、玻璃、塑料、竹、木、防水纸板等等。塑料品种的复杂造就了塑料制品像章的多样,平面的、立体的、硬的、软的、彩色的、黑白的;用萤光塑料做成的“夜明像章”至今可在暗中放光,用折光塑料配合偏心装置做成的“闪光像章”仍旧可在胸前转动闪亮。甚至还有砸不烂,摔不坏的,泡在淡水、海水、碱汁或醋罐子里不会发生化学变化的。一九七一年,我在工厂劳动,突然有位工友失踪了,半个月后,清理强酸池,发现池底有一双塑料鞋底和一枚聚乙烯材料的像章,于是断定他是失足落“水”,连骨头都腐蚀得一干二净,像章却仍旧完好,只是少了那金属制的别针。
铝、铜之类的金属像章种类最多,图案最复杂的,据我收集到的即有六千种左右。单是外型,就有圆的,方的,椭圆的,长方的,五角的,六角的,七八九十角的,和说不上算什么形状的。而形象更五花八门:头像、半身像、全身像,侧面、半侧面、正面,青年、中年、老年,讲话、读书、阅兵……再配上松、竹、梅,日、月、星,红旗、天安门、延安城……还搭上少至二字、多至上百字的政治口号和语录,真是变幻无穷。
我所收集到的像章,最小的三毫米,最大的二百毫米,和菜盘子一样。一百毫米大小的尚能用别针配戴,再大,只好用绸带子挂在脖子上了。与盛世无缘的人们几乎都不相信那么大的铝饼是纪念章,以为是挂在墙上的玩意儿。幸亏我还收集了一些当年的纪录电影片,看完,你不得不信曾有那么多并非精神病患者的人挂着“菜盘子”上街。目前,升值率最高的是这类大像章。其实,大像章多数很粗糙,六十年代末以为大就是“无限崇拜”的表现,八十年代末相信大就是漫天要价的资本。
七十年代初,被用来造像章的人力物力、特别是精制铝材的浪费,终于使唯一能制止此事的毛泽东心痛了,他以诗人的气度说:“还我飞机。”从此狂潮渐息。到一九七一年冬,全国不再设计制造新的像章。一九七六年九月,北京证章厂替他制作了最后一种纪念章——小小的铝质头像。一个轮回静悄悄地结束了。
除去像章,我还收集毛泽东著作,特别是各种版本的语录。我不敢断言我收藏的像章种数最多,但却可以肯定我拥有丰富的“红宝书”个人收藏。
据统计,在毛泽东著作被视同“革命者的圣经”时,共有五十余种文字,五百余种版本,总印数约五十余亿册。这只是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在书店售出、送出以及以后销毁的数目,如果把各派红卫兵组织和“革命委员会”出版的算上,恐怕要有上百亿册。
列入正式统计的五百余种版本在世界上一些够规模的图书馆能够见到,所以我主要收集非正式的版本,林林总总,我收集了大约一千种。其中最小的开本是五百一十二开,和火柴盒一样大;最大的是四开,和报纸一般大。这些内容一律,开本和封面花样无穷的书比《圣经》的中文版本要多得多。
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歌”,是人们的又一项创造。所以,我也收集“语录歌”唱片。
原本我真没觉着“语录歌”这东西有多伟大,请教专家,是作曲家和音乐史学者告诉我:“可别小看那玩意儿,空前绝后。”前无古人的原因是,在此之前,凡是歌词必须是词,讲格律和韵调:若是专为歌曲而作的词,连什么声起唱,什么音收尾都有要求,否则唱不出效果。而语录歌的词根本不是词,是把毛泽东写的书,说的话一字不改地谱上曲子唱——前人想都不敢想。至于后无来者,自然也为这个,“后毛时代”的人,想都不要想,就“跟着感觉走”了。
据一位曾替语录谱曲几十首的人说,“语录歌”的曲子并不容易作。除去词无韵律,需要曲子去凑合歌词,语录里的“因为”、“所以”、“于是”之类的关联中介词汇很难谱曲,谱了曲子也不容易唱。但是“连文化大革命都能干,谱写语录歌算什么”——那位朋友很轻松地调侃自己“以为是献身的卖身生涯”。
作为“文革文物”被我收集到的“语录歌”唱片不足二百种,并不齐全。在一九六○年代末期之前,占据着中国大陆市场的是七十八转粗纹唱片,这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代的唱片在当时的西方市场早已淘汰,即使是新的,杂音之大、频响之窄亦不可与现时的唱片同日而语,更不用说和什么激光唱片比了。到七十年代,大陆开始出现密纹慢转的聚乙烯软片,这种在西方只供制作低保真度语言片之用的东西,被大量用于出版“语录歌”唱片。当时流行的是这些,我所收藏的自然也以此为主,只有很小的密纹慢转胶版片(所谓大碟)。这种“大碟”在那个时代是作为向世界革命人民传送精神武器制造的,不多。
读者可能猜得出二十年前的聚乙烯软片在现今唱出来有多荒腔走板(目前用立体声听“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恐怕根本不知道曾有过这种唱片),保存下来不太容易;同时会推想那些快转粗纹片收集、保藏该不太难,比照美国一位收藏家保存上千种、张张能唱的例子,曾发行过十几万张的“语录歌”唱片应能收集个齐齐全全才是。可惜的是当时造的胶木片,多数不是胶木片而是“纸基胶木片”,特别怕潮,稍遇水气便裂开、起泡。所以,除了现在能唱的不足二百张,我还有些不会唱的残片。正是这些“哑口无言”的破烂所显示的“目录”,证明我的收藏太不齐全。
影响了我收藏的另一原因是人的因素。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八年,两次在全国范围“清理、上交”,比较彻底地“处理”掉了语录歌唱片。这使得我这后来的收集者永远赶不上日本一家研究机构的语录歌收藏量。这家机构的目录上有大约四百种语录歌唱片,也不齐全,低于中国唱片公司当年的发行目录。如果以每种唱片录有语录歌八首统计,大约有三千段话被谱成了歌子唱,把异曲同词,重复录制之类的折扣打进去,至少也有上千个语录歌。细想想,这确实很轰轰烈烈的。
现在听“语录歌”当然很不顺耳,绝不是享受。但是,若有机会,千万不能错过,应该明白明白目前的中华儿女的半数曾唱过、听过些什么。
最少的歌词只有五个字:“要斗私批修”。照常规,歌的长度至少得有两分钟左右,否则不算歌,成了“唱口号”。于是,作曲者硬是在一个速度、调号、曲式中,将有限的音阶结合得错落有致,把五个字的歌词足足唱了三分钟还多。按说还能唱得更花哨的,但为语录谱曲是严肃的事,上滑音、下滑音之类绝不能用;而为照顾歌者的嗓子,太高或太低的音阶也不能用,唱足三分钟,已属难能可贵。
最长的歌词不能用字数算计了,必读的“老三篇”,整整唱一个晚会。这晚会的名目叫“毛泽东思想光辉照万代”,把《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这三章宏文大联唱,连“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和“白求恩同志一九四二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去五台山工作……”之类的话也谱了曲子
雄文四卷到底是有逻辑有文采的,需要在语录歌里打补钉的几乎没有。唯一的例外是关于造原子弹的话,歌词全文是“早在一九五八年六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连导言也谱了曲,确为罕见。
在“文化大革命”中另一位有资格被人唱“语录歌”者是林彪,歌子极少。林彪有野心,有些话说得太粗,谱成歌子唱出来,非常可笑。有一首进行曲速度的《战歌》唱的是:“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下定决心死在战场上,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简直完蛋得没天日了。
除去语录,毛泽东的诗词当然更要唱。在我收藏的唱片中有几十张——诗词总是要唱的,近年也有人谱了曲当现行歌唱,那曲子是摇滚乐风格的。“文化大革命”时的诗词歌可不敢如此。
我还收集各式的画像、照片和塑像;文革歌曲唱片;红卫兵的袖章,红旗和出版物;还有……看到“东京都人民向毛主席致敬团”的小旗,谁也不能再否认一九六八年的日本客人们竟用“致敬”的名目入境;听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录制的唱片,你只得佩服一九六七年的中国人会在一首歌里唱一百三十多次“万岁”。
文化大革命之后,出于“安定团结的目的和可以理解的原因”,大量的“文革文物”被销毁或被人们随手丢弃。待到改革开放的深入足以形成半地下的像章交易时,半数以上的像章和绝大多数其他“文革文物”已零落成泥碾作尘了。此时,“垃圾可以换钱”的一时小利使得残存的像章到了中间商手中后,就种数论,落入很有限的几位收集者之手的居多;就枚数说,则在观光者的“消灭”下日寡。再过几年,一些所谓“专藏”以私人出让的方式在海外上市,抬高了行市,中间商和收集者的注意力开始转向穷乡僻壤可能存在着的罕见像章,于是顺理成章地出现了赝品。一九八九年春,中间商们干脆哄抬他们有大量存货的几百个常见品种的价格,狠狠地赚观光者、外交官的外汇,把市场悄悄地移到了使馆区、大酒店和北京语言学院门外。中间商的作为,居然使得生活在大众传闻中的北京及其他几个大城市的人们以为海外有一个巨大的像章市场,竟有人想收购我的部分收藏去倒卖——巴金先生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如泥牛入海,可怜的“文革文物”却有行有市成了生意。
事情按着某一些中国人的逻辑发展到这一步,结局便很清楚——终于发生了两件事:在一些地方,取缔了所谓“文物的非法交易”;在深圳,某展览中心举办了“毛主席像章展览”。可惜的是,这个苦心积虑地摆在华洋杂处的开放特区的展览,只有一万余枚,四千余种像章。可悲的是,竟还要据此出版研究专著……
轮回就这样又一次干净利索地结束了。
在这个轮回里,我只能庆幸自己终究以心力和财力换来一些对未来的人们可能有用也可能没用的东西,并且叹息除了像章和“小红书”,别的“文革文物”还没来得及有份加入轮回,便随人下次了。
俱往矣,残阳如血。
残阳如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