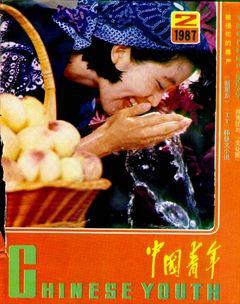论收费与罚款之随意
米博华
我这个人厚道,故连一位挺苛刻的朋友也慷慨的送我一副对子:“有索必酬,无求不与”,横批是:“大人大度”。“大人”一词让我脸红,“大度”一说则敢照收不误。如对机关分苹果之类的事我就从不介怀,堆大或堆小,红的或青的,一律马虎不计。与其为这等事苦恼,不如干点正经事。我信这个:节流莫如开源。
但我这回却为两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较“真”了。一次是去医院看病。举目四望,未见存车处,便把车掖到墙根儿。看完病出来推车,见一大汉走来:“交存车费!”钱掏出来,却没交给他。我觉得有必要让他澄清三个问题。一、如果存车是种营业性工作,他应该有营业执照。不能随便一个什么人,穿件破大衣,脖子上横套个“军挎”,张手就可以要钱。对此,他并不作回答。二、我付两分钱可以,但这钱是委托别人为我服务的报酬。我存车前并未看到他(更谈不上委托),为什么要交这不明不白的委托费呢?对此,他说放到这儿就是委托。我反驳道:“阁下是否交我五块钱?”他问:“凭什么?”“凭我给你看家了。”“可谁让你给我看家的?”“可谁又让你给我看车了?”我这样说,明显是胡搅蛮缠,但他要我二分钱的理由就真那么充分么?三、这二分钱虽少,但其中责任很大,而责任的区分是需要凭据的;譬如“存车牌”“存车卡”之类。现在北京地区存车简化了这道手续,是对存车人利益的默默侵犯。车没丢,你掏钱;车丢了,他不管。他可以毫不费力地缴你的械:“谁证明你的车存在我这儿了?”
第二件事是搬家。我把手推车放到胡同一侧,忽然从一杂货店闪出三五个人,说:“这得罚款五元。”有位说得罚七元。我说,掏钱不难,但也要说清两个问题:一、根据哪一级成文或不成文的法规,我把车放此处就定要罚款。他们雄赳赳地扛出一面牌子,上书“在此处放车,罚款五元。”这倒让我松了口气,原来此牌所本的是该店“政策”也。我说:“请各位先凑五元给我!因为贵店的烟囱经常熏我们。”“笑话,这又不是你的地盘。”我说:“那么何以证明胡同这块地方乃贵店之属?”二、此店罚五元之处分出自何典?他们无言以对,但态度依然蛮横:“我们就是这么定的。”“那么,因污染了民宅,扰乱了民生,各位首级搬家可否?”“你凭什么?”我答:“本宅就是这样定的。”
这是抬杠,不折不扣的抬杠。我得承认,道理并不会在我这一边,我之所以要抬杠,因为他们更无道理。”“凭什么?”他们也好,我也好,谁都找不到牢靠的凭据,信口雌黄而已。倘我随地吐痰被罚款,执罚的哪怕是老太婆,我也不能不认,因为那是市府的规定,和罚款人是否孔武有力无关。
在我看来,法不可能包罗万象,连手推车放到哪儿都作出明确规定。但你又不能不说社会生活的每个小环节上可以没有法的精神。
就说存车这件小事吧,我们不妨作个假设。如果我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是不是可以在闲来无事的时候,往最热闹的地方一站,伸手向所有把车存在马路上的人要钱?是不是可以收够了钱,把车子扔到一边,回家涮羊肉去?是不是可以突然宣布“今日存车费均提高至两角?”我想是不行的。开饭馆要有执照,摆地摊也要有执照,这执照不仅证明经营活动的合法,甚至还明确规定它的经营范围以及诸多细则要求。不然的话,会不会真有挂羊头卖狗肉的事也未可知。所以我说,存车事小,但较起真来也不简单。
另方面,我们的生活中还存在着类似“本店就是这样定的”土政策。我的一位亲戚按《婚姻法》规定的年龄完全可以“办事”了,但那个单位的领导就是不批。他们不否定我那位亲戚的年龄已经达限,却又说“我单位提倡男25女23岁。”咱们的生活中就是有这样的怪事:提倡并不是提议倡导之义,那意思你明白就是了。而咱们常说的“有法必依”,在很多地方也并不一定有“必须”之义。倡导也好,必须也罢,胳膊肘总是朝里拐;对我合适的就“必须”,对我不合适的就“不提倡”。结果好端端的法,到了有些人手里竟可以变成违法的避风港或保护伞。
我这次和存车的大汉及杂货店的一群较量了一回,觉得还是较一下真好。有人就爱拿“家法”充“国法”、治“国法”。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是“对簿公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