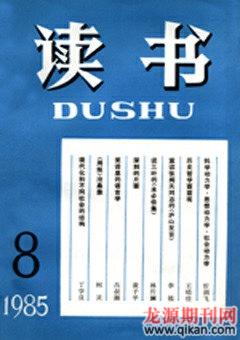对《燕赵悲歌》创作得失的思考
李慰饴
作为近几年兴起的改革文学的开拓者之一,蒋子龙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作家。每有新作,皆有口碑。实在是难得的幸运。当然,作家的勤奋、热忱,是理应得到公认的。但是,有些赞扬也往往引起我们的忧虑。我们相信作家的才华,但时尚和舆论有时也会以偏爱妨碍作家健全地发展。读了中篇小说《燕赵悲歌》(一九八四年第七期《人民文学》)和一些评论后,更感到有必要谈谈自己的看法,期望和评论者、作家共同讨论。
蒋子龙的这篇写农村改革、农民企业家的作品一问世,就引起了轰动。几乎所有的评论都认定它在思想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我在读了作品之后,却发现评论者赞扬的似乎并不是小说本身作为整体的思想艺术成就,而只是作品中那些表面的、效果性的东西,或者说是小说中薄弱的、粗糙的东西。
捧杀和抹煞都不是科学的慎重的态度。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丰富而又充满矛盾的文学现象本身。既不应放纵感情而褒贬,也不能囿于礼仪而模棱。
应当承认,蒋子龙的作品、他的以改革为题材的“开拓者的家族”创作系列,包括这篇《燕赵悲歌》,的确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这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
蒋子龙很敏锐,善于抓住现实中的问题,并竭力快速地用作品和读者拥抱。他比那些过于沉溺自我情怀的作家外向。他着意使作品及其主人公有一种果敢、豪放、自信的特点。正如时势造英雄一样,时势也造就人们的英雄观。时至今日,人们迫切需要气宇轩昂的男子汉,力拔山兮的大力士,叱咤风云、出奇制胜的智多星。我们曾经僵硬得太久了,后来又伤感得久了、缠绵得久了。群众期待狂飚式的风格和人物。同时,我们也深知,改革的愿望和呼声虽然十分强烈,改革的春风也在中国大地上劲吹,但盘根错节的羁绊以及各种各样的病毒霉菌仍然比比皆是。在这乍暖还寒的时候,新颖、泼辣本身就是一种兴奋剂和补药,引起希冀者的共鸣。何况蒋子龙是真诚和严肃的。他和他的主人公一起追求忧国忧民的思考,直率、奔放的风度和铿锵尖利的语言。从乔光朴始,他赢得了许多读者。
我们知道,作家和作品往往是会因其合于时宜而被厚爱的。《燕赵悲歌》和武耕新的形象在被蒋子龙及时地创造出来后,又被读者(包括评论家)接受,并按社会的需要再创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对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它所达到的社会功利目的,与它本身的艺术成就并不总是一致的。评价《燕赵悲歌》艺术上的得失,实际上取决于作品塑造的核心人物武耕新形象的成败。那么,该如何评价这一形象的文学价值呢?
武耕新——这个“老东乡一带几乎无与匹敌的新型农村领导人”的形象,从社会学的角度,从历史政治的角度来看,在客观上是可能的。第一,中国农村正在开始大变革,涌现了许多传奇式的改革者,包括脱颖而出、咄咄逼人的,“农民企业家”们。这是历史的现实性,是带有方向性的趋势。第二,我们虽然不必追寻武耕新和他的原型之间的“对数关系”,但是我们却可以相信作者是有真实依据的。且不说这个大赵庄是河北省某个农村的艺术再现,我们甚至可以找到形成文字的极为相近的材料。例如,《当代》一九八四年第三期上有一篇报告文学《西关明珠、光彩诱人》,如实报道了农民企业家李德海的事迹,写出了他的奋斗、山东牟平县西关大队的痛苦的过去和“西关明珠总行”的令人瞠目的今天。我们可以肯定《燕赵悲歌》的故事,并不是神话、幻想和乌托邦,是有现实真实性的基础的。
但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生活原型的存在,历史可能性的具备,并不是艺术真实本身的成立,更不是艺术水平的绝对保证。艺术的真实应该更完整、更细致、更生动,“从纷乱的生活事件、人们的互相关系和性格中,攫取那些最具有一般意义、最常复演的东西,组织那些在事件和性格中最常遇到的特点和事实,并且代之以创造成生活画景和人物典型。”(高尔基:《论文学》)而我以为,燕赵悲歌》的作者正是因为没有能在历史的真实和社会可能性的基础上,使自己的创作进入更高的艺术真实,因而造成了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缺陷。有人说蒋子龙的作品是“形象化的政论”,这个说法倒也准确,但这也正是作品的缺点所在,他首先是在写“政论”,不过是“形象化”的罢了。
作者笔下的武耕新是一个奇人,他给大赵庄创造了真正的奇迹,也给中国农村树立了一个令人眩目的榜样,正如李德海在西关大队所做的那样。他们都一样有哲学家的思想和开拓者的能力,都一样有过人的智慧和胆略。这些超人的品质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样杰出的人才是怎样生长、发展起来的呢?在李德海的经历中有清晰的脉络(苦难的童年、一定的文化基础、部队多方面的实践锻炼,还有十分勤奋的学习,等等),他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在武耕新这里,我们却没有看出他的巨大才能和知识赖以滋长发展的足够的根据。我们并不要求作者详细叙述主人公的行状,我们也不否认有些人可能具有某种潜在的素质。但是,性格和能力从潜在到迸发的过程,对形象的塑造来说,应该有可信服的基础和一个发展的层次。可惜,作者急于推出他的英雄——实际上是急于推出自己的理想,把武耕新描写为一个奇迹、一种抽象。对于这样的英雄,人们是难以真正了解的。
曾经是痛苦的武耕新,穷途末路、灰心丧气、一筹莫展的武耕新是怎样战胜自己的呢?他这个“缺乏高瞻远瞩的想象力,既无信心,又无规划”的人,“瞎眉合眼”成了“全村引路侯”的人,又是怎样实现了巨大的飞跃,突然认识了时代和经济规律的呢?请看,他“弓着腰,两腿象灌了铅,脚步踉跄、晃晃悠悠,行踪飘忽”,“象在梦中一样走着”,在“空气阴冷、夜色凄迷”中,象幽灵一样整整在村外转了三宿。他是绝望了,甚至想到寻短见。在这里矛盾是深刻的、真实的,如果作家能按照生活的辩证法去追踪、表现他的主人公的命运和精神世界,本来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人物。但是,作家没有这样做。矛盾的线索突然中断了:“突然浑身一激凌”,他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无所不通、无所不能、无往不胜的新人。用一个评论者的话来说:武耕新“涅
作者说“历史简直是用开玩笑的方式,把一个叱咤风云的新农民介绍到这个世界上来”。其实,这个玩笑不是历史开的,而是创作离开生活真实的结果。从这种玩笑般的恍然大悟开始,武耕新和大赵庄的神话般的发展,都象建立在沙滩上的高楼大厦。从武耕新的“涅
当然,作者有权跳过不愉快的某些细节,进行他认为需要的剪裁,却不应该忘记形象是要创造出来而不是在宣言中推出来。作者仅仅选取了几个生活片断进行细致的描写,虽然有些也可谓生动,但统观全局总有避重就轻之感。即使在这些片断中从侧面点出了武耕新等人在奋斗着,却也没有显示这种奋斗的艰难。更不用说有那种身历其境的震动了。矛盾在作品中被冲淡、被缓和。事实上的改革,而且在中国广大农村苏醒过程中,大赵庄这种比较孤立的改革,是不会象小说中设计得那样顺利的。一个改革者要战胜客观上的磨难和主观上的桎梏又是多么错综复杂,这些如果不能真实地反映出来,改革本身的必要性都会成为问题了。
作品中也写了斗争,这是以县委书记李峰为一方,以武耕新和县委副书记熊丙岚为另一方的斗争。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差不多是每一部写改革的作品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两方各以一个人物(或几个人物)为代表,唇枪舌剑、明争暗斗,也差不多自成规范。《燕赵悲歌》也不离这个路子。如能写得象作者本来希望的那样使人相信、令人感动、催人惊醒、给人新意,也未尝不能达到艺术的高度。可惜作品中所表现的斗争是静止的、平面的、概念化的,浅涉辄止,没有真正挖掘,形成层次和起伏,矛盾和斗争被归结为道德类型差异的缘由。矛盾的说明多于矛盾的运动;矛盾的“定格”多于矛盾的演化;矛盾的“位能”多于矛盾的“动能”。斗争并没有展开,解决得也过于容易。李峰虽然掌握很大的网络系统,可是对武耕新种种标新立异的创举,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的阻碍;熊丙岚的作用也是似有却无,在小说中没有恰当的调度。他被排挤、一笔勾销;调查组也派下来了。有点山雨欲来之势。然而山雨并没有来。全都无损武耕新和大赵庄一根毫毛,“我自岿然不动”。结果,调查组来得无力,去得无声,真是简单极了。这并不证明武耕新们的强大,不过证明李峰们实在称不起是什么对手。
在中国,实际上政治的权力曾经怎样被滥用而往往不可抗拒。即使最窝囊无能之辈有了它,也会有很大能量和几分威严。一个县太爷对一个农村大队,有着相差几个数量级的悬殊的优势,如果形成水火难容的两方,将有多么严重的较量是不难想象的。这个李峰仅仅只采取派一个调查组的行动,可说够宽容的了。就是这个调查组也未进行什么真正的调查,就落荒而逃了。在《燕赵悲歌》中,围绕改革的斗争却停留在起跑线上。何况,在实际生活中,即使没有李峰,没有调查组,也会有千变万化的阻力和磨难。社会变革,包括农村改革,引起的矛盾连锁是多方面的,本不应简化为一两个反对改革者的对抗和破坏。牵一发而动全身,大赵庄在那样的时期开始的改革,不可能在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里独立完成,它的每一项事业都要依附、作用于大的机体,包括各级机构、各个业务渠道、各种制度、各种利益的组合,更不用说广大的社会的习惯、心理和意识。要想前进,不跨越这无数道障碍是不可能的。不要说办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的工厂,就是一寸钢筋、一根钉子、一斤肥料、一升汽油、一张订货单……也休想轻易弄到手。也许并没有明显的营垒、公开的敌人、摸得着的打击和听得见的陷害,但是障碍、困难和问题是显然的。武耕新的本领在哪里?他有什么样的三头六臂?他是怎样建设他的天堂般的孤岛的?我们的读者是多么想从这其中来了解他。可惜,这一切都在剪裁下消失了。剩下的只是辉煌的业绩和无所不在的豪情!
人物的性格、命运,不是在运动中、在矛盾中去揭示、去发展,而是靠说明、靠旁白、靠内省。形象虽然涂上浓重的油彩,却无法掩盖实际的苍白。这样的人物虽然看来高大,实则空泛浮飘。作者借助于外在的、夸张性的所谓“个性化”手段,初看闪闪发光,近观则多为镶镀粉抹之举。和一些同类作品相似,改革者的武耕新能言善辩、出口成章,随时自有哲理警句,凡事都是无师自通,可说集各家百艺于一身。他还狂放不羁、有那么一点天马行空的味道。初读颇使人有新鲜之感,似乎不同凡响。但细思之则在峥嵘奇丽之间透着矫情和雕琢的痕迹。
的确,改革家可能有敏捷的思维、丰富的激情,也可能还有雄辩的口才。他有开拓者的勇气,也不免有些按世俗和守旧的眼光看去是越轨和非分的举止。但改革家同时也是社会生活本身孕育、脱胎而出的普通人。没有天生的改革家。改革的愿望和智慧,也不是面壁通灵或天书秘授而来,而是在实践中、甚至在挫折、打击和失败中获得的。真正的改革者应当是善于按客观规律推动生活不断改造和完善自己的人。我们一些作家把自已苦思冥想的连珠妙语和乖张行为一古脑儿堆在他们的英雄身上时,正反映了他们对自己描写的英雄的隔膜,对改革实际的生疏。
在《燕赵悲歌》中,写得较好的不是主要人物,而是武耕新的家庭成员们。由庄严的主题转入温情的世俗,作者才比较应手。人情相通,总能找到他易于突破的角度。几个家庭场景写得亲切生动、声息可闻。单独来说,不失为生花之笔。可惜这些描写与武耕新的性格发展,与他的奋斗史这一主线,联系不紧密,并且比例失当,反而冲散了、切断了主要的脉络。有因小失大、因次失主之感。
事情就这么不遂人愿。本来蒋子龙想写出风云变幻的社会变革,写出奋勇格斗的勇士,写他们“复杂的经历和精神上的磨难”,“写出人物丰富的、真实的、深刻的思想性格”,“悲也、壮也”。但是他没有达到,虽然他有可能达到。
生活能激励人思考、呐喊,但要把生活本身艺术地表现出来,又是一回事。《燕赵悲歌》的创作得失,给我们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