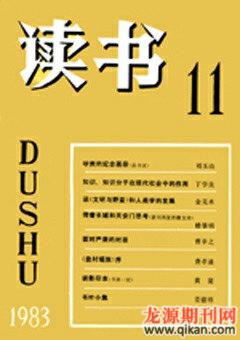《回忆亚东图书馆》序
王子野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已排出清样,编者寄给我看看并求作序。我早年同这家书店曾有过一段历史关系,对它的情况也知道一些,读了清样之后不能不说几句话,因此对编者所请欣然应命。
亚东从成立到停业恰恰是四十年,如果把它的前身芜湖科学图书社的历史也算进去,应该是整整五十年(一九○三——一九五三)。实际上作者的回忆正是这么算的。
亚东是一家很小很穷的独资经营的书店,五十年来先后进用职工不过五十来人。但它在我国近代新兴出版业中的地位却不能小看。它是在戊戌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这个时期中产生的,所以它的主人汪孟邹老人称它是“维新和革命的产物”。大体上可以这么说: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是它的草创时期,从五四到大革命是它的黄金时代,大革命失败后它就开始走下坡路。虽然它的后期出了一些坏书,影响不好。但从书后所附的出版物目录来看,好书还是占多数。其中特别是《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吴虞文录》等几种文集,一批标点整理的古典白话小说,五四以后涌现的一批新诗集以及蒋光慈等人的一批早期的革命文学作品曾经风行一时,有过很大的影响。因此应该肯定它对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作出了贡献。在《新青年》、《向导》周报以及其他一些进步刊物的出版、推销工作上也是很有成绩的。
作者的回忆比较全面,比较完整,每件事的来龙去脉都讲得清清楚楚,基本上真实可信。由于亚东与陈独秀、胡适、章士钊等知名人士有很深的关系,交往频繁,回忆中所讲的都不是仅凭记忆,而是有物为证,到处引用日记、札记、书信、文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这是很可宝贵的。特别是陈独秀的狱中来信一束,对研究陈独秀的生平是大有用处的。这批信大约有五十多件,前年据汪无功(汪原老之子)同志来信说:原件已在“文革”中丢失,无法寻找。真可惜。
书中多处讲到这些名人的遗闻轶事,也不是得之于道听途说,而都有比较可靠的根据。例如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当了北大校长,恳切要求陈独秀出来担任文科学长,几次登门拜访(当时陈尚在上海编《新青年》,因事去北京,住在旅馆里),有时候一早就来,陈还没有起床,蔡不让茶房去叫醒他,只让拿张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外等候。这件轶事是根据亲见者汪孟邹的回忆写的(见本书三五——三六页)。又如陈独秀与胡适关于“问题”和“主义”的争论,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争论都是根据作者本人的日记整理出来的(见本书九四——九五页)。
关于党在大革命时期的出版工作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但是过去材料很少。本书对上海的新青年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以及上海书店的情况以及迁移广州的经过都有较详细的介绍。特别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党的出版重心移到武汉,当时成立了中央出版局,先是张太雷同志担任局长,后由汪原放接替,(见本书一一六——一一七页)这段史实似是第一次披露于世。
出版史上还有许多问题过去都搞不清楚,这本书提供了许多可贵的材料。例如《青年杂志》是如何发起的,后来又为什么改称《新青年》(见本书三一——三三页);又例如《向导》周报是如何创办起来的(见本书七九——八○页),作者都引用日记材料作了较详细的介绍。此外还有五四时期几种《文存》的编辑出版经过,“亚东本”古典白话小说的标点、校读和出版情况,都是出版史料研究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在这部回忆录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因为标点白话小说的工作就是本书作者所做,所以讲得最清楚。有些事要是他不讲,谁也不知道。例如陈独秀为《儒林外史》写的序原来是汪原放写的,经过陈独秀修改了几个字就署了陈的名字发表了。这样的事如果作者不作交代,将来的版本学家就无法弄清。还有商务的《万有文库》,以前都知道是王云五搞的,读了这部回忆录才知道最初的倡议者是胡适,得到高梦旦和张元济的赞同才搞起来的(见本书九九页)。
总之,这是一部很有史料价值的书,研究近代革命史和出版史的人从中可以发现某些别处见不到的有用资料。还有这部回忆录的写法也别具一格,一忽儿引一封信,一忽儿引一段日记,一忽儿来一段对话,写得生动活泼,读起来引人入胜。
假如研究出版史有一个学习前人经验的目的,那么我以为在亚东这家小书店的历史中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对待出版工作严肃认真。这主要表现在出版“亚东本”古典白话小说上。亚东在和当时上海滩上搞“一折八扣”粗制滥造的书商作竞争中虽然吃了败仗,仍然坚持自己的谨严作风,决不为争夺市场而去追踪粗制滥造的恶劣行径。宁可卖不掉,也不能自毁声誉,这种精神是可贵的。第二,讲究工作效率,既要保证质量,又要加快出版周期。在这部回忆录中讲到,一部上千页的《水浒传》从标点、校读到付排,印制成书先后只有八个月,而标点、校读工作只有两个人担任。《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出版同样也是高速度。虽然速度这么高,却又能保证质量,这真不容易。鲁迅对这些标点和校正的白话小说作了公正的评语:“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作者和读者的。”一九四七年十月有位署名萧聪的评论家在《大公报》写了文章表扬“亚东版的书籍,校对特别仔细,错字几乎没有,版本形式也特别优美”。说亚东版的书籍错字比较少是对的,说没有错字不符合事实。我最近查阅《胡适文存三集》,就发现了错字,连标题的头号字也错了几个。校对完全不出错字是很难的。
三十年代初我在亚东工作的几年,对他们工作作风中的以上两条优点是深有感受的。也许是因为年轻时受了这种感染,所以毕生对出版工作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
亚东的主人汪孟邹老人由受维新思想影响面对新书业发生兴趣,同盟会革命来了,他又同情革命,从五四运动到大革命,他逐渐倾向同情共产主义。他说共产党好,但是他怕得很,不能成为共产党员。这是老实话。我在上海的几年,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汪原放是一位学者,经常埋头校读古书和翻译。这两位出版界的老前辈曾经给我许多有益的教诲,支持和鼓励我业余自学,介绍我读进步书刊,赢得我对他们的尊敬。汪孟老我从一九三四年离开亚东之后就再没有见过面。五0年北京召开全国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时在特邀代表中有他的名字,我多么盼望能在北京和他见面。可惜他以年老体衰,不堪旅途之劳,终于没有能来。同汪原老最后一次见面,是一九七八年五月我去上海参加科普创作会议时。这时他已达八十一岁高龄了。见面之下,高兴之极,晤谈三小时以上,毫无倦容,分别时还约定下次到上海再去看他,想不到两年后竟与世长辞,再也见不到面了。
在写这篇序文时不能不怀念这两位可敬的老前辈。
最后再交代一下本书前的“亚东图书馆编辑所同人合影”的来历。这张照片是我父亲保留下来的遗物,去年我的侄儿回绩溪老家去找来的。照片前排左起第四人程健行就是我的父亲。他是一个旧学很有修养的人,工作认真踏实。本书中提到他帮助汪协如校点《缀白裘》花了不少时间精力。我查《缀白裘》的《校读后记》的确是这么说的。可惜他在一九三○年春就去世了,年仅三十五岁。父亲去世后留下寡母和五个孤儿。我居长,才十四岁,最小的弟弟才三岁。不用说,我们家庭里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于是托人将我介绍到亚东去当学徒,这样我就在亚东工作了四年(一九三○年——一九三四年),在亚东四年的业余自学的生涯对我一生影响至大,它不仅使我学到了基础的文化知识,而且接受了革命思想,初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为我后来参加革命的思想准备奠下第一块基石。
书后的亚东图书馆同人名单中的程敷铎就是我的原名。改用今名是一九三八年到延安后开始的,姓王是随母姓。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