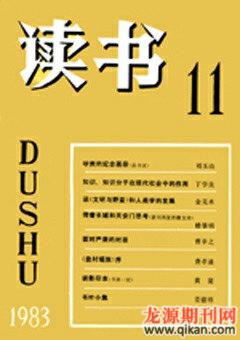从舒曼的感慨谈起
王德埙
十九世纪德国音乐家舒曼既有着成功的音乐创作实践,又有着丰富的音乐评论的经验。谁能说他“不懂音乐的本质”呢?然而对此感慨最深的却正好是他。舒曼面对着下面三个带着根本性的严肃问题,苦索冥思,不得其解:
音乐艺术的本质是什么?
音乐审美感受的性质是什么?
音乐的社会功能是什么?
回答这些难题是音乐美学这门社会科学的任务,而在舒曼的时代,音乐美学还处在草创时期。所以,舒曼的苦恼是可以理解的。按现代多数美学家的观点来看,音乐美学是一门边缘科学,音乐的本质问题从毕德哥拉斯起不断有人求索。
正当舒曼感慨万分之际,出生于捷克的二十九岁的音乐家汉斯立克亮出了“自律论”的旗帜,就音乐本质问题提出了答复,也对西方音乐史上过去的种种看法提出尖锐的挑战。他的《论音乐的美》故意显示了形式主义的偏向,认为“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运动的形式”,主张按音乐艺术的特殊性去探讨音乐的本质,从而正式确立了自律美学的基础。
新近出版的杨业治据增订版翻译的《论音乐的美》的中译本,为我们认识至今仍在西方音乐界有着相当影响的汉斯立克的美学观点,提供了便利。
汉斯立克对西方音乐美学中“感情论”的批评有其合理的因素。它使当时泛滥的浪漫主义音乐美学的一些庸俗无稽之谈趋于衰减。但由于他的极端的形式主义观点,却未能完全击中感情论的要害。
汉斯立克的美学观是不完整的,因为他缺乏历史的观点。他强调音乐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却忽略了在历史的长河中,音乐又是在同其他艺术,特别是在同音乐文学互相渗透,彼此融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从历史的观点看问题,音乐艺术同其他艺术的相关是绝对的,音乐同人类社会的相关也是绝对的,这正是他律美学中的合理的内核。汉斯立克直率地反对这一合理的内核,他片面地强调器乐,从根本上否定音乐的内容,这就为现代西方某些极端的器乐派别提供了美学依据。
汉斯立克毕竟是一位资产阶级的音乐家,他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识论,运用于音乐美学的研究,这给他带来了很大局限。例如,他对作曲家大脑机制的认识最终还是归因于“一种原始神秘的力量”,从而陷入了不可知论。但汉斯立克又是一位目光锐利的美学家。他最先在音乐美学研究中吸收当时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特别是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事实证明,这种方法的确有利于对音乐艺术作客观的考查。汉斯立克提出了有关音乐美学的一系列问题,有很强的理论色彩。他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无论哪一种音乐美学都无法回避他所提出的问题。尽管他的美学观点存在着种种缺点,但他对音乐自律性的阐述,毕竟为音乐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
在音乐美学这一领域,还存在着很多疑难问题,曾经使舒曼不得其解的三个问题,至今仍有待于我们深入探研。音乐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从哲学角度提出来的问题,也是音乐美学的基本立足点;音乐审美感受的性质,以及社会的人在音乐创作、表演和欣赏过程中的心理机制如何,这些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音乐心理学的角度去研究。音乐美学必须吸收心理学、特别是现代大脑科学的研究成果,并用以印证美学家从哲学角度研究所获得的结论;至于音乐的社会功能,则必须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加以考查。因为音乐艺术作为一种上层建筑,乃是人类社会的精神产品,人的“音乐之耳”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
(《论音乐的美》,〔奥〕爱德华·汉斯立克著,杨业治译,人民音乐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三月第三次印刷,0.8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