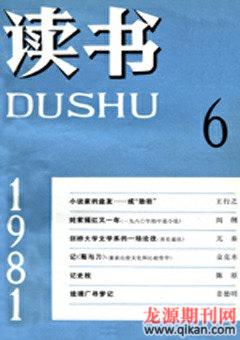古纸新篇
忍 言
潘吉星和他的造纸史研究
不久前,某大报上有篇署名短文:《考古发现否定了蔡伦造纸说》,介绍他们对先后出土的西汉灞桥纸、金关纸等进行了分析检验,结果证明“它们是真正的纸”,“从而否定了流传一千多年的蔡伦造纸说”。作为学术研究,这篇文章讲的方法和成果,都是应该值得人们尊重的,但作为一种学术动态,则早在十几年前,就已有人对灞桥纸作过检验分析,认为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历史上的蔡伦造纸说不可信。
此人是谁?他就是《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的作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潘吉星。还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他的第一篇研究造纸史的成果:《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就在《文物》上发表了。根据,灞桥纸;方法,分析检验;结论,真正的植物纤维纸。一切都和那篇文章讲的一样,不过这已是十六年前的事了。所以,那篇文章所谓“最近”云云,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不确的。
潘吉星一九五四年毕业于大连化工学院化工系。还在学生的时候,他就有志于化学史的研究,毕业后曾一度从事教学工作,化学史研究还只是教学余暇时的一种“副业”。一九六○年,他被调到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一九六二年他才将自己研究的主攻方向,集中到了中国造纸技术史方面。
造纸术始于何时?这是研究造纸史劈头碰到的问题。一千多年来,人们都是根据《后汉书》的记载,认为纸是东汉的蔡伦发明的。旧中国凡是产纸的地方,都有一座“蔡侯祠”。“蔡伦造纸”几乎成了妇孺皆知的历史常识了。一九三三年,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曾在新疆罗布泊地区的汉代烽燧亭遗址中,发掘出一片西汉古纸,它的质料经过鉴定是麻纤维,这样就动摇了“蔡伦造纸说”。但从那时以来,学术界不少人始终怀疑这一发现,再说它又只是“孤证”,所以传统“蔡伦造纸说”仅是摇而未动。一九五七年,西安灞桥又出土了一片西汉纸,一时引起了轰动,但人们却又把它当作“絮纸”,即丝纤维造的纸。这样,当潘吉星着手研究造纸史时,解决灞桥纸是否“絮纸”就成了重要的难点。科学的起步是问题,难点正是启导人们探索的诱饵,敢于知难而进,就会有希望成功。研究灞桥纸是否“絮纸”?潘吉星终于选择了这个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
选准了问题,第二步就是怎么解决它。潘吉星当时觉得,论证千言,不如亲手作一次化验。他用放大镜对灞桥纸作了物理结构和纤维形态的外观检验,接着又作了严密的显微分析,结果断定灞桥纸的主要原料,是大量大麻和少量
有人曾经怀疑,灞桥纸是不是真的汉纸?理由是它的出土,不是考古工作者发掘的,而原出土墓又发现有“扰土层”,这片古纸是否可能由盗墓人夹带进去的?潘吉星说,这样的“作伪”简直难以想象,因为果真这样,那作伪者不但要精于造麻纸的技术,还要对造纸史有深刻的研究,才有可能逃脱现代科学的技术鉴定。这一驳论揆诸情理是稳妥的,不过重要的还是从实物本身的形制来说明。为了破除某些人的疑虑,潘吉星后来又把灞桥纸同一九七四年武威旱滩坡出土的东汉麻纸作了比较,进一步证实它的原始性。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实物,就在一九七四年,甘肃金关又出土了两片汉纸,它是由考古工作者发掘的,经过分析化验,同样证明它是西汉纸。这样,造纸术始于西汉,终于成为学术界多数人承认的科学结论了。
造纸术起于西汉,传统“蔡伦造纸说”也就被推倒了。笔者以为这一结论的学术意义,不仅在于将造纸术发明时间提前了将近两个世纪,而且透过作者为了确凿无疑地弄清历史事实,体现了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这种探索精神不只反映在研究的最终成果上,同时还突出体现在治学方法上。“纸上得来终觉浅”,潘吉星研究造纸史是把考古发掘、文献考证、分析化验、模拟实验、土纸调查和技术探讨这六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这就改变了传统史学单纯依赖文献、迷信书本的研究方法。潘吉星是学化学的,分析化验当然是他拿手好戏,所以,最能说明他治学方法上有所创新的还是模拟实验。证明灞桥纸是西汉纸并不难,潘吉星一九六三年就已用化验方法解决了。但这种古纸实用的价值有多大?它是如何制造的?有哪些工艺过程?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所谓“技术史”也就无从写起了。可是,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文献,即使某些载籍上有片言只语,也大都讹错很多。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实地动手去做,再造出一种“西汉纸”来。一九六五年,潘吉星那篇推翻“蔡伦造纸说”的论文发表以后不久,他又到了陕西凤翔县的纸坊村。就在这个小山村里,他要进行一场探究历史原型的模拟试验。他先对民间作坊的造纸技术进行了细致调查,接着按古书蛛丝马迹的记载,结合调查的资料,拟定了十一种方案。一切准备就绪,于是潘吉星和几位老纸工一起动手干了起来。虽然是模拟原始的手工技艺,要求却非常严格。每一方案都要试验三至五次,每次试验都有十几道工序。事先,潘吉星要画图,事后要拍照,每个工序他都亲自动手,一面做,一面向老纸工请教,同时还要仔细揣摩每一工序的细微末节。经过两个多月的辛勤劳动,终于造出了一种理想的样品,经考古学家鉴定,它同西汉灞桥纸一模一样。模拟试验成功了,这是值得珍视的成功。直到如今,潘吉星手边还保存着一叠模拟纸,其中有一张上用毛笔写了六个字:“事实胜于雄辩”。是呀,科学贵在求真,历史重在事实。潘吉星的研究活动,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通过模拟实验,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潘吉星具体描述了汉纸造纸的工艺过程,写出了造纸史《汉代的造纸设备和工艺流程》一节。后来,他还设计了一幅技术操作的工艺流程图,请人画了出来,形象地再现了汉代造纸的情景。
解决了造纸术的起源问题,是潘吉星研究造纸史的突破点。从某种意义上说,造纸史还是一片未经深入开拓的领域,潘吉星没有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只是把它作为继续探掘的起点。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研究,潘吉星在中国造纸史的一系列问题上,都有所发现,提出不少的创见。譬如施胶技术和涂布技术,都是造纸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过去西方和日本学者曾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或者认为在唐代才出现,或者认为在南北朝就有了。这也难怪,他们所取的古纸样品仅限于唐代。这一方面,潘吉星比起国外学者有不少有利条件,他可以对大量年代确凿的汉、晋、南北朝和唐、宋古纸进行细致的检验和广泛的比较,认为这两项技术早在东晋时代就已出现,纠正了国外学者的结论。又如竹纸,过去有的记载说是起于西晋,潘吉星则对晋、唐、宋许多古纸进行了化验,结合文献及技术分析,认为它最早出现于唐、五代,到了宋代才被普遍使用。其他如水纹纸、还魂纸,甚至某些少数民族的造纸起源问题,潘吉星都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位科学家曾经说过,科学上的进取精神,就是不安于书本上给你的答案,而要尝试发现与书本上不同的东西。作为学术观点,潘吉星的某些结论可能还有商榷的余地,但它所反映的不因袭旧说,不苟同权威的治学精神,则是值得肯定的。
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潘吉星发表了有关造纸史专题论文九篇,研究了现代造纸工艺学、古文字学、植物分类学,翻阅了正史、各种地方志、类书、别集、笔记、碑帖、考古发掘报告以及近人各种论著,还有日、英、德、俄、法等语种的国外文献,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在这样深厚的基础上,潘吉星经过深入系统地研究,写出了《中国造纸技术史稿》,一九七九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史稿》一出,很快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反响。国内不少通史,根据它对造纸术起源的论述作了相应的修改。美国的钱存训博士写信向潘吉星表示,他与李约瑟合著的《书于竹帛》一书,也将按潘的研究改变原来关于造纸起源问题的观点。一九八○年,《中国造纸技术史稿》就被译成了日文出版,没有多久,又出版了另一种日译本,有的章节还被日本学者译成了英文。
为什么一本专门史著述的出版,竟有如此强烈的反响?笔者觉得,恐怕是由于这件事意义,不只是一般学术上的影响。
造纸术的发明,是我们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三百多年前,培根曾经说过,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起了改变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的作用,没有一个帝国,一个教派,一个显赫人物,能与这三种发明在人类事业中产生的力量和影响相比。培根没有说到纸,这是因为那时英国普遍使用的还是羊皮纸。如果晚一个世纪,培根说这番话,恐怕不会忘记还有造纸术发明。当然,这是笔者的一种揣测,但也不是毫无根据。如果把培根的话移用来评价纸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不也是同样适用吗?但我们这样做时,千万不能按照阿Q的逻辑,一切都用“我们先前也曾阔过”来自我陶醉。造纸术的发明诚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后来我们却大大地落后了。不但纸的制造和运用远远不如别人,甚而连它的历史研究,很长时间也都是国外的学者遥遥领先。不过,炎黄子孙绝不是天生的不肖,只要我们急起直追,现代文明之巅是一定可以登攀的。即以造纸史的研究说,《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目前已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造纸史的专著。日本大阪市立大学佐藤武敏教授,肯定了此书有四大特色,而且特别指出,和过去欧美、日本学者个别的、概论性的研究不同,《史稿》是对中国造纸史系统的全面的叙述,认为“这种尝试在世界上尚属初创”。被西方认为是研究中国印刷术和造纸史第一流学者的钱存训博士,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印刷和造纸)的“导言”中,列举了迄今各国论中国造纸史的著述后说,《史稿》“这部书是用一切语文写出的论中国造纸技术论著中最为全面和最为详尽的研究”。能否这样说,《史稿》的出版,标志着造纸史研究这一领域已由我们中国学者夺得“金牌”了呢?
潘吉星还写过肖莱马传记,这是迄今第一部系统介绍这位德国著名化学家的专著;五十年代,他还曾从达尔文著述中摘录了一百多条中国科学史材料,对照国内外的许多文献逐条进行考证,追寻出这些史料的原始来源,从而肯定了达尔文在创立进化论过程中,曾从中国古代科学遗产中吸取了许多思想资料。六十年代,他还和别的同志一起主编过《世界化学史》。对《本草纲目》、《天工开物》这两部古代科学著作,他也进行过专题研究。虽然这些研究大都偏重于科学技术,但对理论问题,潘吉星也有浓厚的兴趣。记得他曾同笔者谈过,研究自然科学史,只有注意理论问题,才能总结出有益的规律教训。这话是意味深长的。
科学的昌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科学和社会不是天生一对兄弟,什么时候都会携手并进的。一位美国科学史家曾经说过:“科学总是革命的和非正统的,这是它的本性”。社会往往由许多凝固的网结一层一层地包裹着,科学只要有所发展,都会或多或少扭动这些网结,冲击着人们固有的价值观念,以致社会在很多时候都充当了科学前进的路障。这从中国科学史中可以得到最好的证明。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科学技术的许多领域,历史上我们民族所取得的成就,一直是西方所望尘莫及的。可是这些成就却在西方被融化到现代科学的熔炉中,成了他们傲视我们的一种资本。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哪里?单从科学技术本身无法说明,只有从历史上的社会制度中才能找到。著名的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假使说中国并没有产生一个亚里斯多德,我认为,那是因为阻碍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发展的那些抑制因素,早在中国可能产生象亚里斯多德那样的人物以前,就已经开始起作用了。”封建专制制度是阻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位西方老人真是一语破的。翻一翻二十四史就会发现,历来科学家都是被列入“方技”,科学只是当作“术数”,和占卜、算卦当作一类的。那时的儒生,他们读书是为了通向仕进之途。落拓的时候,有些人还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傲人,一旦钻进了宦门,就把自然科学知识鄙薄为旁门邪道。我们在为祖先的辉煌成就惊叹不已的时候,不能忘了这个历史事实。
科学探索是没有止境的,潘吉星下一步还有番更大的雄心。今年,他应美国华盛顿斯密森研究院之约,将赴美作专题研究一年。五个月前,他曾对《文汇报》的一位记者说过:要采用红外技术、电子扫描、电子显微、光谱质谱分析等现代技术,对古代造纸术的全过程作更加精细的考察,进一步修改《史稿》;并决心搞出各个时期纸的结构图,来解决文物真伪鉴定的难题。同时,他正准备对中国四大发明的另一发明——火药史——作一番研究。
潘吉星的这个设想,只是一个普通中国学者研究工作的远景规划,但我们却可以从中受到一种鼓舞,只要有更多人的埋头苦干,探索不止,那中国科学技术的复兴昌盛不是指日可待吗?
一九八一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