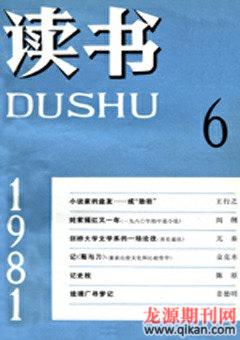学海扬帆七十春
乐 齐
在上海南京西路一座洁静幽雅的公寓里,我拜访了著名古典文学家、语言学家,复旦大学教授郭绍虞先生。郭老已经是八十八岁的高龄了,又身患多种疾病,但他依然寸阴不废、分秒必争。他潜心治学、著书立说,取得了累累硕果。这位在书林学海辛勤耕耘了七十多个春秋的老学者,回忆起自己漫长而曲折的治学生涯,禁不住感慨万千,浮想联翩。
一八九三年,郭绍虞生于苏州。从小就酷爱文学,喜欢写诗,中学时代就曾组织过诗社“东社”。十六、七岁时,正赶上辛亥革命。中学还没念完,因家境清寒,只能半途辍学,在乡间当小学教师。稍后,他来到上海,一面在中、小学教书,一面在书局当编辑。他任教的尚志小学,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出版中心商务印书馆的子弟学校;因为这个缘故,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商务印书馆的藏书楼——涵芬楼丰富而珍贵的藏书。时至今日,这座名扬中外的藏书楼在郭绍虞的脑海里还留着鲜明、亲切的印象。
在这里年轻的郭绍虞划出了扬帆启航的第一桨。他如饥似渴地读着,抄着,搜寻着,思考着。一九一六年,他的处女作《战国策详注》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接着,第二本书《清诗评注读本》也问世了。这时的郭绍虞只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不久,他又应邀在上海爱国女校和东亚体育学校任职,专授“中国体育史”课程。可是,当时还没有一本系统的体育史专著,给教学带来困难。郭绍虞下决心自己编写一本中国体育史。凭借着涵芬楼的藏书以及自己对古代文献的谙熟,他旁征博引、援古证今,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体育项目细加考定,于一九一八年写出中国第一本体育史专著——《中国体育史》,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三万字的专著一出版,立刻受到欢迎,曾多次再版,收入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
本来,按照计划,郭绍虞还要写一本《中国体育学史》,作为《中国体育史》的续篇,专门论述“古人关于体育之学说”。可惜,后来因为环境变化,这本有关中国古代体育理论的著作未能写成。
在现代一些青年人的心目中,郭绍虞只是一个学者。其实,早在五四时代,他就是文坛上的活跃分子了。
郭老告诉我说:“五四过后不久,我离开上海来到北京,在北大旁听,参加了有影响的‘新潮社,并成为《晨报》副刊的特约撰稿人。五四时期,国难当头,青年们大都有股正气,积极向上,进取心特别强。他们一方面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反帝反封建;一方面抓紧时机,脚踏实地,发愤读书,以充实自己。当时,我要听课、写文章,还要见缝插针,奋发学习英文、日文、德文。”
正因为郭老勤奋好学,他在文学、哲学、史学等一些领域内,都有建树。他翻译过日本高山林次郎的《近世美学》,武者小路实笃以及其他日本思想家、作家的作品。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杜威在北京大学做的《思想之派别》的讲演,就是由胡适口译、由郭绍虞笔录整理发表的。他还译介过欧文、圣西门、傅立叶和拜伦、莎士比亚、别林斯基等外国哲学家、文学家的传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一九年底,他在《晨报》上发表了《马克思年表》,这是中国现代出现较早的介绍马克思生平的材料。在学术研究上,他的长篇论著《艺术谈》从一九一九年七月开始,在《晨报》上连载达半年之久。当时还是新文学运动的初期,现代文艺理论还处于草创阶段,这样一部十多万字的艺术论著的出现,无疑是很有历史价值的。目前,郭老正在对这部六十多年以前的旧作进行整理。在创作方面,郭绍虞写过一些新诗。一九二○年十月,瞿秋白等人作为《晨报》驻俄国记者前往苏联,郭绍虞很羡慕,专门写了《流星》一诗赠别。一九二二年文学研究会编印的郑振铎、朱自清等八人诗集《雪朝》中,就收有郭绍虞的诗作十六首。
“听说那时你与郑振铎交往很深,你们是怎样认识的?”我问。
郭老说:“到北京不久,郑振铎就来找我。他当时是铁路学校的学生,正与瞿世英、瞿秋白、耿济之等一起办刊物。我们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一九二○年下半年文学研究会酝酿成立时,我住在北大旁边的春台公寓,我们之间的过往更加密切。我记得,我们时常在紫禁城的护城河边散步,商讨办刊物、成立文学社团的事,还不止一次在耿济之家里开过会。”
谈起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也是最大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成立,虽然事隔整整六十个年头,但有些片断还能依稀辨记。作为这个现代文学史上深有影响的文学组织的发起人之一,郭老告诉我,在该会的十二个发起人中,眼下大多数已经谢世,还健在的只有叶圣陶和他二位了。这些人当时多数都是他的挚友,只有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三人年纪较大,是社会名流。他们所以能与一般穷学生一起,成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主要是因为这些爱好文学的青年把他们视作长者先辈,对他们加以尊敬倾慕的结果;而他们的声望和地位,也确实给这个文学团体增添了号召力和权威感。
文学研究会的筹备工作,郭绍虞是一直参加的。只是到了一九二一年初,他接受了济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聘请,离京南下,未能参加成立大会。在济南作了短期逗留,不久,他又成为美国教会学校福州协和大学第一任国文系主任、教授。虽然远离京沪,但他与文学研究会的联系仍然十分密切。他的许多作品不断见于会刊《小说月报》、《文学旬刊》和《诗》等刊物上。而文学研究会的另一个发起人、他青少年时代的密友叶圣陶,也在他的介绍下来到福州协和大学任教。
在大革命中,文学研究会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很多会员转向政治活动。一九二七年初,在大革命的高潮中,郭绍虞由河南的中州大学来到革命中心武汉,在第四中山大学工作。他与当时在武汉的沈雁冰、吴文棋、樊仲云、傅东华、孙伏园等人一起,组织了“上游学社”,办了刊物《上游》。这个团体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文学研究会的骨干分子,可以说是文学研究会在大革命时期派生出来的一个“外围”组织。在研究文学研究会的发展史和郭绍虞的个人经历时,这个团体是不能不提到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郭绍虞应冯友兰的邀约,到燕京大学当教授。用他自己的话说,开始钻进了“象牙塔里,故纸堆中”。象文学研究会中一些成员,如他的老朋友朱自清、俞平伯等一样,他走进了书斋,过着学者生活。三十年代是郭绍虞著述的丰收时期,他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撰写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陶集考》、《宋诗话辑佚》(上下集)、《国故概论甲辑》(文艺理论部分)、《近代文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特别是写于一九三四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连同出版于四十年代的下册,是中国比较完备系统的文学批评史专著。书内材料丰盈,引证博繁,体例完备,立论新颖,被学术界视作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权威之作。
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多事之秋。在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在国难时艰一天深似一天的岁月,郭绍虞不可能也不愿意过着真正超脱政治的隐居生活。他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更是一位富于正义感的爱国教授。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北京的时候,他表现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可贵的民族气节。在完全背瞒着他的情况下,日伪华北作家协会把他列入了委员会名单。郭绍虞发现后立即去信责问,当事人曾为此回信道歉。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敌伪报纸上的这一条消息,他还受到“审查”。费了好大的周折,郭老翻箱倒箧,从纷杂的书物旧稿堆中寻拣出当年的这封道歉书信,才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那时,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不要说研究学问,就连起码的生活条件都难以维持。尽管日伪大学有着优厚的薪金,但他也丝毫不为所动。宁愿守着清苦的日子,也不肯向敌人屈膝,同流合污。因此,有些人曾用“唱高调”来讥讽他;他当即写了题为《高调歌》的诗,作为回答,表明自己的爱国心迹和对敌人的蔑视。后来,实在被逼得走投无路,只能携家带口,南走上海,到开明书店做了编辑。
日本投降后,郭绍虞任同济大学中文系主任。虽然他已经是一个知名的大学教授了,但因政治腐败,物价飞涨,加之学校常常欠薪,为了养活一家之口,他不得不同时在光华、东吴、之江、大夏等好几个大学兼课。特别使他难以容忍的,是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他接触了地下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积极投身于民主运动的洪流中去。他参加了党领导的“大学教授联谊会”,担任了这个组织同济大学分会的主任。因此,他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列入了黑名单,遭到通缉。即使在这种动荡险恶的环境里,郭绍虞从来也没有放下案头的书,没有搁下手中的笔。四十年代,除了完成《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以外,还出版了《学文示例》、《语文通论》、《语文通论续编》等几部学术著作,为中国文学和语言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这位在旧社会苦苦挣扎奋斗了半生的教授,当旭日在中国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已经年过半百了。躬逢盛世,他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上海刚解放,陈毅市长就接见了包括郭教授在内的一批文化界著名人士。一九五四年,他重病缠身,组织上关心他的健康,为他精心治疗,又送他到风景幽美的华东疗养院休养一年,使他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一九五六年,他加入了共产党,从此,生活目标更加明确。亲眼看到了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一天天走上了繁荣富强的大道,他从六十年的生活经历中深切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感情更深了。郭绍虞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评价分析中国古代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正如他在一首诗中说的那样:
犹是当年笔一枝,
却从旧说换新知。
固应学问无穷境,
真信马恩是我师。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他多次修改自己的旧作,新的著作也一本本产生出来。写于五十年代末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就是试图以马列主义文艺观点来阐述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他还校释了《沧浪诗话》,辑注了《诗品》。一九六二年,他主编了《中国历代文论选》,这套篇幅浩繁的巨著,收集了从上古到近代两千多年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论文,成为高校的基本教材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极有价值的参考书。
十年浩劫中,郭绍虞也身受迫害。就是在这种时候,他还是不忘写作,准备修改《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四人帮”喧嚣一时的“儒法斗争”声中,他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愿歪曲历史真相,只能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修改暂时搁笔,而开始撰写《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本色。
当“日出冰消”“风吹雾散”的春天来到时,郭老虽然年已老迈,但仍然精神振奋,每天努力工作,即使卧病在床,还要倚靠床头,膝上放块木板,照常写作。在最近三四年内,郭老又修订和撰著各种著作十几种,近二百万字。他为原来主编的三卷本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充实内容,又与助手一起,增添新篇,增订成四卷本;还另外编辑付印了一种适合大学生用的一卷本的“简本”。他的《宋诗话考》考证了宋代多种诗话的作者、版本、内容体例和优劣得失,是研究宋代文学理论的重要史料。五十八万字的长篇巨制《汉语语法修辞新探》是郭老数十年研治语法修辞的结晶之作。他周密地论证了汉语具有的简易性、灵活性和复杂性的特征,着重说明了汉语语法必须结合修辞的特点,指出过去汉语研究和教学将语法和修辞分割开来的错误,希望语法界一反旧时的语法研究方法,来一番改弦易辙。这些新颖而大胆的论点,已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愿尽吾学,高下定程,先后竣工;愿毕吾生,星长拱北,川长向东。”这是郭绍虞先生在一首《自述》诗中表达的心愿。在经过了七十多年的长途跋涉之后,在他的治学计划一一“竣工”之后,他又在忙着选编自己的文集。这位可敬的老人还在继续不断地努力,创造新的精神财富,要把自己最后一份力量献给祖国和人民。
记郭绍虞教授
在上海南京西路一座洁静幽雅的公寓里,我拜访了著名古典文学家、语言学家,复旦大学教授郭绍虞先生。郭老已经是八十八岁的高龄了,又身患多种疾病,但他依然寸阴不废、分秒必争。他潜心治学、著书立说,取得了累累硕果。这位在书林学海辛勤耕耘了七十多个春秋的老学者,回忆起自己漫长而曲折的治学生涯,禁不住感慨万千,浮想联翩。
一八九三年,郭绍虞生于苏州。从小就酷爱文学,喜欢写诗,中学时代就曾组织过诗社“东社”。十六、七岁时,正赶上辛亥革命。中学还没念完,因家境清寒,只能半途辍学,在乡间当小学教师。稍后,他来到上海,一面在中、小学教书,一面在书局当编辑。他任教的尚志小学,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出版中心商务印书馆的子弟学校;因为这个缘故,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商务印书馆的藏书楼——涵芬楼丰富而珍贵的藏书。时至今日,这座名扬中外的藏书楼在郭绍虞的脑海里还留着鲜明、亲切的印象。
在这里年轻的郭绍虞划出了扬帆启航的第一桨。他如饥似渴地读着,抄着,搜寻着,思考着。一九一六年,他的处女作《战国策详注》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接着,第二本书《清诗评注读本》也问世了。这时的郭绍虞只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不久,他又应邀在上海爱国女校和东亚体育学校任职,专授“中国体育史”课程。可是,当时还没有一本系统的体育史专著,给教学带来困难。郭绍虞下决心自己编写一本中国体育史。凭借着涵芬楼的藏书以及自己对古代文献的谙熟,他旁征博引、援古证今,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体育项目细加考定,于一九一八年写出中国第一本体育史专著——《中国体育史》,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三万字的专著一出版,立刻受到欢迎,曾多次再版,收入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
本来,按照计划,郭绍虞还要写一本《中国体育学史》,作为《中国体育史》的续篇,专门论述“古人关于体育之学说”。可惜,后来因为环境变化,这本有关中国古代体育理论的著作未能写成。
在现代一些青年人的心目中,郭绍虞只是一个学者。其实,早在五四时代,他就是文坛上的活跃分子了。
郭老告诉我说:“五四过后不久,我离开上海来到北京,在北大旁听,参加了有影响的‘新潮社,并成为《晨报》副刊的特约撰稿人。五四时期,国难当头,青年们大都有股正气,积极向上,进取心特别强。他们一方面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反帝反封建;一方面抓紧时机,脚踏实地,发愤读书,以充实自己。当时,我要听课、写文章,还要见缝插针,奋发学习英文、日文、德文。”
正因为郭老勤奋好学,他在文学、哲学、史学等一些领域内,都有建树。他翻译过日本高山林次郎的《近世美学》,武者小路实笃以及其他日本思想家、作家的作品。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杜威在北京大学做的《思想之派别》的讲演,就是由胡适口译、由郭绍虞笔录整理发表的。他还译介过欧文、圣西门、傅立叶和拜伦、莎士比亚、别林斯基等外国哲学家、文学家的传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一九年底,他在《晨报》上发表了《马克思年表》,这是中国现代出现较早的介绍马克思生平的材料。在学术研究上,他的长篇论著《艺术谈》从一九一九年七月开始,在《晨报》上连载达半年之久。当时还是新文学运动的初期,现代文艺理论还处于草创阶段,这样一部十多万字的艺术论著的出现,无疑是很有历史价值的。目前,郭老正在对这部六十多年以前的旧作进行整理。在创作方面,郭绍虞写过一些新诗。一九二○年十月,瞿秋白等人作为《晨报》驻俄国记者前往苏联,郭绍虞很羡慕,专门写了《流星》一诗赠别。一九二二年文学研究会编印的郑振铎、朱自清等八人诗集《雪朝》中,就收有郭绍虞的诗作十六首。
“听说那时你与郑振铎交往很深,你们是怎样认识的?”我问。
郭老说:“到北京不久,郑振铎就来找我。他当时是铁路学校的学生,正与瞿世英、瞿秋白、耿济之等一起办刊物。我们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一九二○年下半年文学研究会酝酿成立时,我住在北大旁边的春台公寓,我们之间的过往更加密切。我记得,我们时常在紫禁城的护城河边散步,商讨办刊物、成立文学社团的事,还不止一次在耿济之家里开过会。”
谈起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也是最大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成立,虽然事隔整整六十个年头,但有些片断还能依稀辨记。作为这个现代文学史上深有影响的文学组织的发起人之一,郭老告诉我,在该会的十二个发起人中,眼下大多数已经谢世,还健在的只有叶圣陶和他二位了。这些人当时多数都是他的挚友,只有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三人年纪较大,是社会名流。他们所以能与一般穷学生一起,成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主要是因为这些爱好文学的青年把他们视作长者先辈,对他们加以尊敬倾慕的结果;而他们的声望和地位,也确实给这个文学团体增添了号召力和权威感。
文学研究会的筹备工作,郭绍虞是一直参加的。只是到了一九二一年初,他接受了济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聘请,离京南下,未能参加成立大会。在济南作了短期逗留,不久,他又成为美国教会学校福州协和大学第一任国文系主任、教授。虽然远离京沪,但他与文学研究会的联系仍然十分密切。他的许多作品不断见于会刊《小说月报》、《文学旬刊》和《诗》等刊物上。而文学研究会的另一个发起人、他青少年时代的密友叶圣陶,也在他的介绍下来到福州协和大学任教。
在大革命中,文学研究会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很多会员转向政治活动。一九二七年初,在大革命的高潮中,郭绍虞由河南的中州大学来到革命中心武汉,在第四中山大学工作。他与当时在武汉的沈雁冰、吴文棋、樊仲云、傅东华、孙伏园等人一起,组织了“上游学社”,办了刊物《上游》。这个团体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文学研究会的骨干分子,可以说是文学研究会在大革命时期派生出来的一个“外围”组织。在研究文学研究会的发展史和郭绍虞的个人经历时,这个团体是不能不提到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郭绍虞应冯友兰的邀约,到燕京大学当教授。用他自己的话说,开始钻进了“象牙塔里,故纸堆中”。象文学研究会中一些成员,如他的老朋友朱自清、俞平伯等一样,他走进了书斋,过着学者生活。三十年代是郭绍虞著述的丰收时期,他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撰写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陶集考》、《宋诗话辑佚》(上下集)、《国故概论甲辑》(文艺理论部分)、《近代文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特别是写于一九三四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连同出版于四十年代的下册,是中国比较完备系统的文学批评史专著。书内材料丰盈,引证博繁,体例完备,立论新颖,被学术界视作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权威之作。
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多事之秋。在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在国难时艰一天深似一天的岁月,郭绍虞不可能也不愿意过着真正超脱政治的隐居生活。他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更是一位富于正义感的爱国教授。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北京的时候,他表现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可贵的民族气节。在完全背瞒着他的情况下,日伪华北作家协会把他列入了委员会名单。郭绍虞发现后立即去信责问,当事人曾为此回信道歉。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敌伪报纸上的这一条消息,他还受到“审查”。费了好大的周折,郭老翻箱倒箧,从纷杂的书物旧稿堆中寻拣出当年的这封道歉书信,才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那时,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不要说研究学问,就连起码的生活条件都难以维持。尽管日伪大学有着优厚的薪金,但他也丝毫不为所动。宁愿守着清苦的日子,也不肯向敌人屈膝,同流合污。因此,有些人曾用“唱高调”来讥讽他;他当即写了题为《高调歌》的诗,作为回答,表明自己的爱国心迹和对敌人的蔑视。后来,实在被逼得走投无路,只能携家带口,南走上海,到开明书店做了编辑。
日本投降后,郭绍虞任同济大学中文系主任。虽然他已经是一个知名的大学教授了,但因政治腐败,物价飞涨,加之学校常常欠薪,为了养活一家之口,他不得不同时在光华、东吴、之江、大夏等好几个大学兼课。特别使他难以容忍的,是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他接触了地下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积极投身于民主运动的洪流中去。他参加了党领导的“大学教授联谊会”,担任了这个组织同济大学分会的主任。因此,他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列入了黑名单,遭到通缉。即使在这种动荡险恶的环境里,郭绍虞从来也没有放下案头的书,没有搁下手中的笔。四十年代,除了完成《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以外,还出版了《学文示例》、《语文通论》、《语文通论续编》等几部学术著作,为中国文学和语言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这位在旧社会苦苦挣扎奋斗了半生的教授,当旭日在中国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已经年过半百了。躬逢盛世,他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上海刚解放,陈毅市长就接见了包括郭教授在内的一批文化界著名人士。一九五四年,他重病缠身,组织上关心他的健康,为他精心治疗,又送他到风景幽美的华东疗养院休养一年,使他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一九五六年,他加入了共产党,从此,生活目标更加明确。亲眼看到了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一天天走上了繁荣富强的大道,他从六十年的生活经历中深切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感情更深了。郭绍虞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评价分析中国古代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正如他在一首诗中说的那样:
犹是当年笔一枝,
却从旧说换新知。
固应学问无穷境,
真信马恩是我师。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他多次修改自己的旧作,新的著作也一本本产生出来。写于五十年代末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就是试图以马列主义文艺观点来阐述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他还校释了《沧浪诗话》,辑注了《诗品》。一九六二年,他主编了《中国历代文论选》,这套篇幅浩繁的巨著,收集了从上古到近代两千多年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论文,成为高校的基本教材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极有价值的参考书。
十年浩劫中,郭绍虞也身受迫害。就是在这种时候,他还是不忘写作,准备修改《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四人帮”喧嚣一时的“儒法斗争”声中,他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愿歪曲历史真相,只能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修改暂时搁笔,而开始撰写《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本色。
当“日出冰消”“风吹雾散”的春天来到时,郭老虽然年已老迈,但仍然精神振奋,每天努力工作,即使卧病在床,还要倚靠床头,膝上放块木板,照常写作。在最近三四年内,郭老又修订和撰著各种著作十几种,近二百万字。他为原来主编的三卷本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充实内容,又与助手一起,增添新篇,增订成四卷本;还另外编辑付印了一种适合大学生用的一卷本的“简本”。他的《宋诗话考》考证了宋代多种诗话的作者、版本、内容体例和优劣得失,是研究宋代文学理论的重要史料。五十八万字的长篇巨制《汉语语法修辞新探》是郭老数十年研治语法修辞的结晶之作。他周密地论证了汉语具有的简易性、灵活性和复杂性的特征,着重说明了汉语语法必须结合修辞的特点,指出过去汉语研究和教学将语法和修辞分割开来的错误,希望语法界一反旧时的语法研究方法,来一番改弦易辙。这些新颖而大胆的论点,已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愿尽吾学,高下定程,先后竣工;愿毕吾生,星长拱北,川长向东。”这是郭绍虞先生在一首《自述》诗中表达的心愿。在经过了七十多年的长途跋涉之后,在他的治学计划一一“竣工”之后,他又在忙着选编自己的文集。这位可敬的老人还在继续不断地努力,创造新的精神财富,要把自己最后一份力量献给祖国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