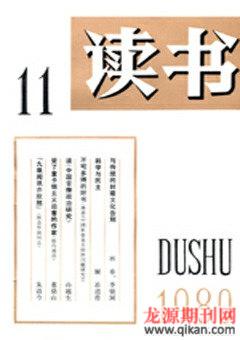大胆讴歌人性的优美
章仲锷
刘心武的《如意》可以说又是闯“禁区”的,所以我也用“人性”这个一向被认为“烫手”的字眼儿作题目,来谈论他的这篇新作。我之敢讲“人性的优美”,而不冠上“革命的”等字样于前,是因为这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分析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时,对其女主人公玛丽花所作的肯定:“尽管她处在极端屈辱的境遇中,她仍然保持着人类的高尚心灵,人性的落拓不羁和人性的优美”;“她之所以善良,是因为她不曾害过任何人,她总是合乎人性地对待非人的环境。”①这些赞语,我看在一定意义上也适用于《如意》的男主人公石义海。这是个极普通、极不起眼、甚至有些浑沌愚昧的老校工。他受人歧视,被认为“麻木不仁”,即使按“中间人物”的标准,也是偏乎后进的;然而,作者真实地写出了他的善良本质与不善的环境的矛盾,使我们不能不产生共鸣,爱上这“质朴到极点的厚实晶澈的灵魂”,讴歌那“升华着纯真的人性美”。
“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照说,“人性”这个字眼儿本不致“烫手”的,可是,打从文痞姚文元刚发迹时起(大约是一九五六年吧),“人性论”的帽子就满天飞;人性、人情、同情心、人道主义等,统统奉送给了地主资产阶级,仿佛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压根儿就六亲不认、七情皆无似的,这简直荒谬可笑到了极点!粉碎“四人帮”,思想得解放,人们对人性问题重新进行探讨,试图破除这个早在十九年前就为周总理批驳过“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的“禁区”;但不管是谈“人性的异化”或“人性的复归”也好,是肯定不同阶级有共同、共通的人性或主张只有阶级性也好,多是理论上的争辩诘难;在创作实践上,也许余悸犹存吧,有的虽写人情、人性,却躲躲闪闪,忌讳出现这几个字;象《如意》这样通过艺术形象,对人性“作真实的赤裸裸的描写”(高尔基语),敢于明确地赞颂它是“使整个人类能够维系下去,使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美、更纯净的那么一种东西”,恐怕还是头一篇吧。我想,既然现在谁都拥护“人民大众的人性”的提法,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歌颂体现在普通劳动者石义海身上的这种“人性”呢?说刘心武的新作有所突破,首先就是指的此点,这对破除形而上学、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肃清极左思潮和公式化、概念化的流毒,是大有意义的。而从作者自身的创作历程看,也许将会成为他步入一个新阶段的分野和起点。
《如意》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小说中的一句话,写的是“两人各执一柄如意而终于没有如意的爱情”。这“两人”,一个是弃婴出身、“打小伺候洋鬼子”的老校工石义海;一个是“天潢贵胄”的末代“格格”(清朝贝勒之女)金绮纹。而且是迟暮的爱情(他们正式约在天坛“搞对象”时都已年近半百),乍一听,也许有点儿罗曼蒂克和传奇色彩。其实,作者笔下的这双男女,都是很平常的角色:男的是个文盲、粗人,还是罗圈腿;女的无依无靠,在家糊纸盒、折书页子过活。他们的“阶级觉悟总提不高”,男的还信鬼,甚至胡涂到“竟然对‘天下乌鸦一般黑这样天经地义的话也提出异议”;女的则“放不下多罗格格的臭架子”,还有抽好烟、喝好茶的嗜好……总之,他们既不高大,也不完美,相反,还有些窝囊,存在着缺陷,而且按照那十年通行的“斗争哲学”和“阶级分析”法,特别是石义海的言行,简直近乎“出轨”甚至“反动”。比如,他竟给“小将们”打死的、淋在雨中的资本家的尸体盖上塑料布,还给被“专政”进行强劳的“牛鬼”们送去绿豆汤;金绮纹竟拒绝那个曾抛弃了她的丈夫、一个加拿大籍富商接她团聚的请求,煞景地破坏了“一则中加友谊的佳话”的诞生,也令人大有不识时务之感。但是,作者正是通过这些娓娓道来的细节,有如抽茧剥笋,使我们逐步地了解到,石义海这原被看作“是一个最简单最落后最不屑人们一顾的、最无味乃至最无价值的角色”,“然而在这混乱疯狂、离奇反常的世态中,他却独能保持自我,不为汹涌恣肆的狂潮左右……”,而他与金绮纹的“用了整整三十年,才终于坐到一张桌子的两边”的爱情,尽管“欢乐是渺小的,哀痛是卑微的”,但“也应当在人类的文明史中占据应有的位置”。
我在此所以笨拙地复述小说并不曲折却很感人的情节,富于哲理的议论,无非是想表明,作者在进行可贵的探索,试图刻画我们伟大民族的“芸芸众生”,描绘平常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歌哭,展示他们质朴却不简单、纯真而又丰富的灵魂。石义海的性格,若按常规分析,是如此难以捉摸。他正直善良,虔诚地尊重自己所爱的人,信守誓言,无限同情无辜的受害者;他有自己的处世哲学,反对“人整治人,人糟践人”,认为“不存心害人的人就是好人”,“人对人不能狠得过了限”;他“不昧良心”,不说瞎话,敢于在批斗“走资派”的大会上,于众目瞠视中,取下党支部书记脖子上坠着的铁饼。这一切,是全然无法用阶级感情和抽象的定义来判断的。对比“蒜苔”那一类“脑瓜灵活”的主儿,更显出了他的“人类的高尚心灵”。就是一些同他接近的人物,如“我”、老曹和葛大爷等,也都对他的内心向往和执着的爱情追求,不甚了了;连那个“比较通人情”的基层支书老曹,虽然能记着这个单身汉的“棉被胎子该换换了”,却“全然忘记了,他也是一个需要女人的男人!他需要一个小小的家庭!一种最普通最琐屑的人生乐趣!”作者所探索、发掘的这出悲剧的主题,就在于他从人物之间的矛盾和鲜明对比的关系中,揭示出石义海在十年浩劫那“非人的环境”里,独能“合乎人性地”保持自我的金子般的心。“不能那么糟践人”!这是正值妙龄的金绮纹,当年在废园里初遇受着非人折磨的石义海时的一句话,后来竟成为他们暮年互相怜爱的感情基础和共同信念。难道这不是通篇小说所呐喊出的最强音吗?它反映了作者的道德信念和他对人类良知、“人性的优美”的讴歌。
《如意》在内容上的突破,也会带来艺术表现上的新鲜感。多年来,由于对典型化原则片面、机械的理解,把所谓概括集中变作“拔高”,取舍、缀合成为拙劣的图解,公式化、概念化盛行,待到“四人帮”肆虐,“三突出”、“高于生活”登场,这种歪曲更导致了瞒和骗的反现实主义文艺统治文坛。纵观现代文学的画廊,堪称典型的艺术形象寥寥可数。而象阿Q、祥林嫂、吴荪甫等人物,也都是无法用划阶级成分和套某些公式所能分析清楚的。“惟其真实,才有生命力”,我以为恢复和发扬现实主义的传统,必须汲取教训,首要的还是在人物塑造上去矫饰、勿“拔高”,在反映、开掘生活上不回避矛盾,不伪造、图解。《如意》在这方面是有长处的。它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人物,大都带着热腾腾的汗腥、土气,披露出赤裸裸的真诚的心,使我们能窥见人物性格的复杂丰富,内心感情的纷纭多变,觉得象那么回事儿,挺有人情味儿。作者没有刻意地编故事,设置人物也不搞分类法,平衡正反两方面的比例。他的取舍、提炼更多地体现在小说的矛盾结构上;对人物的抒写,则力求如实地反映“本来的形象”,而非“批判的变态”(这两句引文是借用马克思在分析玛丽花时的用语)。即使这真实是严酷的、触目惊心的,也不回避,楞给“拔高”。正如鲁迅说的:“倘有取舍,即非全人,更加抑扬,更离真实。”②在我们如过眼烟云,看惯了那么多体现“阶级本质”和“生活主流”的人物像之后,接触到这样的艺术形象(应该说这样的形象,近几年在作品中开始多起来),的确耳目一新。
其实,这篇小说在手法上,倒是颇为“守旧”的,既没有“意识流”,也没有时空的倏忽跳跃;篇首是一段引子,篇末尾声呼应,中间大倒叙里套着小倒叙,时间跨度长达六十年,那左一个右一个的“请想象……”的倒叙开端,甚至还显得有些呆板;文字的锤炼也不足。但是,在布局谋篇上,自有其独到的匠心。例如如意这个信物的深藏不露,就始终牵系着读者,取得强烈的悬念效果。而状物的情景交融,议论的要言不烦,人物语言的十足“京片子”味儿,以及对一些人们“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信笔点染,锋芒所及,发人深思,都可以看出作者在艺术上的不断成熟和提高。
话说回来,目前“人性”这个命题,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探讨,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提倡“争鸣”和作多方面的实践尝试。刘心武的《如意》,迈出了值得重视的坚实的一步,但愿不是绝唱,而是先声,让更多的艺术形象,放出更加绚丽的人性的光彩!
(《如意》,载《十月》杂志一九八0年第三期)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215—217页。
②《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其余引文均见《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