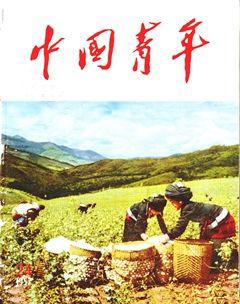雪印/献给:把青春献给北大荒的共青团员们
周纲
黑龙江蜷缩着无声地睡去,
完达山闭着眼在寒风中战栗,
夜,张开了巨大的黑翼,
把北大荒紧紧裹在怀里。
暴风在空中打着呼哨,
雪花在空中飞旋狂跳,
凄历尖峭的寒风里,
夹着一声声饥饿的狼嚎。
天空撕碎了,土地冻裂了,
连老牧人最勇敢的猎狗,
也畏怯地躲在灶下,
不敢出外奔跑。
就在这被风雪封锁的道路上,
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姑娘,
她身上背着沉重的药包,
大步地奔跑着,显得那么匆忙。
狂舞的雪花迷住她的双眼,
刺骨的寒风冻得她浑身打颤,
一阵阵暴风迎面扑来,挡住她,
像一块又厚又重的门板。
突然一阵猛烈的风暴,
一下将姑娘刮倒,
她挣扎着爬起来,
爬起来又被风暴推倒。
她只好顺着雪道往前爬去,
喘着气,低着头,躬着腰,
借着那一线微弱的雪光,
辩认前进的小道。
她翻过光滑的土坎,又爬上小桥,
猛抬头,看见一丛丛野兽的蹄印,
这新的杂乱的蹄印告诉她,
饥饿的狼群正在把充饥的食物寻找。
姑娘停下头,不敢前进了,
狂风里,又传来一声声狼嚎,
她睁大眼惊惶地四外搜索,
从口袋里摸出了削铅笔的小刀。
“要是……我,我碰上了,
那……那该是多么糟糕。”
黑暗中她似乎看见一群饿狼,
正对着她张牙舞爪。
姑娘的身子一下缩紧,
闭着气,不敢出一点声音,
风呵,像发现她已经胆怯,
一阵比一阵刮得更凶更狠。
往前?每一步都有生命的危险,
退后?十里外又没有一户人烟,
刹那间,姑娘的心呵,
像揉乱了的一团丝线。
“万一……可是我才十九岁呀,
在人生的道路上,还有长长的路程,
难道我就看不到自己的第二十个春天,
也不能去作我应该做完的事情?”
姑娘的头低垂下来,
焦愁地闭上了眼睛,
但那紧抱在胸前的药包,
却突燃触到了她的咀唇。
呵!今晚在那呻吟的病房里,
有多少同志在忍受着煎熬,
说不定院长和医生还在村口,
站在风雪里,等我等得心焦。
后退?!这想法多可耻呀!
她好像觉得脸上在发烧,
而那耳边的一阵阵风声呵,
也似乎在大声地对她嘲笑。
难道我报名到北大荒来的决心,
只不过是用肥皂吹起的泡泡?
难道共青团员竟不如一支小鸟,
懦弱地匍伏在地上,不敢飞高?
姑娘忽地从雪堆里挺起身来,
揉掉睫毛上的冰屑,
迎着那狂暴的风雪,
踏着狼群的脚印向前奔跑。
上坡,她背着药包往上爬,
下坡,她抱着药包往下滚,
像一个吹不散的雪球,
在茫茫的雪原上翻滚。
而在这一片荒漠的土地上,
她好像看见北大荒未来的面貌,
电灯闪着光,麦穗点头笑,
康拜因的喧响,代替了呼啸的风暴。
旷野里,再也听不见凄厉的狼嚎,
打麦场上,手风琴奏着轻快的曲调,
夜晚,每家人都把收音机扭开,
听毛主席建设共产主义的报告……
她奔跑着,仿佛觉得——
风变小了,狼叫得也不可怕了,
黑沉沉的夜空呵,
似乎变得明亮了。
她奔跑着,仿佛一张新打的跌犁,
在北大荒无垠的雪原上,
为春耕刻下了最初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