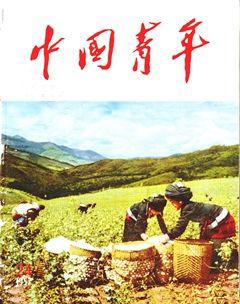新时代里的寄生草
石光
一个什么样的秘密
1955年9月,“人民文学”编辑部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干部。据说是因为犯了错误,由作家协会人事科调出来,暂时安放到“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当时正搞肃反运动,大家都很忙,即使最爱打听内幕的青年,也顾不上去了解她犯了什么错误,人们也很少有时间和她交谈;她自己呢,除了把自已打扮得很入时,有时对着别人作着微笑外,也很少主动和大家接近。
但是,秘密终是会揭开的。在一个晚上,这个女干部带着一种神秘的表情,向同宿舍的一位同志吐露了她的问题。
“………我不是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只是个生活问题。我和我爱人的感情不好,爱上了别人。……那个人非常好,是个作家,很有名气,又有钱。你也认识他的。……他对我好极了,非常爱我,常常夸奖我年轻,聪明,热情。和他结婚会很幸福,也会很有钱。……”
接着她就要这位同志为她“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还特别加了一句:“我只和你一个人说了呵!”
其实,就在她和这位同志倾诉秘密的前几天,就巳经和另外的人说过了。之后不久,她又告诉了好几个人。无论对谁,都同样要叮嘱为她保守秘密,也有一句:“我只和你一人说了呵!”
人们听到这个“秘密”本身,固然感到气愤,但更气愤的,是她对“秘密”所持的态度。她对自已生活上所犯的错误,看起来并没有半点悔改之意,相反地,还以此在人们面前炫耀;她是在回忆着这段肮脏的“爱情”,作着未来的美梦。
这个女干部是谁,爱上她的又是什么人,他们俩干了些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请听下面分解。
诗人、金钱炫惑了眼和心
这个女干部名字叫高瑛,是1955年随爱人由东北调到北京中国作家协会的。她没有什么专长,但又不愿到“文艺学习”作登记信稿的工作,作家协会人事科只好把她暂时留下作些登记干部卡片的工作。从地方到中央,由小机关到大机关,从接触小作家到接触大作家,对于这个出身于小商人家庭,本来就有向上爬的思想的高瑛来说,是有很大诱惑力的。虽然她到北京不过几个月,但是,她的思想却在迅速地变化着。
恰巧在这年七月,高瑛因工作上需要了解作家的稿费收入,她和艾青有了接触。在第一次帮助艾青计算版税时,诗人的声誉、金钱和艾青对她表露的感情,就炫惑了她的眼和心。在他们接触的整个过程中,艾青向她宣扬的是自己的名誉、地位、金钱。艾青告诉她,他曾去法国留学,到过20多个国家,写过很多诗,出版过不少诗集,他的诗享有国际声誉。有多少女人追求他、爱慕他:有音乐学院和戏剧学院的学生,有某女作家的妹妹,有……,这些人对艾青的诗爱得快要发狂了。艾青还让高瑛看了些青年寄来的充满着歌颂和崇拜的信件。高瑛越看心里越对艾青有好感,再加上艾青一再夸奖她年轻,聪明,热情……,又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高瑛:“人生不会有几个年轻的时候,浪费了太不值得。”说高瑛,“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生活得好一些”。艾青还不用高瑛开口,一伸手送给她一百多元。这些意想不到的事使她昏眩,使她迷醉,她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幸运儿。她向艾青渲染了自己和爱人的不和,声称:“当关系破裂到一定的时候,离婚的一切顾虑都需要打消的。”就这样,高瑛不顾自己是有夫之妇,不顾自己已有了两个孩子,她完全倾倒在艾青的名气和稿费上,她不知羞耻地满足艾青的兽性要求。
“一面是庄严的工作,一面是荒淫与无耻”。高瑛就是这样在全机关忙于肃反的时候,瞒着组织,瞒着丈夫,不断地和艾青通奸,走上了腐化堕落的道路。
嫌弃丈夫只是一个小小科长
高瑛和艾青搞得火热的时候,也就是高瑛和自己的丈夫关系急趋恶化的时候。她提出了离婚的要求,组织上没有同意,她就向爱人采取了猛烈攻势,在家庭中制造裂痕,扩大矛盾。她对爱人冷嘲热讽,说什么“当个小小科长就满足了,什么东西也写不出来,你完了。”公开骂爱人:“你为什么不离婚,我对你一点留恋也没有,我不愿回这个门,看见你就像看见最讨厌的东西。”她常常深夜不归,而且搬到外屋去住。
说高瑛和爱人的感情原来就不好,那是假话。他们是在1950年结婚的,她的丈夫是东北一个省文联的秘书长兼创作部长。当时,在高瑛看来,找到这样一个爱人是够理想的,他是领导干部,又能创作,比她所在的文工团里那些提琴手和歌唱家要好得多。所以在未结婚前,当那个秘书长生病住院时,她不辞辛苦一天到医院看望几次,从而肯定了关系。但是当爱人调到北京以后,只不过担任个“小小科长”的职位,又没有什么著名的创作,而她自己有机会接近更有名望,更有地位和金钱的人,自然,爱人在她眼里就逐渐减色,最后成为“讨厌的东西”了。
高瑛的这种羡慕虚荣,追求享受的思想不是偶然的。还在她读中学的时候,作商人的父亲就常对她说:“你好好读书,只要我活着,一定设法叫你出国留学。”高瑛的理想是“做一个不平凡的人”,“想创一番事业”,“能够使人佩服和羡慕”。但是她又不刻苦,不踏实,不论是学习和工作都是飘飘浮浮,总想耍点小聪明或是借着别人的力量出名得利。在东北鲁艺文工团时,她时而对提琴手表示好感,说:“我的志愿就是学提琴”;时而又和搞音乐创作的同志亲近,表露自己想当歌唱家或是诗人的心情……。但是,很遗憾,她的志愿都没有实现,她和文联秘书长结婚以后,也是平平凡凡。而现在,她居然结识了艾青,她认为这回可有出头之日了。在她给艾青的一封信里,她写道:“我是一个很喜欢文学的人,也曾有过作文学工作的幻想,这幻想,一天天一年年的加深了,如今有了你,多少年来的幻想有了实现的希望,你将成为培植我写诗的土壤。”其实,高瑛并没有认真读过几本文学书籍,更没有下过什么功夫。她不过是想借艾青的力量使自已成名,至少也可以借艾青的“光辉”来照亮自己。更何况,艾青已为她未来的生活作了周密的打算,买了房子,结婚后搬进新居,要雇炊事员,打杂的,还有褓姆……。高瑛一想到自己不久就要由一个平凡的女人一跃而为享有一切的诗人夫人,就飘飘然了,恨不得把她的“幸运”向全世界宣布。
高瑛的无理取闹和反常态度,不能不引起她爱人的怀疑。在爱人的一再追问下,高瑛以离婚和让爱人替她保守秘密作为交换条件,向爱人坦白出来。但是在几次谈话中,她完全是一种炫耀和无耻的态度。她夸耀艾青对她如何体贴,有“丰富的诗人感情”;艾青如何有钱,他们怎样安排了今后的生活。只要爱人答应离婚,艾青出多少钱都是可以的,她自己的东西什么也不要,孩子也由艾青负担。……
这种丑恶的事情,当然不能令人容忍。她的爱人向组织和法院控告了。高瑛和艾青都受到了国法、党(团)纪的制裁。为了避免他们的接触,高瑛暂时调到“人民文学”编辑部。
四菜一汤的幸福
受处分不久,高瑛和爱人正式离婚了,而且很快地就和艾青结了婚。紧接着她拒绝了组织分配的工作,在十二月向组织上递了辞职书。显然,组织处分和法律制裁并没有把高瑛挽救过来,她仍然按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道路走下去,最后居然要求脱离革命队伍。组织上为了再一次挽救她,党总支的同志找她谈过话,让她认真考虑自己的前途;也告诉她,她还年轻,参加工作也有好几年了,虽然犯了错误,只要下决心改正过来还是有希望的。这些善意的劝告也像严厉的处分一样对她不起任何作用。她声言自己有条件不工作,艾青完全能够把她培养成女诗人。她让保姆领回了七百元退职金。以后,她既不参加原单位团组织生活,也不顾把团的关系转到街道上去,团费由别的同志为她垫交,而且声称过两年满25岁就要退团了。就这样,她拒绝组织上的帮助离开了组织,离开了革命队伍,非常得意地开始了她逍遥自在的贵妇人生活。当同志们对她提出批评时,她甚至无耻地认为别人是在羡慕她、嫉妒她的幸福。
高瑛所谓有条件可以不工作的含意,就是她不用劳
动可以靠艾青过舒适的寄生生活。而且觉得和艾青结了婚,似乎自己也就成了名诗人而身价百倍了。在碰到作协和“人民文学”的同志时,她总装作煞有介事地告诉别人:“我很忙,要写诗,要为艾青处理稿件,要招待外宾。”
说她忙倒是真的。她忙着享受,忙着上百货大楼,逛东安市场,选衣料,做衣服;她忙着为艾青摆设古董,布置房间,忙着陪艾青游山玩水,忙着为艾青打扮自己。她希望自己长得更丰腴一些,因为艾青喜欢这样。她还忙着找一切机会向别人炫耀自已挥金如土的豪华生活。她写信给东北的同志说:我幸福极了,每天吃的是四菜一汤。告诉“人民文学”的同志说:“我幸福极了,艾青对我很体贴,为了叫我喜欢,他什么都听我的。”她夸耀有一次和艾青到上海、杭州,住国际饭店,一天仅房钱就花十八元;她还请别人去参观她的衣橱,炫耀一下艾青为她买的五光十色,春夏秋冬的服装。好心的人劝告她应该节省一点,她满不在乎地回答:“怕什么,艾青有的是钱。”
她的确也写过一点诗。例如有一次当她送艾青上飞机以后,就写了几句:“飞机飞上了天空,我的心也随着飞上了天。”她还写过一首把艾青比作松树的诗:“我看见了你,就想起了云。……云是幻变的,你是长青的。”这些言之无物的东西,她居然还向别人吹嘘,说人民日报向她要诗,“诗刊”也要,好像做了诗人太太,自己也就成为名诗人了。
荣誉,金钱,“四菜一汤”,这就是她的人生哲学和幸福观。在人们看来,她不过和艾青的古董、花瓶、金鱼一样,是艾青生活中的点缀品、装饰品,她自已却满足得浮上了天。什么组织、革命和工作,在她脑里早已消失尽净了。
这就是他们真正的爱情
高瑛和艾青都说,他们是追求真正的爱情。艾青还把高瑛比作安娜·卡列尼娜。在高瑛给艾青的信里曾经说过:“只要由于我们的结合,能够给人类多贡献出点有益的东西,能够给家庭生活带来幸福,别的都没有什么考虑的。”看起来,好像他们还是为着什么共同理想和事业而结合的。其实戳穿来看,这不过是一种粉饰。他们是在互相利用来满足私欲。高瑛追求的是名诗人的荣誉和物质享受,艾青要的是年轻的女人。结婚后,这种利害关系就慢慢暴露出来了。
艾青自已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已上中学,两个男孩也是小学生了。高瑛把他们看作眼中钉。一位著名的外国诗人到艾青家作客,高瑛打扮得花枝招展地招待外宾,而艾青的雨个男孩子却因为衣服破旧,被锁在屋里。大女儿爱听音乐,屋里有个收音机,高瑛硬逼着孩子把收音机搬到自已屋里,其实她根本放着不用。艾青因为怀念第四个孩子玫玫(和艾青原来的爱人生活在一起)而写了一首诗:发表后,高瑛在一怒之下,把玫玫所有的照片都撕毁了。三个孩子受不了她的虐待,曾经联名向艾青请愿,要求到妈妈那儿去。就在今天十月,为了给两个男孩子添制棉衣,高瑛还大发雷霆,把屋子里的摆设打得个落花流水。高瑛对待别人的孩子是如此无情,但是对于自已的那个孩子,却“要把她打扮成为女王一样。”其实,她并不是真爱这个孩子,当她从前和艾青谈情说爱的时候,也曾把孩子一个人丢在宿舍里摸着空床叫妈妈,或是在星期六晚上让孩子在托儿所空等。像这样灵魂里浸透着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也难怪连母性的感情都没有。
为了银行的存款,争存折,她和艾青也经常争吵,有时甚至打架。
就在对孩子对家庭经济这两个问题上,已足够说明他们的结合,完全是建筑在赤裸裸的金钱和私欲关系上面。
做了艾青的反党助手
尽管他们在生活上有着利害关系和矛盾,而在许多政治观点上,高瑛完全是夫唱妇随,艾青说什么,她就应什么。她伴随艾青奔走于江丰、吴祖光的反党小集团之间;她用电话通知右派分子姚芳藻,说丁玲很委屈,很可怜,让姚去看丁玲;当组织上批判江李时,她劝告江丰应该放聪明点,“胳膊扭不过大腿”;她私自把作家协会送给艾青的有关批判艾青的整风简报压下,怕艾青看了后受刺戟。艾青的反党言行揭露后,她还帮助艾青“回忆”,替艾青写检讨。艾青照着她写的检讨念,因此,在庄严的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上,出了“在我生孩子以后”的笑话。
从她生活上犯错误以来,团组织对她进行了仁至义尽的帮助和教育。但是她对组织的态度是抗拒的,对立的。谁批评她,她就远离谁,谁同情她,她就把谁当作朋友。就在她破了艾青的反党助手以后,团组织还没有放弃对她的希望;在党组织批判艾青当中,团组织也对她进行了批判,为她先后开了六次总支和支部大会,希望她能痛改前非,回头是岸。然而她仍然执迷不悟,在她自已的检讨中,一方面强调自己是受了艾青的影响,辨不清是非,同时又处处为艾青辩护,想把艾青的反党言行,推到其他反党分子身上。对她自已的错误并没有什么认识和悔改之意。就在今年十一月里,团支部最后讨论她的处分,组织委员通知她开会时,她还无所谓的说:“我不来了,你们以后把处分的决定告诉我好了。”
高瑛已经被清洗出共青团组织了,而且也被伟大的时代所抛弃;高瑛可能在将来从她由羡慕虚荣、追求享受而走向腐化堕落的道路中猛省过来,也可能继续堕落下去。但是对于一般爱慕虚荣追求生活享受的青年来说,高瑛的毁灭确实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