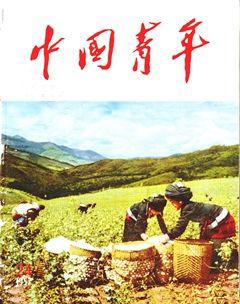妻子的工作
谭韶华
十月三日,我收到妻的一封来信。信上告诉我一个兴奋的消息:她找到了工作,希望我星期六到她那里去玩。读完信,我高兴得像小牛犊一样跳起来。多少个白天黑夜,为妻的工作焦虑着,多少次,我为她没找到工作对她生气,责骂她“无能”、“没出息”。妻呢,也常为自已不能工作感到羞愧痛苦。但每当我生气时,她总是安慰我:“韶华,忍耐一下吧!我会找到工作的。”想不到今天她果然找到了工作。从此我们可以不必再为钱米问题吵嘴了,这怎么能不叫我高兴呢!但是,妻找到的是什么工作呢?她信上并没有告诉我。
星期六晚饭后,我乘车来到妻的住处——七星岗。我刚下汽车,就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呀!你到底来了!我到这里来了三次,每次都等了一点多钟……”在路灯的照耀下,我清楚地看见了妻那付挂满笑容的脸。她今天穿着一件红花色的解放服,小辫上还特意扎了双水红色的蝴蝶结,配着她那细小的身材,显得格外年轻好看……。我真想上前去拥抱她。可是,看到她手上还抱着一个约一岁的娃儿。她见我呆呆地盯着她,羞涩地说:“紧站着干什么?走吧,我的住处转弯就是。”我跟她走着,问她:“你抱的是谁的娃娃?”
“是王同志的,她有事出街去了。”妻回答说。
我们默默地走着。不到三分钟,妻在一座西式洋房面前站住了。她向我说:“我就住在这里,寝室在楼上。王同志他俩也住在楼上,你跟我来吧。”我跟她到了寝室。她扭开了电灯,给我倒了一杯开水,便拿了面盆出去了。我趁这瞬间,打量了这间房子。我看着看着,止不住浮起了微笑;妻能在这里生活是多么幸福啊!可是,妻到底是干的什么工作呢?我正在猜想,妻一手抱小孩,一手端着洗脸水进来了。我从她手中接过了脸盆,便坐在床上一面擦脸,一面向妻问道:“你在这里作的什么工作?”
“就是这个工作。”妻用手指着小孩羞怯地说。
“什么?保姆?帮人?听人家的使唤?……”我霍地一下跳起来,手上的洗脸帕也掉在地上。我的眼睛死死地向妻蹬着,脸上的肌肉不断地抽搐,全身火辣辣的。仿佛周身蒙受了极大的羞辱一样。好半天我从牙缝里挤出几句话来:
“真想不到是这个工作。……你简直是在给我丢脸!”
“韶华:为啥要这样……这不同样是劳动,是工作么?”妻带着凄凉而委屈的声音回答我。她的话没说完,
便伏在床上呜咽起来。孩子也哇哇地大哭。
“什么工作?劳动?你就在这里干一辈子吧,我走了。”我气汹汹地向门边冲去。
妻听说我走,便连忙起身将我拖住:“要走明天走吧,车子快收班了。”正在气头上的我,根本不听她的,把她掀在床上。这时,孩子哭得更厉害了。我走近门边,忽然从隔壁房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梅娘娘,娃儿在哭什么?”
“啊,她要我抱到街上去找你。”正在伤心的妻,一面擦眼泪,一面哄着孩子:“好,不要哭了,你妈妈回来了。”说着,便抱着孩子出去了。
房间里留下我一个人。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只好捺住气,闷坐在床上。几点钟以前,我还以为她在某个机关和工厂工作,还准备今晚祝贺她,一同愉快地度过这周末。谁知一切想象都成幻影。大学生的妻子给人家做佣人,抱娃儿……羞辱呀,羞辱呀!……。我正想着这些,妻转来了。她嘴上露出苦笑,眼中含着泪水,低声向我说:“王同志请你到客厅去玩。”我本想不去,然而又不能没有礼貌,只好忍着气去了。
女主人热情地招呼着我。她怕我没有吃晚饭,便从妻身上接过孩子,叫妻去买点吃的东西。我连忙劝阻她。但女主人还是叫妻去了。
妻走后,女主人便和我随便攀谈起来。她对学校生活很感兴趣,问起我很多情况。当她听到我是学教育专业时,连声赞叹道:“太好了,太好了!人民教师,灵魂工程师!我爱人还不是在大学作讲师,今天有事没有回来。我也在幼儿园工作。哈哈,大家都是同行道的。”
后来话题转到妻身上。
“你爱人性情很好,在我生平中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好的性格。她既不多言多语,做事又勤快,又踏实。真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女主人夸奖似的说。
“嗯!……”我不知怎样回答才好。我也觉得妻的温顺淳朴的性格是无可非议的。
“她才来时,有点不好意思。其实,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同样是劳动嘛,只不过社会分工不同而已。在出席全国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上,不是也有饲养员、炊事员,他们不也是很光荣么?你说呢?”她一面谈,一面用眼望着我,好像在征求我的意见。顿时,我脸上马上红了起来.接着,她又说:
“你爱人还有些文化,如果她肯学习,还不是可以抽时间到业余中学去读书,你也可以作她的家庭教师!”
女主人说到这里,妻右手端着一大盘●菜,左手拿着一瓶酒进来了。女主人立即收住话题,把孩子放在沙发上,起来帮助妻摆杯盘碗筷,并招呼我和妻入席。在席上,我们又谈了关于教育,关于幼儿园的工作,后来还谈到了目前的大辩论等。在我们谈话中,妻在一旁也偶尔插一两句,但都用眼睛瞧瞧我,似乎怕我批评她说错。后来也就一起谈开了。
散席时,已是十二点。也许是神经过度紧张,再加上喝了点酒,我显得非常疲劳。女主人便叫我们去睡,并嘱咐我们早上晚点起来。我走回妻的寝室,倒在床上便朦胧地睡去了。
这天晚上,我做了许多恶萝:我似乎在与妻打架,女主人又来拉开……又好像有人拼命地追赶我…………。终于,工厂的汽笛声把我惊醒了。乳白色的曙光从窗户射了进来。我想起昨晚上发生的一切,也好像是梦一样。女主人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留在我的记亿中。我以前所认识的帮人就是作人家的奴婢,女主人一定是一个凶恶的刻毒的太太;可是今天这位女主人对我的妻却像姊妹一般,对劳动还有深刻而正确的认识。而我却是以旧眼光来看今天的一切。平常我在讨论会上也会说一套什么“劳动创造一切”、“知识分子要改造好,应参加实际劳动锻炼”等。可是昨晚却粗暴地对待自己的妻子。她哪里错了呢?她诚实地参加劳动,赢得了人们的敬重,这是她的光荣,难道不也是我的光荣?怎么是“给我丢脸”呢?想到这里,我看了看身边的妻,她安详而自然地睡着。眼角上还留着泪痕。我想昨晚她一定哭了。这时,我的心像针一样扎着。真想给她干点什么。我穿好衣服轻轻地走下床来。忽然看到屋角的一把帚帕。于是,就拿起它,浇着些水,来回地在弄脏的地板上擦起来……
妻终于醒了。她跳下床来,诧异地盯着我。忽然,她眼睛转几转,眼眶里充满了泪水,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喃喃地说:“韶华,你太好了……”这时,我也禁不住滴下了泪水,用手抚摸着她,带着歉意地说:“萍,昨天是我对不起你,请原源我。以后我再不这样了。你就在这里好好地干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