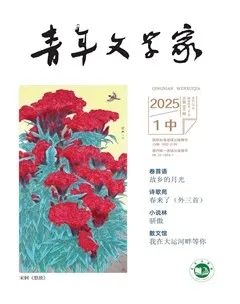海的彼岸
大海是我的家乡。每逢海浪怒吼、汽笛轰鸣之时,渔夫阿公总是叼着烟,提着热茶,与伙计远航。而我,总是在码头目送他离开。
“阿公,你要去哪里呀?”小小的我,躲在阿公身后,怯怯地问。
“去海的彼岸!”阿公爽朗大笑,伸出被海风割的开裂的手,抚我的头。
“为什么要去?”我不解地问。
“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洁白的帆一次次驶向碧空的尽头,那番话在我的心海泛起阵阵波澜,使好奇的小船轻轻摇曳。
那时,我恰好翻开《老人与海》。圣地亚哥的身影霎时与阿公那瘦小的身影重合。我为之着迷。可当时年纪还太小,除了对那惊险的搏斗着迷之外,我对鱼骨头扼腕,对故事的结局疑惑不解……
在懵懵懂懂中,岁月的海风将我这艘曾充满了好奇与疑问的小船,剐蹭出斑驳的铁锈。青春之船,在迷惘与怯懦中,停泊在码头,从未远航。
转眼来到初三,巨大的压力如风暴般咆哮。狂风,骤雨,我这艘小船更是以生病为理由,躲在码头,迟迟不愿出发。此时,阿公的人生之船也在大风大浪中受到重创—他得了胃癌,即使做了手术,每天也很难吃下饭。可他还是不顾家人的劝阻,一如既往,嘴上叼着根烟,手中提着杯热茶,每天随着妈祖的呼吸—那起伏的潮汐,在海上游荡。
那一天,我们又站在了熟悉的港口,一个是失意的少年,一个是虚弱的老人。
他,更瘦了,缩成一团,而眼睛依旧坚定。
“阿公,你别干了,家里不差钱,身体养好要紧。”我满是焦急。
阿公轻掸烟灰,双眼始终盯着遥远的天际线。“宁子啊—”他的声音低沉而嘶哑,“我们是妈祖的孩子,是海的孩子,不管风浪多大,船只都不能腐烂于码头,而应勇敢地向着海的彼岸前行。”
夕阳无限好,何惧近黄昏?万丈金光照亮了那瘦小的老人。而我,第一次发现,阿公竟如此高大。
那天,我再次打开《老人与海》,一页页纸如惊涛骇浪般拍打心船,无形间斩断了那根束缚我的粗绳。
人如船只,从船坞中造出后便停泊在码头,可它绝不可以,也绝不可能永远地停留在平静的码头。正如作家弗雷德里克·巴克曼在《焦虑的人》中所说的:“留在港口的小船最安全,亲爱的,但这不是造船的目的。”
总有一天,它会向那海的彼岸起航,开始与命运搏斗,将鱼叉插进鲨鱼的心脏。它可能一路上风平浪静,也可能一路波涛汹涌;它可能满载而归,也可能最后仅剩一副大马林鱼骨头。
但无论如何,它都要起航,它都将起航。终有一天,它必须去直面广阔的未知,而不是腐烂在狭窄的港口里。
直到岁月的海浪击碎它最后一块船板,直到光阴的海风撕烂它最后一片船帆,直到它抵达海的彼岸,在夕阳中邂逅圣地亚哥,邂逅阿公,与他们一样,捧起热茶,在蒸腾的热气中,为下一艘即将起航的船只讲述属于自己的传奇。
我会停歇,可我不会一直停留;我会失落,可我不能一直怯懦。海风正呼啸,彼岸酝酿着风暴,而码头之上,我发出沃尔特·惠特曼式的呐喊:“当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所有的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