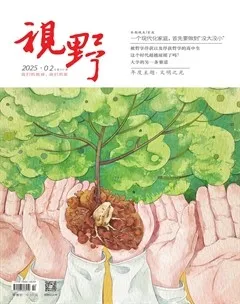你了解“毒物兴奋效应”吗?

理查德德·多尔爵士是英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位流行病学专家,是他最早证明了吸烟会引起肺癌,也是他最早把放射性和白血病联系了起来。为了进一步证明放射性的危害,他还对比过放射科医生和其他科室医生的平均寿命,却意外地发现前者反而比后者活得长些。
上世纪80年代,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家顺着多尔爵士的思路,研究了2.8万名在核燃料运输码头工作的搬运工在九年间的死亡率,并与3.25万名其他码头的搬运工做了比较,结果发现前者的死亡率反而比后者低了24%!谁都知道高剂量的放射性对人体危害很大,这个令人惊讶的结果只能说明,低剂量的放射性也许对身体健康有某种神秘的好处。
听起来有点不合常理对吗?其实早在1888年,德国药剂师雨果·舒尔茨就找到了一个类似的案例。他发现高浓度的重金属能毒死酵母菌,但微量的重金属反而能促进酵母菌的生长。也就是说,重金属既可以是毒药也可以是良药,两者之间的角色转换只是取决于浓度。
再往前推,16世纪的瑞士曾经出过一个很有名的江湖郎中,名叫帕拉塞尔苏斯。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研究生命的奥秘,推翻了很多前人的医学理论。他尤其喜欢研究毒药,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有毒的,而很多被认为是毒药的物质在小剂量的情况下很可能对人体有益。后来他把毕生的经验总结成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世间万物皆为毒药,没有任何东西不是毒药。之所以有些东西不是毒药,只是因为剂量不够。”
因为他的这个观点,后人把帕拉塞尔苏斯尊称为“毒理学之父”。
这个提法颇有些哲学的意味。但哲学不能治病,要想把这个思路用到医疗上来,还必须有符合科学标准的临床试验做基础才行。
毒理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准确地描述毒品剂量和毒性的关系。传统理论认为,世间所有毒品都遵循两种模式。一种是线性模式,即毒性和毒品剂量呈正相关关系,小剂量有小毒性,大剂量有大毒性,大部分致癌物都被认为符合这种模式,所以致癌物质无论多少都是有毒的。另一种是阈值模式,即毒品剂量小时完全无害,只有超出了某个阈值才会产生危害。这种模式的适用范围更加广泛,比如说,即使是水,超出一定浓度对人体也是有害的。
前文提到的重金属对酵母菌生长的影响则属于另一种全新的模式,后人将其命名为“毒物兴奋效应”。这个词来自希腊文,意为“刺激”。这个概念是说,某些毒物在低剂量的时候反而有益。如果画一条毒性和毒品剂量的相关性曲线,这条曲线将是典型的“双相曲线”,低浓度时浓度越高越有益,当浓度上升到某一阈值后,浓度越高则越有害。
举例来说,实验证明,高浓度的镉能毒死蜗牛和苍蝇,但低浓度的镉反而能提高它们的生殖能力。高剂量的辐射能杀死任何动植物,但低剂量的辐射却有助于提高植物的生长速度,并能让蟋蟀和小鼠更长寿。
“毒物兴奋效应”理论是毒理学界最具争议性的理论,因为其机理还没有搞清楚。但这并不妨碍一些科学家把这一理论延伸开来,把毒物的概念扩展为一切生存压力,包括饥饿、高温、感染、紧张……所有那些听上去不那么美好的生理刺激。新的理论认为,适当的生存压力对生命是有好处的,生存压力会促使生命体启动应急机制,而这种应急机制具有延迟效应,在生存压力消除后仍能起到某种积极作用。
比如,哺乳动物在细菌感染、重金属中毒或者发烧时会分泌一种“热休克蛋白”,它们能和细胞内的其他功能性蛋白质结合在一起,保护它们不被破坏。警报解除后,残余的“热休克蛋白”仍然能够起到某种保护性作用。再比如,人在进行体力劳动时大脑会分泌某种生长激素,促进神经细胞的生长,这大概就是为什么锻炼身体能够延缓帕金森病的发病速度。体育锻炼还能让人的身体处于轻度的“新陈代谢压力”状态(饥饿同样也会产生这种效果),这种状态能够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灵敏度,这对减缓糖尿病的症状有好处。
“毒物兴奋效应”甚至能够解释为什么蔬菜和水果是健康食品。以前人们曾经认为蔬菜水果能帮助人体清除有害的自由基,但临床试验一直没能证明这一点。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爱德华·卡拉布莱斯教授认为,蔬菜和水果中含有很多植物特有的化学成分,这些植物小分子本质上就是杀虫剂,是植物经过多年进化产生出来的对付食草动物的生物武器。人吃的蔬菜水果数量有限,摄入的植物毒素不足以对健康产生危害,但低剂量的植物毒素反而能促使人体产生应激反应,这才是蔬菜水果对健康有好处的真正原因。
(林冬冬摘自三联书店《在万物内部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