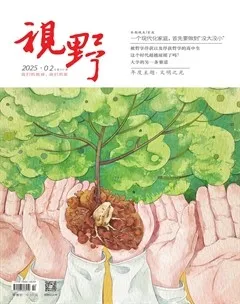我在重点中学教摇滚

今年48岁的老温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教书,他是一名历史老师,也做过超过二十年的班主任。在校园里,大家通常喊他“李老师”,而在网上,他是Vincent80,“老温”这个绰号便来源于此。很长时间,他是西祠胡同论坛“大西洋驿站”音乐版块的版主。
两个身份的交叉,是老温从2000年开讲、持续至今的摇滚乐选修课。摇滚课的开篇有固定的两个元素:一是唐·麦克莱恩的Vincent(《文森特》),和老温重名;二是乔治·迈克尔的Listen Without Prejudice(《听无偏见》)的专辑封面,这是老温希望摇滚课能传达出的理念。
老温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保送上了师范大学,后来顺理成章当了老师。每年拍毕业照,他都要穿上一件印有切·格瓦拉大头照的衣服坐在第一排。其实,他更喜欢早年接受采访时的一张照片——他手握贝斯站在讲台上,背后是用英文写出来的摇滚发展历程,尽管英文不是他写的,照片也是摆拍,但情是真的。老温说,这是一张分量足够放在他追思会上的图片。
25年间,有超过500位学生选修过这门摇滚课。在每个周四的下午,老温带着他们暂时告别作业和考试,去摇滚乐的世界游玩一圈。
以下是老温的讲述。
这门摇滚选修课的正式名字是《摇光滚影——现代影音文化》,今年已经开到了第25个年头。
2000年是摇滚课诞生的那一年,学校发下来通知,鼓励老师们开设选修课,大家都可以报名试试。我那时参加工作刚两年,年轻气盛,天天穿约翰·列侬等各路摇滚主题T恤,脑子一热,就报了自己要教摇滚。一轮评估结束,批下来了三门选修课,我的摇滚课就位列其中。
不管怎么样,我完全是出于热爱才要教摇滚的,既然申报成功,那就干起来。
最开始上摇滚课的几年,我一直用的是Word文档,列一个表格,左边是专辑封面,右边是介绍和一些经典曲目。当时教室的投影长得还像个小电视机,挂在铁皮箱子里,每节课我就拿着这个文档给大家捋。那时候也没有手提电脑,为了给大家放歌,我就背着一书包自己的磁带,手里拎着录音机去上课。后来教室电脑有光驱了,但那时候新技术时灵时不灵,CD有时候放不出来,为了保险,我还是背着大书包,拎着录音机去上课。最早一批学生对我的印象,基本都是背着大黑包,穿着乐队T恤走在校园里。
大概这么过了五年,课上一个小孩儿跟我说,老师,您可以做超链接,我吃惊,还能这么搞?后来我学会了,才结束了背CD、磁带上课的体力活儿。
大概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也开始琢磨这个课程到底该怎么上,最后算是遵循了西方现代音乐史的脉络,以“爵士轻音”为例,先上溯到新航路开辟和三角贸易,再从南北战争、种族隔离、黑人民权运动说开去,将布鲁斯、拉格泰姆、布基乌基和迪克西兰等音乐类型穿插其中,最后落在新奥尔良爵士,这是爵士乐最早的篇章。
后面就到了摇滚乐的诞生。但我不会一上来就讲猫王,我会从偷袭珍珠港开始,讲战后美国经济繁荣、婴儿潮、垮掉的一代,还有玛丽莲·梦露、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还有诺曼·梅勒、塞林格、赫伯特·马尔库塞……这些都是摇滚乐诞生的大时代背景。
讲完20世纪50、60年代摇滚乐的诞生,我又会讲英伦入侵,再到70、80年代朋克、雷鬼、金属等,都会结合诸如越战之类的相关历史事件作为时代背景,很多PPT页面都是我直接从历史课件上复制过来的,然后是与近现代科技史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电子音乐史,再到最后一讲回到根源的蓝调专题……课程设置上,我有一点私心,一个是我跳过了鲍勃·迪伦的专题,因为挚爱,不舍得讲;另外一个,就是排在最前面的校园民谣,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也和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联系最为紧密。
我只给一支乐队做了专题——披头士和英伦入侵。在20世纪60年代,就在利物浦这一座城市里,居然一下跳出来四个留着拖把头的顽皮男孩儿,引领了60年代的流行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整整一代青年人以摇滚乐为精神信仰,形成了独立的世界观,改变了处世的态度,并以此完成了人格和精神气质的自我塑造——这个源头是可以在披头士这支乐队身上找到的。
说到底,我讲的其实还是历史,只不过聚焦的是一个青年文化勃兴的时代:伍德斯托克、嬉皮士、爱之夏,那个时代里的人是根据一种精神去做事的,他们有自己的理想、真诚和激情。
摇滚课最开始讲的那几年,我的课绝对是超前的,也是信息量巨大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在我的课上才第一次系统地了解摇滚乐,他们之前对此完全陌生。
很长一段时间,摇滚课都没有被特别关注过,也因此我的摇滚课和我的学生们都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由长大了。
开始上课,第一件事是关灯,这样才能专心听音乐。每节课的开头必然是展示一张名叫Listen Without Prejudice(《听无偏见》)的专辑封面,我告诉学生们,这是我希望这堂课能传达给你们的信息。
上摇滚课的第一年,我碰上了一个孩子,她是其他人眼中的“不良少女”,总独来独往、不服管理,教育处经常约她谈话。最后他们也没办法了,知道她可能喜欢听摇滚乐,我又开了这么一门课,就过来找我帮忙,看能不能跟这个孩子聊聊。那一次,我跟她聊了很多摇滚相关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那次聊完,这个女孩儿跟其他人说,这个学校居然还能有老师不古板,知道戴夫·兰帕德。这是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我甚至还有一件他们的乐队T恤。
后来,这个孩子就能听进去我说的话。可能是我自我感动,但我觉得她对学校的态度也可能就此改变了,她开始相信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
(晨健摘自《青年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