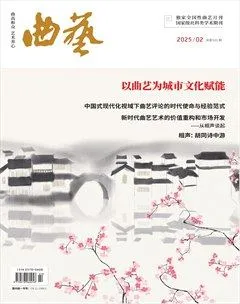对曲艺艺术助力特色文化城市建设的一点思考
人类创造了灿烂的城市文明,中华民族也建造了大量繁荣的城市。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市得到了极大地发展,但也因为包括文化相对缺失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影响,产生了“城市病”。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和核心资源。建设特色文化城市,延续城市文脉是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曲艺艺术有着鲜明的地方性、亲民性、大众性特点,深受群众喜爱,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特色文化城市,曲艺艺术大有可为。
一、城市略论
城市是人类文明极其重要的成果,是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的产物。城市的出现和发展是人类经济、科技、文化进步的深刻反映。
自人猿揖别,人类经过漫长的进化发展逐渐告别了茹毛饮血进入到农耕时代。继而生产力不断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手工业和商业逐渐兴盛。因生产和交易的需要,相关从业者相聚而居,同时部落和政治集团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开始建立城池,这就是城市最早的雏形。“在远古时代,人类从茫茫的荒野之中走进城市。这是人类社会的最伟大的进步之一。正是人类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走进城市,使城市文明成为划时代的界标。”①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建立了大量的城市,创造了灿烂的城市文明。据《史记》记载,黄帝建“五城十二楼”,这应是我国关于城市的最早记载。考古发现,距今约3800年的夏朝在今天洛阳偃师的二里头建立了规模可观的王城。城内布局分明、功能齐全,道路、供排水等公共设施较为完善,已基本具备了城市的功能和特点。盛唐时期的长安和洛阳两京不仅是当时中国城市的典型,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当时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11世纪的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省开封市),人口逾百万,“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②足见当时的“汴京富丽天下无”。元明清时期,北京当仁不让成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明清两朝500多年都城的历史,让北京积淀了丰厚无比的文化。
在北方的城市持续发展的同时,随着孙吴政权建立和晋、宋两朝的南渡,长江以南被不断开发,并逐渐出现了南京、杭州、苏州等新的经济文化中心,南朝诗人谢朓就诗赞南京“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宋朝词人柳永也称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近代以来,天津、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下,在洋务运动及近现代科技的推动下,以不同于中国传统城市的模式和速度崛起,成为区域经济、航运、文化、金融、贸易、科技中心。
约5500年前左右,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出现在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而在重商主义、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等的推动下,近现代城市不断涌现。这些城市吸引和集中了大量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的资源和人才,成为国家和区域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交通中心,对周边产生了极大的辐射力量,推动着社会迅速发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持续推动城市建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更是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24年的67%;城市数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29个,在2023年末增至694个。城市的大规模发展,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蓬勃态势。
二、文化之思
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便利,也引出了弊端。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都市都曾经或仍然被环境污染、失业、犯罪、住房紧张、交通拥堵所困扰。在治理“城市病”的过程中,人们还发现,野蛮生长的城市深刻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历史积淀的文化在慢慢消失,原来的精神生活被经济活动或文化“泡沫”所取代。城市患上了“城市病”。
我国的城市也没有例外。改革开放初期,有些城市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片面追求GDP增长,为建设所谓现代化城市大拆大建,牺牲城市肌理拉直城市道路。传统文化在城市的不断膨胀中日渐式微,城市的历史被淡忘、城市原有的特色模糊不清,最后几乎“千城一面”。“城市处在未来发展成与败的十字路口……城市更胀大,交通更拥挤,资源更短缺,城市病更严重。”③“对于量大面广的城市化建设,如果我们较为自觉地把它看成一种文化建设,那么结果就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相反,如果失去文化的追求,则可能导致‘大建设、大破坏’。在此意义上说,今天的城市文化建设直接关系中国的未来。”④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一些国家就对城市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关注和研究。“从1933年关于‘功能城市’的《雅典宪章》提出,到2003年伦敦市‘文化城市’的定位,也已经经历了七十年关于文化城市的探索。在实践中人们认识到,城市不仅具有功能,更应该拥有文化。文化是城市功能的最高价值,文化也是城市功能的最终价值。”⑤“2003年伦敦市长发表‘城市文化战略’的演讲,旨在维护和增强伦敦作为‘世界卓越的、创意的文化中心’,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城市’并投入巨资兴建新的文化设施。”⑥
党和国家也对治疗“城市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城市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和要求:“推进城市修复、生态修复工作,延续城市文脉。”许多专家学者和民间有志之士对城市建设和发展进行了广泛研究,纷纷提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城市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庞大,由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等多种元素组成的富有生命力的系统,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有机结合。马克思认为,城市的经济基础和科学技术水平决定了城市的政治、文化,后者又反过来深刻影响着前者的建设和发展,规定、指引着城市的发展方向。如果说建筑、道路是城市的骨架,经济是城市的血脉,那文化就是城市的灵魂。文化贫乏的城市是灵魂呆滞、枯燥,缺乏生命力的城市。一个城市的实力不仅取决于城市的经济实力,也取决于城市的文化实力。文化也是一种资源且是吸引人才的核心资源。世界上依靠文化优势在竞争中取得成功的城市很多,而缺乏文化优势的城市尽管在某个时期经济发展迅速,但也终究缺乏后劲。所以找到城市的文化底色,就是发展文化城市的重要方法。
每个城市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自然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独有的、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文化特色。城市的文化特色是万花丛中的一抹亮色,是独有的资源和竞争力。不同文化可以互鉴交流、融合,但文化特色不可模仿和复制。“城市特色影响文化定位,文化定位体现城市特色,而文化定位一旦形成,又必然会强化城市特色。”⑦“深入研究城市的历史发现,创新城市的文化特色准确城市的文化定位,建设特色文化城市,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必然道路。‘城市’与‘文化’的联姻是历史进步的必然。城市发展的走向必将是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⑧
三、曲艺之助
2022年,吴亮莹演绎的评弹表演唱《声声慢》在网络走红,吴侬软语玲珑婉转的唱腔引发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到苏州园子现场聆听。《声声慢》展现江南特色的音乐,让年轻观众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使更多人听到了苏州声音,彰显了苏州城市文化形象。而《声声慢》的走红也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深入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使曲艺艺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信息技术革命使曲艺艺术传播渠道更宽广,减少了观众观看表演的时空限制。而在推动曲艺单一介质在网络上发展的同时,还有曲艺人探索起了曲艺艺术与动漫、电子游戏等新艺术形式相结合,进而“借船出海”、推广自身的可能性。2024年,陕北说书《黄风起兮》爆火,登上了各大社交媒体,登上了央视舞台,还拿到蛇年央视春晚推荐卡。陕北说书的非遗传承人熊竹英随之被地方文旅部门、高校、游戏主题音乐会邀请参加各种演出、学术活动,甚至外国人都会主动哼唱甚至学习陕北说书。究其原因,就是陕北说书成功与火遍中外的游戏《黑神话:悟空》成功合作。“陕北说书与3A游戏,一个传统一个现代,似乎并无相关性,实则有中华文化赋予的深层链接。”⑨
伴随着机遇的是严峻的挑战。《声声慢》和《黄风起兮》只是少数,大部分曲艺曲种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年轻观众减少、创演人才流失、拿不出优秀作品、不适应新传播业态发展的窘境。特别是不适应新传播方式这一点在城市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新媒介对乡村和城市的影响“一视同仁”,但城市的喧嚣更大程度上稀释了文化,“泡沫”“快餐”在线上和线下传播力度更大,让“城市病”对曲艺有了更大的冲击。如何传承和发展曲艺艺术,发挥曲艺艺术在建设特色文化城市的作用,是曲艺艺术工作者及文化艺术研究者亟待解决的课题。
曲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曲种都是由当地的“地气”孕育出来的,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和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如苏州评弹、天津时调、东北二人转等,几乎成为当地的全民艺术,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皆对其钟爱有加。人们不仅观看曲艺表演、评论曲艺表演,还参与曲艺表演。观众不仅是曲艺艺术的消费者,同时又是曲艺艺术的评判者和曲艺艺术人才的培养者。观众的爱好引导着艺术家们的艺术之路,只有被观众认可的演员才能真正成为合格的曲艺演员。也正因为兼具地方性和群众性两个特点,曲艺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最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的艺术形式。特别是在当代,城市空间日益紧张,但曲艺就是具有在螺蛳壳里做“水陆道场”的能力——人员少、规模小、无需复杂道具服装、既可在室外又可在正规剧场演出,这一切都能让曲艺成为城市文化乐章中最活跃的音符和最鲜亮的底色。
“到天津听相声,到东北看二人转,到江南听评弹,不算白来一场”,这是游客的念想,也应该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抓手。近年来,我国多地开始探索地方曲种“出圈”的有效密码,为文化城市建设激发“曲艺力量”。天津自2010年开始举办相声节,至2024年已举办了多届。2023年的相声节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因为正值癸卯新春,2023年的相声节不仅吸引了本市的观众走进剧场,还吸引了众多外地观众。一些观众专程到天津观看相声节,甚至有的观众带着行李箱奔波于相声节各个剧场。这不仅进一步提升了相声的知名度,有效增加了曲艺与旅游的黏性,更为天津的“曲艺+旅游”提供了“平时发展、有力推进,抓住时点、推出名片”的有效方法。
研究、探索曲艺艺术与城市特色文化的交点,求取两者之于“彰显城市文化特色”始终是让曲艺助力城市文化建设的关键一招。
曲艺的核心竞争力不仅包括“稀缺性”,还包括“通用性”。如果所有外地人和年轻人都难以看懂曲艺或不认同其传达的观念价值,它的再生能力必然会被不断削弱。而要让城市受众认识曲艺、理解曲艺,相关从业者就必须深度解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找寻城市生活中可供转化升华的素材,打造出真正能引发城市受众共鸣的作品。当然,这并不是要曲艺创演者一味迎合大众审美和流量经济,而是要求他们和相关主管部门引导、鼓励、发掘曲艺中富有积极意义、对城市生活有促进作用的成分,做好改良、阐释,打造一批反映新时代风貌的经典作品,以这些作品为抓手带动更多人关注、研究曲艺。
曲艺的传承发展也离不开特定的时空条件。正如有学者总结的,非遗文化一旦脱离了时空环境就难以传情达意、让观者体会其中的价值与意义。城市的文化认同首先表现为“对地脉和文脉的尊重和维护,对潜藏于人们集体无意识中的城市身份与记忆的确认、激活与建构”。当前,各地都在不同程度挖掘本地文化,打造“古城”文化名片。但古城不能只成为一个显著不同于城市其他地理板块的景点,而应当成为无处不在、被各种城市符号普遍指向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古城仅有硬件设施是不够的,要从更高更全面的角度考虑,有力提升文化资源和相关服务保障体系的建设,赋予古城“灵魂”。而曲艺作为最接地气、最有民俗韵味的艺术形式,理应在其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社会的支持和帮助下,曲艺艺术定会重放异彩,助力特色文化城市建设,与特色城市文化共发展。
注释:
①张鸿雁:《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论—中外城市形象比较的社会学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
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2020年,第3页。
③转引自单霁翔:《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中国名城》,2008年第1期,第12页。
④武廷海、鹿勤、卜华:《全球化时代苏州城市发展的文化思考》,《城市规划》,2003年第8期,第62页。
⑤单霁翔:《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发展路径辨析》,《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第53页。
⑥吴良镛:《总结历史,力解困境,再创辉煌—纵论北京历史名城保护与发展》,引自国家图书馆编:《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史鉴卷上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349页。
⑦单霁翔:《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中国名城》,2008年第1期,第11页。
⑧单霁翔:《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发展路径辨析》,《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第41页,
⑨杨钰莹:《文化中国行——陕北说书如何从“爆火”到“长红”?》,《农民日报》,2025年1月17日。
(作者:天津市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