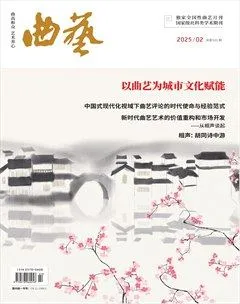传统到现代:略论民国时期苏州评弹的都市化
传统艺术在市场环境下面临的生存困境是我国文化产业综合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尽管近年来依托政策支持与业界努力,剧场、书场独见“银发族”的情况已有所改善,但传统艺术的守正创新之路依然任重道远。虽然越来越多的民族文化瑰宝被列入非遗保护名录,但我们的欣慰与担忧仍然是并存的。困局来自许多方面:作品囿于一隅,演员青黄不接,观众日渐流失,以及诸多各家难言之经,但若要究其根源,仍应回到传统与现代这对矛盾中寻求答案。
据国家统计局报告,截至2023年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6.16%,而该数据在1949年尚只有10.64%,这表明,在70多年间中国经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然而,当中国不断向现代化社会迈进的同时,传统与现代间的矛盾也在各个领域逐渐凸显。而传统的艺术形式,几乎无一例外地发展成熟于“过去”,这是由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发展形态决定的。所以要探讨传统与现代间的纠葛,仅聚焦当下难免身在此山而为一叶障目,不妨回到历史中寻找答案。事实上,作为中国社会整体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传统艺术在近代上海的发展历程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样本,已有的研究多关注传统艺术进入上海后的新样态,但对新样态与传统艺术生产方式间关系的讨论明显不足,而后者恰恰是考察传统艺术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一环。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江南代表性曲艺曲种苏州评弹为对象,通过考察其在近代上海的发展历程,探讨该时期评弹现代化转型的特点、程度和局限,以期为当下传统艺术的守正创新提供借鉴。
一
要考察传统艺术的现代化转型,首先应对传统时期的艺术生产方式做一讨论。传统艺术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根植于传统社会,这不仅直观地表现在形式或内容上,更体现在艺术生产的逻辑与艺术本体的特征中。以江南地区代表性曲艺曲种苏州评弹为例,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地理环境(水路交通和乡镇布局)以及农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农事节律)从根本上塑造了她的艺术本体——在书场说演长篇书目的演出形式和以说表为核心的演出技巧。前者是空间关系,环太湖流域密布的水网不仅构筑了江南地区星罗棋布的市镇格局,也为艺人往来鬻艺提供了交通的便利;后者是时间关系,所谓“菜花黄,说书像蚂蟥;菊花黄,说书变大王”,民众以农事节律为主导的生活决定了评弹业的淡旺季,也间接影响了演出的周期与书目的长短。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评弹艺术本体的生成规律。在交通成本与农事节律的制约下,说书人以相对固定的节奏在江南乡镇间“背包囊,走码头”,短则数月,长则半年。到书场排日听书,是江南民众最日常化的消遣,而长篇书目曲折的故事情节与复杂的人物关系正是吸引听客循序渐进连续听书的关键。加之碍于文化水平,旧时有编新书能力的艺人比较少,且成本颇高,如若持中短篇演出,便只有两种选择——在一家书场不断更换书目,或持一部书目不断更换书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然不具可行性。在此基础上,为适应走码头过程中不同听客群体差异化的审美需求,淡化同一书目反复说演带来的审美疲劳,说表在演出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说表赋予了说书人对书目或芟芜汰冗,或细致描摹的拉伸空间,也令演出的艺术呈现能够根据听客的审美需求适时而变,由此发展出了评弹“各家各说”“常说常新”的独特艺术生产方式。
当依托于传统社会的艺术形式与现代社会发生接触,势必产生诸多复杂的矛盾。中国在近代的艰难转型,显示了古老国家欲图挣脱延续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桎梏是何等困难。即使在近代江南,明清以来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始终未能带来实质的内生性转机。最终,西方铁蹄在19世纪中期叩开了看似牢不可破的国门,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生产方式裹挟着欧风美雨式的现代生活,向以上海为首的港口城市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入侵。不到百年,上海这座江南小镇便一跃成为执全国经济文化之牛耳的国际都会,并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顶峰,如忻平所说:“就建国前中国现代历史而言,20-30年代的上海现代化进程发展得最快,社会生活的现代性体现得最为突出,历史进程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矛盾表现得最为强烈,历史的进步与历史的痛苦展示得最为明显,外在与内蕴两种现代化动力在此的契合程度凸显得最为深刻。”①无论时人还是后人,对近代都市上海的直观印象,都直接地与霓虹闪烁、光怪陆离的摩登生活联系在了一起。丰富、发达的娱乐产业无疑是上海最引人瞩目的现代化标签,“晚清以来,上海聚集了京剧、越剧、沪剧、评弹、淮剧,以及滑稽、昆曲、扬剧、粤剧、锡剧、绍剧等几十个剧种,成为了近代中国最大的戏曲舞台”。②此外,电影院、舞厅、歌场、跑马场、跑狗场、弹子房、游乐园等一众新式娱乐场所的加入更为上海的娱乐生活增添了摩登气息,也令沪上娱乐产业的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在此过程中,以苏州评弹为代表的传统娱乐形式普遍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变革,生发出了诸多前所未见的新特征,逐渐形成一套匹配都市社会的市场逻辑,深刻影响了评弹在近代的发展。
二
上海在苏州评弹艺术史中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致于直到今天关于“苏州评弹发源于苏州,发祥于上海”的讨论仍令苏沪二地的评弹爱好者们莫衷一是,争执不休。问题的核心在于持论双方对“发祥”一词解释的差异,赞同者意欲借此强调评弹来到上海后的高光表现,反对者则认为其抹杀了传统时期评弹在中心地苏州的繁荣历史。但可以肯定的是,双方均不否认近代上海在评弹艺术史中的里程碑地位。
相较于评弹的传统中心地苏州,上海的现代商品性娱乐业不论在市场规模、容量,还是经济效益、社会影响等方面,都是传统中国历史上亘古未见的。此种新旧间的过渡,得益于政治、人口、经济等各种内外相继因素的交织联动,制造了一个有别于传统农耕文明的近现代城市空间,深刻改变了这座城市的社会结构。正如周武所指出的,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对江南传统中心地苏州、杭州的取代,是现代城市对传统城市的取代,“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③近代上海的都市社会结构带来了有别于传统市镇的全新市场空间布局。传统江南市镇的间隔普遍保持在20至30里,而30年代的上海则拥有以西藏路、南京路和静安寺路交界一带的1个中央娱乐区,与8个次中心娱乐区④,各次中心区与中央区间始终保持了1300米至2000米左右的距离。同时,娱乐区以消费型娱乐为核心功能的街区属性,也令其拥有远超传统市镇的娱乐场所数量,“三四马路、大新街附近一带以及南市城隍庙等处,简直是五步一家,十步一处,到处悬挂着书场灯笼与招牌”。⑤“此外附属小茶馆里的说书也普遍全市,无论是偏僻的地方,总能够找到一二处。书场之在上海,大家已公认是平民化的消遣场合了。”⑥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就空间上看,上海庞大的市场体量使其在城市内部形成了一个相较江南大市场的、缩放式的评弹市场网络,构成了“大江南”“小上海”的市场格局。在上海,各娱乐区间的距离相较传统市镇间距缩短了约10倍,而城市道路的建设进一步扩大了个体的活动半径,平整宽敞的马路上往来的各式交通工具,突破了过去乡镇石路、土路中颠簸前行的独轮车所能达到的最远边界。据计算,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上海市民通过交通工具(电车、公共汽车、黄包车、脚踏车等)出行,在同样的半小时出行时间内,可达到的范围已由步行的1.5至2公里扩大到5至10公里,外出空间相较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增大将近4倍。⑦如凤鸣台书场,就有三路电车、十路公交汽车直达门口,“交通最便”。⑧活动半径的扩展对娱乐业发展的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意味着市民活动半径中所涵盖的娱乐场所的增多,便捷轻松的出行体验也令市民更愿意外出参与娱乐活动;另一方面,从业者活动半径内的市场份额也相应增加。由此,在一定程度上,说书人以往在“大江南”网络中的走码头活动得以在“小上海”的城市内部网络中实现。

新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拓展了都市娱乐业的市场空间。除各类书场和私家堂会外,上海最先利用无线电技术开辟了空中书场,在不占据实体空间的状况下最大限度地拓展了评弹的市场范围。“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无线电播音的普及,上海的广播电台发展十分迅速,电台设立众多,最多时电台数超过一百家”⑨。时人为之感叹:“一到下午,说书节目,便陆续开始。待到晚上,听到的不是唐大爷和秋香,便是樊家树和沈凤喜。说书先生一面叮叮咚咚地弹着三弦,一面逼紧着喉咙唱着词句,这时上海差不多要变成说书世界了。”⑩
庞大的市场、丰厚的报酬以及都市摩登的魅力,令上海释放出了强大的虹吸效应,“上海先生”成了说书人们在“码头老虎”之上最高的追求。大量响档纷纷赴沪鬻艺,书场场东为了招揽听客,在争聘名家的同时还创立了多档越做的形式。越档,指一个书场同时聘请多档艺人,通过压缩每档的演出时间实现合作演出的表演形式。虽然早在上海以前,苏州就已有二档越做的历史,但越做真正意义上对传统形式的突破,则是在20世纪初的上海完成的。多档越做最先由游戏场“楼外楼”推出。为吸引游客,“楼外楼”经理一改评弹“一日一档”的演出惯例,转而同时聘请三四档说书人同场演出,将每档的时长压缩至45-60分钟,首开多档越做先例。这一演出形式下,听众的花费只是略高于在旧时书场的,就能欣赏有如年终会书般响档云集的盛况,时人为之感叹,“目前上海各书场,平常每场都有四五档之多,好像天天在那里说会书”11。多档越做在“楼外楼”的成功,很快便为各大游戏场所效仿。据张健帆回忆,“小世界的说书场,……日夜两场,好像说会书一般”12“尤其在盛夏之夜,邀上两三知己,登上琼楼高处,泡上一壶清茶,彼此把茗清谈,听听说书,望望夜景,乘风纳凉,是为当时上海人所公认的赏心乐事。”13
多档越做的兴起大大加快了说书人在都市中的流动速率,并逐渐将说书人从传统的农事节律中抽离,纳入到现代工业节律中。多档越做通过压缩每档艺人的演出时间来实现多档同台的效果,这意味着艺人也会同时接下多家书场业务,频繁地在各书场间流动,这种流动的实现不仅需要依托市场的体量与便捷的交通,更需谨守时间的规则:
现在说书一档,限定四十五分钟,上下档衔接都有一定时间,不能或迟片刻。如有一档误卯,便要牵动大局。照旧式惯例,前面一档说书,须看下面一档先生到场后,才可落回下台,赶别一家场子,无须再顾这边的冷场,所以目今的说书人,绝对不能误卯的。14
由是,以时、分、秒为单位的更为严格、精确的工业时间取代了以年、季节、节气为单位的农业时间,乘着黄包车在书场间奔波的说书人们就如拉尔夫金所说的那样:“时间世界不再与潮起潮落、日出日落以及季节的变化相联系。相反,人类创造了一个由机械发明和电脉冲定时的人工的时间环境:一个量化的、快速的、有效率的、可以预见的时间平面。”15
庞大的市场规模与更快的演出节奏,令上海俨然变成一个缩放式的江南市场,说书人以更快的速率在各式书场、堂会、电台间流动,停留沪上的时间大大增长。如周玉泉“三十岁到五十岁的二十年中大部分时间在上海,偶然出码头,也是短时间的”。16 1930年的《大光明》报曰:“吴小松、吴小石、魏钰卿等辈,情愿作沪上寓公。其次亦不惮繁琐,流转江湖。”17徐云志因上海业务太多,索性把家迁至上海,“书场演的太熟,就在电台播唱。最忙的时候,一天要做八家电台,人家叫我‘八面威风’。等到电台又太熟,就专做堂会”。18
正是因为都市市场强大的内循环能力,大大加快了评弹的都市化。尽管在此之前说书人同样会到上海鬻艺,但30年代评弹所表现出的都市化气质远超过去任何一个时期。张健帆在忆及自己中学时(20世纪20年代)的听书体验时,曾谈到被同学嘲笑“喜与老人为伍”,并被冠以“说书先生”的绰号取笑19,而短短十年,评弹已然摇身一变成了都市流行文化的一员,引领着都市的摩登风气。薛筱卿创造性地为弹词加入伴奏,加深了上下手间的互衬,增强了弹词的音乐性。周云瑞在《珍珠塔·唱道情》中,借鉴了流行歌曲《人鱼公主》的音乐,发展了伴奏过门,使听客耳目一新。《啼笑因缘》《秋海棠》等现代书的编创,令评弹跳脱出了传统题材的桎梏,“西装旗袍书”风靡一时。范雪君在小落回时,弹唱流行歌曲和最新电影插曲,活跃书场气氛。听书的场所也开始由桌椅板凳、闲散悠然、满是市井烟火味道的旧式茶馆转移到装修考究、配备沙发座椅、音响设备与空调冷气的专业书场,说书人的日常演出空间逐渐与这座城市的气质融为一体。1932年的《社会日报》曾谈到说书业在上海的转变:
说书之于上海,在十几年以前,简直也是一班老先生们专有的享乐,现在是慢慢地普及起来了。……二十世纪化的东方书场的情形,却不同于前面所说的了,那边简直跟南京大戏院差不多,有摩登风流的年轻姑娘,有脂粉满面的青年子弟。20
广告是消费主义的重要载体,相较于霓虹灯广告牌带来的视觉冲击,无线电则以声波的形式将广告投放到了都市社会的各个角落。借助评弹的艺术表现手法,广告常常能有更强的表现力。说书人的“三寸不烂之舌”不仅能让听客为之捧腹而不致生厌,还可以将广告用开篇播唱,使人耳目一新。这种对有声广告的艺术化加工,不论是流行歌曲还是地方戏曲都很难做到,而评弹却能在插科打诨中灵活地加以穿插,或是专作广告开篇,以艺术化的方式加以表达。这无疑是商业广告进入无线广播时期后的一个重要创新,如盛利食品公司的广告开篇:
连天烽烟说申江,赤日炎炎火伞张,卡德路边人影众,中心地点闹洋洋,(君可见)一帜独悬高屋顶,盛利两字露锋芒!四川路中名早扬,老店新开营业兴,乔迁更加生涯旺,同行眼内出红光。物美价廉人皆知,大名鼎鼎可称王!冰淇淋,与冰棒,橘子杨梅触鼻香,各式刨冰件件有,凭君选择滋味尝,(保你是)赞誉连连呼清凉。价钱巧,品质良,清洁卫生味芬芳,电话三八三八九,出门送货用冷气装。代价券印成美术化,亲朋馈赠最相当,万千主客都称好,有口皆碑永不忘,盛利饮冰播上洋。21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市民,在酷暑之日闲坐家中,享受着收音机畔随电波传递而来的弦索叮咚之声,若有解颐之念,只消照着广播中一个电话,便有商贩将刨冰饮品送货上门。如此都市生活,何尝不叫人神往?
三
尽管20世纪30年代后评弹在上海的发展表现出诸多新气象,但是否意味着该阶段的评弹已完成了现代化转型仍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评弹在都市市场中的内循环依旧延续了传统时期的艺术生产方式,即携一到两部书目在各个演出空间之间流动,只是频率更快,周期更短。然而尽管上海有着远超一般码头的市场体量,却依旧无法满足评弹长期演出的需要,为了消解听客的审美疲劳,即便是名家响档也仍需定期离沪跑码头。最典型的例子是“孤岛”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令该时期租界内的娱乐业畸形繁荣,评弹也不例外。为避战乱,大量名家响档久居租界不愿他往,初期生意自然红火异常,但不到两年,大批书场的经营便开始每况愈下,即便是身居行业金字塔顶端的沈俭安、薛筱卿、蒋一飞等,开书数月,卖座也毫无起色,以致被迫提前剪书22。到1943年,即便是“执书坛牛耳”的“描王”夏荷生业也遭逢了“抽签”23的窘境,究其原因,是“在沪之时日较久,隶‘东方’连做‘复档’,无怪听客如食炒熟之韭菜,淡而无味,不足为奇矣”24。由此可见,上海市场的都市内循环并不足以使其脱离传统江南市场独立存在,评弹演出也随着说书人的赴沪、离沪而在传统与现代间徘徊。
在艺术生产方式未发生变革的前提下,评弹的诸多都市化特征实际与其艺术逻辑相悖。多档越做压缩了每回书的时长,要求说书人更频繁地在书场间辗转,1947年刘天韵、谢毓菁师徒一天需隶“书场七家,及电台二处。自午后至深夜,所拼钟点前后衔接,几无片刻宁晷”25。而各家书场、电台的开书时间不尽相同,导致说书人在各家说的回目也前后相异,往往厘清混杂交叉的书路便要费去大把精神。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更多的说书人选择将重心由说表转向与书情关联较弱的弹唱与放噱,或借精致华丽的衣饰胜出:
(新型书场)聘请说书艺人,但求外表,不务实际。有许多响档,书艺并无骨子,只是噱头多,年轻漂亮,能够吸引烟视媚行的女听客,色迷迷的男听客,为饱耳福兼饱眼福起见,也会趋之若鹜。所以新型书场主人,为生意眼着想,非多聘较有噱头,衣饰华丽的男说书人不可。若是不修边幅,落拓不羁,而有真才实艺的说书人,反在摈弃之列。26
空中书场的特点——视觉缺失、听觉放大同样弱化了说表的效果,助长了“重唱轻说”的倾向。“起脚色”的受限尤其显著,“书场上,听客亲见其人,若有言不达意之处,可以面部表情及手势为之。如《玉蜻蜓》中之‘金大娘问卜’,《双珠凤》之‘堂楼详梦’。书中之瞎子,并不开口,而作暗中摸索状。至于无线电中,则完全不能,须详细表明,而听者反味同嚼蜡。至于评话中打武,更非手势解数不可,刀来枪去,如身历其境。在无线电非细细交代不可,故较难于书场也”。27视觉的缺失对评话的打击尤为明显,因“评话注重现行,书中既多开打,状两军交锋,刀来枪去,虽在台上,手执扇柄,虚张声势,描摹一刹那之神情,能使座上听客,为之动容。惟在播音室中,传声不能传影,乃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况开讲评话者,须状叱咤风云,慷慨激昂之志士壮汉,粗声大气,于电波声中,震耳欲聋,故于播音初期,独多弹词节目,评话绝无仅有”。28
“重唱轻说”促成了弹词开篇的独立,进而推动了流派唱腔的大发展,在这一层面是值得肯定的,但需注意的是,二者的繁荣实际上也掩盖了“重唱轻说”埋下的隐患。在艺术生产方式未改变的情况下,开篇和流派唱腔并不能达成市场逻辑与艺术逻辑的自洽,而是仍需依托长篇为基础存在,一旦脱离书情,便只是用吴语演唱的流行歌曲,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余论
毫无疑问,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影响力,是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比拟的。“这个字眼如同兴奋剂一样激发着人们的想象,点燃了人们的希望。”29如同张鉴庭“七进”上海一样30,评弹在上海站稳脚跟也绝非一蹴而就。经历了清中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的漫长探索,评弹才逐渐由老气横陈、慢条斯理的旧式茶馆中转移至最时兴的游戏场、新式书场,再经由无线电渗透至上海的每一条寻常里弄,这些身着长衫、手握纸扇的老派说书先生,在商业文化的包装下竟摇身一变,同时髦的影星伶人一起占据了大小报章杂志的各色版面。说书先生成了“海派文化”的一员。然而在这种摩登气质背后,评弹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却是值得深思的。笔者认为该时期评弹的现代化转型仍是有限的、不成熟的,并集中表现于表演形式、内容等外在结构上对都市文化的适应,并未触及内在艺术生产方式的变革,于是我们便看到外在结构的革新在很多时候实际是对内在艺术逻辑的消解,而由于更广阔的江南外部市场仍处于传统社会之中,这对矛盾关系的冲突又在流动中得以缓和。如今,当中国的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传统艺术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已日渐瓦解,如何从根本上实现艺术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变革,同时避免流于表面的盲目创新造成的异化侵蚀,是所有传统艺术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
注释:
①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页。
②熊月之:《上海通史·民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3页。
③周武:《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史林》,2003年第1期。
④次中心娱乐区有外滩地区;四川北路、乍浦路与海宁路地区;淮海路、陕西路与茂名路地区;南京西路与江宁路地区;静安寺地区;城隍庙地区;曹家渡地区;兆丰公园地区。参见楼嘉军:《上海城市娱乐研究1930-3939》,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92页。
⑤唐凤春口述材料,上海评弹团艺术档案,第24卷第24件。
⑥德惠:《有闲阶级的消闲地,平民阶级的娱乐场—书场在上海》,《生报》,1938年3月15日,第1版。
⑦楼嘉军:《上海城市娱乐研究1930-3939》,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1-22页。
⑧聿修:《上海各书场写实》,《申报》,1941年10月23日。
⑨申浩:《雅韵留痕:评弹与都市》,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64页。
⑩微言:《聆余漫谈(三) 国内播音界之现状》,《申报》,1933年11月4日,第14版。
11百批:《说会书》,《锡报》,1938年12月26日,第3版。
12横云阁主:《小世界中小书场》,《铁报》,1946年6月21日,第3版。
13吴申元:《上海最早的种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7页。
14《说书人的误卯》,《上海生活》,1939年第5期,第81页。
15 Rifkin.J, Time Wars, the primary conflict in Human History, New York, Henry Holt, 1987, p12.转引自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3页。
16评弹研究室:《周玉泉谈艺录》,《评弹艺术》第7集,中国曲艺出版社,1987年,第139页。
17青狮:《书坛琐话》,《大光明》,1930年4月18日。
18徐云志:《我的艺术生活—学艺和演出经历》,《评弹艺术》第25集,内部印刷物,1992年,第57-58页。
19横云阁主:《老伤》,《社会日报》,1940年1月19日,第2版。
20逖修:《上海的书场》,《社会日报》,1932年7月12日,第1版。
21茜萍戏作:《盛利开篇》,《上海日报》,1938年7月2日,转引自《中国苏州评弹社会史料集成》(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650页。
22笑凤:《书场生涯衰落原因》,《正报》,1939年5月25日,第3版。
23抽签:旧时书场中有竹制筹码,作为听客入座凭证,上端有孔,散场后收回套入一如烛盘之铁签内。倘听客因台上说书人艺术平庸,味同嚼蜡,不待终场,即先离座,堂倌例须向其收取书筹,故曰“抽签”。
24横云阁主:《抽签与漂档》,《海报》,1943年3月27日,第3版。
25横云阁主:《谢毓菁飞车赶书场》,《上海人报》,1947年10月26日,第2版。
26横云:《书场中的听客》,《铁报》,1946年7月20日,第3版。
27潘心伊:《书坛话堕[五]》,《珊瑚》第1卷第9号,1932年。
28横云阁主:《评话播音节目》,《导报(无锡)》,1947年10月22日,第3版。
29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0页。
30弹词名家张鉴庭曾在30年代末多次尝试进入上海市场,尽管此时已在江浙一带小有名气,但仍经过7次尝试才最终在上海站稳脚跟。
(作者:上海体育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评弹文化研究中心成员)
(责任编辑/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