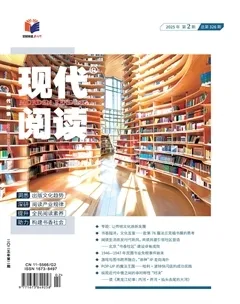纵观近代中俄之间的非对称性“对决”
中国历史就演变模式而言,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从先秦到晚清,持续在一个“超稳定结构”里得意洋洋地自我复制,是为“自我发展”;从晚清到当代,则是在一个“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中左右为难地应对挑战,是为“他我发展”—在这个关节点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与外国的对决,也是“天下”与“世界”的对决,更是不同时代的对决。
近代中国有几大痛心之事,使国人至今难以释怀:一是鸦片战争之后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军与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中国失去了香港,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一是咸丰八年(1858),沙俄与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中国失去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六十万平方千米的领土,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黑龙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船只航行;一是在甲午海战之后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日本与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失去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赔偿军费两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一是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签订《辛丑条约》,“赔款”海关银四亿五千万两……其中,“最痛的点就在黑龙江流域”。
卜键的《黑龙江纪事:内河·界河·掐头去尾的大河》,以丰富的历史内容(全书约50万字)、完整的叙事结构(正文分为21章151节)、严谨的学术态度(全书援引成书的史料90种、中文著作58种、外文译著58种,各章文末共有注释718条),讲述的就是在“他我发展”的大背景下,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万平方千米国土的前世今生,以及与此相关的各色人等间的恩恩怨怨。
就籍贯而言,笔者算是一个南人,对书中提到的南人北上,自然比较关注,心里总是在想:这些前辈千里之行,究竟所为何来? 《黑龙江纪事》告诉我们:福建水师的陈枚还率领一支擅长水上作战的家乡子弟兵,从温暖湿润的福建艰苦跋涉,来到冰雪覆盖、人生地不熟的瑷珲(今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为的就是收复故土、戍守边疆。既然身为军人,自当卫护国土。“家国情怀”大约是后人对他们的赞誉,他们自己可能未必会有更多的想法,但这并不应该也不会减少后人对他们牺牲精神的敬重。
在选材上,《黑龙江纪事》是一曲白山黑水间的“凡人歌”。我们看到最多的,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原住民、外放的官吏、从闽南北上的普通士兵、流放的文人、闯关东者,加上俄罗斯的哥萨克、沙皇的特使、身兼多种身份的科学家、到远东淘金的探险家、十二月党人及后裔,以及日本间谍、英法海军、后世的史学家与作家……不管他们各自追求的是什么,是自觉行为还是被动参与,这些人都构成了“黑龙江纪事”的主角,共同演绎着历史场景里的风霜雨雪和现实生活中的爱恨情仇。
而给笔者留下印象最深的,则是自诩“中华统绪不绝于线”的清帝国与对标西方文明的沙皇俄国之间的非对称性“对决”。这是一场中国与外国的对决,也是一场“天下”与“世界”的对决,更是一场划时代的对决。这场对决的非对称性,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历史演变的全过程,令后人痛心而又无奈。
对时代挑战的不同解读
那是一个蒙昧的时代,比如对于开矿,清廷似乎从来都有些警惕和反感,应与担心工人聚集闹事相关;同时那也是一个变革之声渐起的时代,仅仅一年之后,朝廷就批准了黑龙江将军关于开办漠河金矿的奏请。
书中以关东铁路对比西伯利亚大铁路为例,说明在19世纪后半段,中俄都曾经力图走上一条新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内部的改革之声一度十分强劲,并取得相当的进展,是为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同治中兴”。而俄廷的表现也有几分相像,但要更早开放一些,力度也更大一些。
咸丰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56年元旦),清朝皇帝连发三道谕旨,皆与黑龙江无关,说的都是国内的平叛,对于边疆大员的紧急奏报,也仍然是一味训诫—“不得轻易启衅”。而沙俄帝国此时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甚至比清廷还要沉重和严峻。清、俄两个相邻大国的主要外敌都是英国和法国,同时遭受着英法的武力逼凌。而俄国的边防与海防军队反而有所加强。到了咸丰十年(1860),清朝皇帝的心腹大患仍在于太平军,至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事情,始终未摆在前面。而沙俄帝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却是专注于远东地区的大河流域。面对同样的时代挑战,两个朝廷依据各自的理解,作出了不同的回应,其中的“道道”值得玩味。
“同”中有 “异”的朝廷
卜键通过分析乾隆皇帝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政府文书,研究两国之间的关系,探索清朝君臣的外交思路与话语模式。他引用邹爱莲的文章指出,从乾隆二十七年(1762)开始,弘历的“元旦开笔”再无变化,多少流露出正在由积极进取走向骄傲与停滞。与此相反,经过彼得大帝改革,沙俄军队脱胎换骨,不断发动对邻国的战争,俄国国土面积扩大,综合国力一直在提升,虽然还未将扩张重点转向东方,但在对华交往中已是要求渐多。大国之间的碰撞发生了,首先是外交语言的冲突,在相关议题上几乎没有一个能达成共识。
在卜键笔下,同为专制君主,乾隆皇帝博学睿智,意志坚定,自信自强,尽心地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果断镇压一切叛乱,包括思想上的反叛,在走向兴盛的同时傲视天下,故步自封;叶卡捷琳娜二世热情坦诚,富于心计,精明强悍,牢牢掌控着军队,也有着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变革务实的精神。乾隆身边文星闪耀,如王杰、董诰、纪昀、刘墉,要做实事,也要为皇上誊录诗稿,撰写敕谕,以及奉承唱和与颂圣;叶卡捷琳娜二世崇尚文明与哲学,虚心向一代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请教,在国民中开展了一场实实在在的启蒙运动。沙俄的尼古拉二世年轻时就在父皇的安排下游历各国,参与国家大政,国际视野与综合素质皆远非清帝咸丰可比。俄国在被称为“世界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战争”的第九次俄土战争败北,尼古拉一世自杀以谢天下,也给国家和继位者一个转弯的机会。相比而言,当英法联军攻破京城, “万园之园”圆明园被焚,咸丰皇帝则带着一帮后妃和近臣逃至承德,日日笙歌。“天下之主”缺乏对“天下”起码的担当,令人唏嘘。
就君臣关系而言,虽然当时两国都是君主专制,但戈洛夫金能够反问沙皇是否对现状满意,而蕴端多尔济能否反诘嘉庆皇帝则大概率是否定的。同样是独裁统治,俄廷能为臣子留下些微抒发个人情绪的空间,而清廷则无人敢给皇上撂挑子。两者在这一方面存在明显差别。
正因如此,清俄两朝在人才使用上也显示出了不同之处:穆拉维约夫家族出了一批叛逆(著名的“十二月党人”),却并未影响尼古拉一世对其破格使用,使得原本混乱沉闷的东西伯利亚很快就一派生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同治朝之前,位于京城的俄罗斯馆已经出现了多位术业有专攻的汉学人才;而清朝虽然也兴办了俄罗斯学,可并未见到有熟稔俄国和俄语的人,常常连准确的翻译都找不到。
书中写道,23岁的俄军中尉鲍什尼亚克受命调查库页岛,历时一个多月。回程时食物告尽,有十天只能以干鱼、野果与半腐烂的海豹肉充饥,向导生病,自己的脚被冻伤,拉雪橇的狗一条一条死掉。就这样,他仍然将发现的煤矿、天然港湾、河流山川特别是村屯作了勘测记录。在卜键看来,仅这份执着坚忍的敬业精神,就令多数只知酗酒赌钱、欺压部族民众的清朝官吏难望项背。在《瑷珲条约》签署之后,沙俄愈加得寸进尺。大敌当前,黑龙江将军奕山和吉林将军景淳不思抗战,不设防备,却在自己人之间掰起了手腕。他们虽无胆略,却有“政治智慧”,能预料到大块失地已难避免,朝廷和国人必会追究,必须先占地步—两位将军通过平行的“咨文”各执一端,抢占舆论高地,目的当然是面对皇帝斥责以求自保。
既无实力又无技巧的外交
鉴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理念,彼时的清朝统治者只知“天下”而不晓“世界”,对于近代以来“外交谈判”的基本理念、规则意识、制度设计、团队建设、谈判技巧、经验积累等,更是一概不知,甚至好像也不想知道。
凡是边界谈判,都需要耐力与强大意志,也要求对国际法的了解与经验。而我们看到,在这些方面,清朝大臣显然有很大欠缺。他们往往准备不足,以为能够轻松压服对手,一旦出师不利就气急败坏。就这样,谈判形势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一个灾难走向另一个更大的灾难。
在清朝的机构设置中,很长时期内只有理藩院,没有外交部。在皇帝及一班枢阁大臣看来,管他什么大使、公使、特使、专使、信使,都是贡使。一勺烩的结果是一锅粥,既无外交上必要的分寸感,更无抓住契机谋取自身核心利益的大智慧。
为了解决黑龙江地区的逃人问题,中俄在康熙时期建立了沟通机制。但是,在这一沟通机制中,黑龙江将军无权与沙俄地方当局对话,所有涉外的大事小情,都要上报朝廷,再由理藩院或大臣索额图出面交涉,包括与尼布楚督军交涉。一圈公文履行下来,时间过去许久。机制上的深层弊端,导致了外交斗争上的屡屡被动。
东北的封禁由来已久,吉林将军固庆抵任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几乎每一件奏折都是禁止垦荒,不许外地移民参与屯田、到卡外居住以及砍树垦地……各种关卡障碍,将内地人挡在黑龙江下游与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外。“一禁了之”的政策,限制了自身力量的加强,在无形中为沙俄军队和非法移民的大举侵入,打开了方便之门。
书中梳理了俄清在办理外交上的差异:俄人是片纸必存,每晤必记,认真归档,谈判时随时拿出来当棍子抡;清人则是谈判地忽南忽北,主谈者临时差遣,沟通之际现场发挥,也不留意存档。德勒克多尔济密奏皇上,已在边界卡伦加强了防范但较为隐蔽,谕旨虽未表示不满,也仍然警告他“此事关系外国”,应当“镇定办理,断不可纷纷启衅”。这是一句沿用了至少三朝的套话,说了等于没说,甚至说了不如不说—它反而限制了现场处置相关事宜官员的手脚。
在具体谈判中,沙俄坚持在北京的谈判应该以边界的实际进展为依托,使军事行动与外表谈判形成合力;而由肃顺主管的大清理藩院则还是习惯分化瓦解的老套路—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英国,批准伊格纳提耶夫由库伦进京。卜键将之评价为“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在这场不对等的谈判中,受限于因循封闭,肃顺与多数清朝官员不懂外交,在捍卫主权和保住满洲根本之地时,行为和语言多有失偏激;而伊格纳提耶夫则是深谙外交路数,一副强盗肚肠,巧取豪夺,根本不管什么公平正义。由于清朝官员基本不懂外交规则,在谈判地点、会谈时间、现场护卫、所用帐篷等方面,屡屡“出洋相”。就连为钦差大臣担任译员的传教士也觉得害臊,甚至以此作为与俄方交涉的一个理由: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类似谈判,完全不懂国际法,因此你们要忍让。
“道”与 “器”均不如人的军事
卜键告诉我们,庞大的清军看似所向披靡,实则每一仗都打得颇为艰难,取胜后忙于庆功与虚假宣传,并不知总结改进。就是在所谓盛世,清军在军事思想、军人素质、武器装备等方面与西方的差距也日渐扩大,在黑龙江地区的边防形同虚设。清代边防的薄弱,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边防卡伦的落伍,完全不具备要塞性质。这导致穆拉维约夫第一次带队侵入黑龙江地区,就一直闯到洛古镇,如入无人之境。在这样一个战略要地,清朝既无卡伦也无驿站,不设一兵一卒,任由俄军在江面上逞凶。将军特普钦也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承认:“江左俄屯处处,连接不断,而江右一带,多属旷地,并无
人居。”
无独有偶,卜键阅读甲午战争史料时,同样深深感到中日双方的不对称性:清军在战略战术上要落后许多,两军的武器配属、统帅才能和士兵整体素质也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清军失败是必然的。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对称性,1858年5月20日的天津大沽口之战,成为一场从战略战术到舰只兵器都极为悬殊的交火,成为一场碾压式的血腥杀戮。
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和反映,中外军事上的巨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制度差异的必然结果。
滞后的视野与认知
欧洲经历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列强竞起,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亦非昔日可比,而自外于世界大变局、缺少国际视野的清朝君臣,仍以蛮夷视之。对于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卜键认为虽然这句话曾广受夸赞追捧,却仍然充溢着“天朝”观念,缺乏开放胸襟和外交诚意,对国家与军队的变革没有根本性效用。晚清的朝廷和封疆大臣不缺少对外国人的警觉戒备,而独独缺少对军事革新和国际格局的了解,也缺少坦诚和大智慧。
在卜键看来,当时的清朝廷不仅昧于世界大势,甚至连自己的传统智慧也不甚了了。面对前所未见的外敌入侵,年轻的咸丰皇帝对《管子》中的“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缺少领悟,连同他那批枢阁大臣中的饱学之士,皆方寸缭乱,令无缓急,且多受洋人牵制,看似急急如律,实则多为陈词滥调,说的都是一些貌似周密严谨的套话废话。
在瑷珲谈判期间,奕山和穆拉维约夫在乌苏里江迤东滨海地区是否以及如何实行两国“共管”这一问题上的理解差异,成为一个难以跨越的概念障碍,演变为此后数年间中俄交涉的焦点,由此导致了日后的重大灾难。
第九次俄土之战后,巴黎和会的谈判结果已见诸报端,香港与南洋的中文报纸不乏报道,却未见有人奏报清廷。清朝的君君臣臣,脑子里都是如何剿灭太平军和捻军,根本顾不上僻远寒苦的黑龙江流域和更加遥远之处发生的“蛮触之争”。而“天朝上国”的习惯性思维,也使多数地方官在处理涉外事件时进退失据。加上诸多外交纠纷极大地牵扯了清朝君臣的注意力,看似见招拆招,实则仓皇应对,越到后来越显得无奈与无力。
书中提到,俄国全权大使戈洛夫金伯爵出使中国,却连清朝京师的影子都没看见,就让一个蒙古王爷给轰回来了。对沙俄而言,这是中俄关系上的重大事件,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外交风波,黑龙江左岸的最终丧失,东北大块领土被侵占,此刻已然潜伏下祸机。而在嘉庆君臣看来,却是那么理直气壮:小小汗国,花言巧语,拿一些天朝不需要的零碎玩意儿,竟固执地不愿遵照规矩行礼,来有何益?记述这一事件的中国文献很少,似乎是小事一件,《清仁宗实录》中对此居然一字未提。
这许是因为,在与沙俄进行边界谈判时,清朝的军机处没有及时查看《尼布楚条约》之类的历史档案,甚或连一份《皇舆全览图》也没有悬挂。签订《瑷珲条约》后,中方的奕山等人自知难逃秋后算账,自不会保留签字画押用的那枝毛笔;而俄方穆拉维约夫所用之笔,立即被随扈在侧的作战处处长布多戈斯基中校收藏,以纪念这个重大的时刻。两方在历史意识和时代敏感方面的差距立马可见。
……
对清帝国与沙俄之间的这种比较,揭示出同为专制制度,两者究竟差在哪里:从最高统治阶级到普通士兵,从政治传统到行政理念,从科技进步到军事变革,从外交规则到官场习俗,从时代观念到全球意识,从宏观视野到细枝末节……“非对称性”无处不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持续而广泛的非对称性,导致了近代以来的中外对决中,清帝国一败于英,二败于俄,三败于英法,四败于日,五败于八国联军……其恶果至今依然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黑龙江纪事》显示,由于历史因果关系复杂且诡异多变,以及相关文献特别是中方文献的缺失,“大历史”中仍然存在不少缺环。这无形中给了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比如:1858年5月20日,如果清军能在大沽口的近岸之地多修建设有射击孔的暗堡,如果能将炮台修筑得再坚固一些,那么这场战争或许将是另外一种结局。而这不仅可能导致出现“黑龙江纪事”的另一个文本,甚至可能影响中国近代史进程。
可惜,历史从来不会正视“如果”—它只是把命运多舛的文本、落满灰尘的史料、残酷无情的场景和不可抗拒的逻辑一股脑抛给后来者,然后转身离去。
20世纪20年代,曾任瑷珲高等小学校长的清末民初爱国诗人边瑾在《龙沙吟》诗中写道:“龙沙万里戍楼空,斑点离离塞草红。六十四屯遗迹在,何人光复大江东?”沉痛之情溢于言表。在今天的瑷珲古城里,有一座著名的历史陈列馆。在院内通向主楼的路旁草坪上,排列着大小不一的石块,石上以朱墨题写某某屯,一共有64个不同的屯名,代表着的就是那永难回归的“江东六十四屯”。
张杨在《夏威夷:帝国往事》一文中写道:1899年年底,梁启超来到已被吞并但尚未正式成为美国第五十州的夏威夷。因疫情滞留檀香山期间,他完成了流传后世感动无数国人的《少年中国说》。1900年1月,置身“新旧二世纪之界限,东西半球之中央”,梁启超感悟此乃“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于是写下壮阔的长诗《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而“心里怀想的依然是大洋西岸的‘老大帝国’和‘少年中国’”。在世纪之交的异国他乡,写下对心中故土的期盼,以“少年中国”剑挑“老大帝国”—那分明是两种历史的对决,更是两个时代的对决。
历史就是当代,转瞬已近百廿。合上卜键的《黑龙江纪事》,耳边响起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换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今天的我,多想一步跨过那条原为中国的内河,后来屈辱地变成中俄的界河,最后沦为掐头去尾的悲怆大河的黑龙江,让“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为了时代风云变幻不停的脚步,为了两百年来难以实现的牵手,为了国人心头时时泣血的海棠。
作者单位:北京市西城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