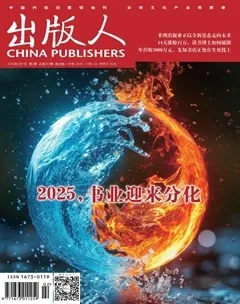在纸墨书香间“复活”千年简牍
有了一代又一代古籍出版人的前赴后继,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千年简牍在纸墨书香间“复活”,化作烛照中华文明的灯火。
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湖北云梦一个名叫“喜”的基层官吏,伴着昏黄的烛光,在竹简上一笔一画地记录着秦朝的法律和他当天的工作情况。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不曾想到,千年之后,自己生前留下的1155枚竹简重现于世,为今天的我们打开了尘封的历史。
《说文解字》曰:“简,牒也。牍,书版也。”在纸张发明普及之前,简牍作为我国魏晋以前最主要的文字载体,其记载的内容涉及古代政治、军事、历史、思想、经济、社会、法律、科技、医药诸多方面,对赓续中华文脉、传承中华文明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以来,简牍的出土呈“井喷”之势,全国各地发现的简牍超过30万枚,总字数超过300万字。高校和科研院所纷纷设立出土文献专门研究机构,创办专业刊物,简牍研究也进入了新阶段。近年来,在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简牍整理出版工作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快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成果出版利用”。《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分类做好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整理”。2023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实施的简牍高质量整理出版工程正式启动,有力地保证了简牍整理项目的出版方向、进度和质量。工程邀请有关文博学术机构和中西书局、文物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岳麓书社、甘肃文化出版社六家主要出版单位参与,其主旨是为全面摸清简牍家底,做好对简牍的保护修复、整理研究、编辑出版和数字化利用等工作。
由于简牍文物的科学保护非常困难,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和整理出版尤为迫切。为还原历史真相,无数古籍出版人与时间赛跑,皓首穷经,虽苦犹甘。
中华书局:厚积薄发打造精品
中华书局的简牍整理出版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渐成规模,21世纪进入爆发期。
据中华书局哲学室副主任石玉介绍,进入21世纪,中华书局更为关注相关选题,策划出版了数十个品种。这些品种,既有对简帛文物的集中公布、整理和注释,如《九店楚简》(2000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岗秦简》(2001年,中国文物研究所)、《关沮秦汉墓简牍》(2001年,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2012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2014年初版,2024年修订版,裘锡圭主编,湖南博物院、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肩水金关汉简校释》(2024年,李洪财)等,又有对简牍所做的带有工具书性质的字词编,如《望山楚简文字编》(2007年,程燕)、《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2018年,曾宪通、陈伟武主编)、《马王堆汉墓简帛文字全编》(2020年,刘钊主编,郑健飞、李霜洁、程少轩编),更多的则是简牍文献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
2009年,石玉入职中华书局,一直在哲学室从事传世文献中经部和子部诸子类选题的整理出版工作,真正接触出土文献,是从出版《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开始的。“《集成》初版出版于2014年,修订本出版于2024年,我真正介入这个项目,大概要从2012年甚至更早一点算起。”该项目规模庞大,成于众手,交稿时间有先有后,又因为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对出版时间有严格限制,所以,在整个编校过程中,石玉的神经时刻处于紧绷状态,唯恐因为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到位,影响了出版周期和编校质量。“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各个环节通力合作、共同努力下,最终保质保量地圆满完成了任务。让我深受鼓舞的是,我的工作得到了一向以治学严谨著称的裘锡圭先生的肯定。在2014年新书发布会召开前,裘先生特意等在会场门口向我表达谢意。这让我受宠若惊之余也长嘘了一口气——总算不负众望,没有埋没这么好的选题!”
《集成》推出后,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先后获得2014年中国出版集团年度中版好书、2014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特等奖、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图书奖、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多项荣誉。
“最初接手这个项目时,我对出土文献所知甚少,能够硬着头皮做下来,且效果还算不错,现在回想起来,只能感叹‘初生牛犊不怕虎’。2024年推出修订本,由于我对内容有了深入了解,心中有了底气,尽管时间仍很紧张,但心态较2014年要从容多了。”据石玉介绍,《集成》修订本于2024年7月出版,9月上市,正好赶上了8月湖南博物院主办的纪念马王堆挖掘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受到广泛关注。该书的修订工作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修订团队在保持原主力阵容的前提下略有变化,最明显的是加入了郑健飞、张婷、高洁等几位学界后进;第二,重写了部分篇目,包括《丧服图》《老子甲本》《阴阳五行甲篇》《去谷食气》《养生方》《太一将行图》《遣册签牌等》;第三,除了重写篇目外,其他篇目也有或多或少的改动。据修订组统计,整理图版部分(此书图版分为整理图版和原始图版)调整图版60余处,新缀残片200余片,对释文注释部分做了近千处修订;第四,原始图版部分增补了200余块残片,这些图片是2021至2022年湖南博物院马王堆汉墓及藏品研究展示中心研究人员在整理未上账的文物时发现的,之后将这些图片全部转交给了修订团队;第五,对全部彩色图版重新调色。此次修订,调整了图片亮度,较之原版更加突出了文字和帛画,给学者研读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
近年来,石玉还主要参与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肩水金关汉简校释》。在编校该书的过程中,他遇到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排版才能完整准确地呈现简牍文字的布局。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开本大小是固定的,不能随意改动,这就基本限定了一行内能够排下的文字数量,而这批简牍的整理,需要呈现出正背面、行文中的空格、分行等信息。“如何排版才能呈现这些信息颇费思量。我和作者交流了多次,也请排版人员尝试了多种版式,最终虽不能说完全达到了预期,但已经在各种限定条件下做到了最好。很多单行简文中出现多处空格,各简空格多少没办法在释文中准确体现,这是略有遗憾的地方。”
如何确保简牍整理出版的高质量?石玉指出,简牍整理的对象大都长期埋藏于地下,未曾被人关注过,需要整理者对其做断代、拼缀、编联、释读和注释,所有这些,都需要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做支撑,因此,选择合适的整理者非常关键。“在出版方面,除了严格贯彻三审三校或多审多校这些必要流程外,还须格外重视版式,尤其是图片的呈现形式,包括图片大小、位置、编号、亮度等,这些都会对读者使用产生很大影响。总之,只有上乘的内容质量配以合适的出版形式,才能打造出读者期待的作品。”
目前,中华书局有多个简牍出版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其中,《秦汉简牍系列字形谱》由西南大学张显成先生主编,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已于2025年1月出版上市。《天长纪庄汉墓木牍》计划在2025年推出。
上海古籍出版社:乘势而为光大品牌
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上古社”)在出土文献领域早有作为。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上古社就派人远赴海外,影印出版敦煌文献,近十年来对甲骨、金文、简牍、碑刻墓志等均有涉猎,且渐具规模性、系统性及可持续性。有了这些积累,在简牍“井喷”的时代,上古社乘势而为,加强品牌建设,通过实施精品战略、关注学术前沿、注重编校质量等方法,维护和光大出版社的品牌。在简牍文献首次公布出版方面,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三部书为代表。其中,2001—2012年推出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九),第一次全彩公布了竹简照片,并有放大图版和原大图版相配合,成为简牍出版物的标杆。
2009年和2010年,北京大学先后接受捐赠,获得了两批从海外回归的秦、汉简牍。时任上古社三编室主任吴旭民编审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先生取得联系,获得了出版这两批重要典籍类简牍的机会。
2014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毕业的毛承慈被编辑室指派担任《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肆)的责任编辑。《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二五”规划重点图书,能担任这么重要的图书的编辑工作,入社才两年的她非常兴奋,同时深感责任重大。进入图书审校流程后,毛承慈在前辈的引领下,首先对照竹简原文审查作者的释文是否准确,同一卷不同的整理者对竹简上同一个字的释文是否统一,然后对注释进行审读。得益于过去在学校接受过古文字、出土文献方面的系统学术训练,她对简文的释读、注释等提出了一些专业意见,得到了整理者的认可。
2017年,毛承慈开始独自负责《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的编辑工作。该书先后被纳入《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重点项目、“简牍高质量整理出版工程”重点项目及上海市“十三五”规划项目等。在编辑过程中,她遇到了三大难题。
一是释文的处理。一批简牍的抄写者往往不是同一个人,不同的人写字习惯往往不同。在整理简牍文献时,需要把古人手写的字转写为今天的楷书字形,这个工作在学界被称为“隶定”。然而,不同整理者的隶定标准不一样。“在编校过程中,要对具体的汉字具体分析,不能仅仅追求形式的整饬、标准的绝对统一,要有灵活多变的处理方式。”毛承慈说。
二是版式的处理。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包含多种文献,最特殊的是数学文献,就是数学算术题的集合。要对这些数学文献进行注释,必然要使用大量字母和数学公式。《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的其他文献都是采用传统的古籍整理版式——繁体竖排。这些数学公式如何设计是编辑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怎样才能便于阅读,不割裂读者的阅读感受?毛承慈思考了很久,也试验了很多方法,最后还是采用将数学公式另行竖排的版式设计。这样能够保持全书整理版式的统一,也不至于太浪费版面。
三是分册的处理。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的形制丰富,涉及竹简、木简、竹牍、木牍等,在入藏北大时依然保持着出土时的原始状态和位置关系,为研究古代简牍书册制度提供了绝佳的实物资料。但是,丰富的形制也对出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关于如何设计版式、怎么分册等棘手的问题,毛承慈和整理者反复商量,最终确立了尊重原始书册的物理形态且兼顾内容分类的出版形式。
“简牍类出土文献的公布整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不会毕其功于一役,出版之时就是修订之始。由于文字辨识、残简缀合、简序编连上的难度,在首次公布出版后,需要经过学界反复讨论,才能趋近于定本。”毛承慈说。上古社在重印《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时候进行了修订。在前辈编辑退休、离职后,项目小组只剩下毛承慈一个人,其他卷次的重印修订工作自然而然由她来做。“这不是简单的个别字词的改动,我们要在尽量不动版面的情况下,进行释文的修订、释文注释的修订、少量简序的改变等多项内容的调整。作者方吸收学界十余年的学术研究成果,对已经出版的一至五卷要进行全方面的修订,推出释文注释修订版。幸运的是,我们编辑室这几年来不断有新人加入,承担出土文献类图书的编辑工作,我们可以一起完成修订版的出版,向读者呈现更加完备的版本。”毛承慈告诉记者,2025年她将完成《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后续两卷的出版工作;她也正在做《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编辑出版的准备工作,预计于2026年初完成。
入行十余年的毛承慈,目前担任上古社三编室副主任。她分享了简牍图书整理出版的宝贵经验:一是对专业出版的坚守。出土文献的发现带有偶然性,但是出土文献的出版是可以规划设计的。出版社要明确自身定位, 打造长期产品线,形成品牌特色,树立强烈的精品出版意识。二是提前介入,严把质量关。简牍文献的首次公布整理具有极高的标准,相应地,对书的出版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最好在项目进入编校阶段之前就提前介入。书稿能高质量出版,除了作者方精益求精,更离不开上古社强大、专业的编校力量的支撑。三是产品线的打造。简牍图书出版并不意味着编辑工作的结束。对于独占性出土文献图书资源,要持续进行深度开发与利用,扩展选题范围,方能发挥其最大的价值。
岳麓书社:天时地利大有可为
湖南出土的简牍数量居全国之最,有近20万枚,近全国出土总数的三分之二,从战国楚简,至秦汉简牍,再到三国吴简、晋简,种类齐全、序列完整、内容丰富。这些简牍的出土或改写了历史,或填补了历史空白。得地利之便,岳麓书社从2007年开始涉足简牍出版。
岳麓书社副社长王文西清晰地记得,2007年1月,他在岳麓书社发行部以员工优惠价购买了一本《里耶发掘报告》。当时,还在读研的他已与岳麓书社签订了就业协议,但毕业论文迟迟未完稿,就是在等着补充《里耶发掘报告》公布的涉及秦朝军事问题的简牍材料,而《里耶发掘报告》的责任编辑正是他后来的师父、岳麓书社时任历史文化编辑部主任管巧灵。
王文西坦言,当年他到岳麓书社上班是怀有一点私心的。“我在读研期间就对秦汉简牍有着浓厚的兴趣,知道岳麓书社在做《里耶发掘报告》,便以为《里耶秦简》也会由岳麓书社出版,想着到这里当编辑天时地利,可以更早地接触里耶秦简的相关材料了。”尽管《里耶秦简》后来并没在岳麓书社出版,人却留下来了。直到2012年,王文西终于协助管巧灵编校了自己参与的第一本简牍类图书《湖南出土简牍选编》。“这本书虽然只是湖南出土简牍的一个选编,但是它把各个阶段有代表性的出土简牍都做了收录,能给人一种直观感受:从战国楚简一直到晋简,各个时代的湖南出土简牍是没有缺环的。做这本书对我个人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坚定了我的信心——湖南出土简牍的出版工作大有可为。”
为了完成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华大典·艺术典》上千万字的编辑出版工作,王文西曾立下“项目不完成我就不剪头发”的誓言,六年书成他已长发及腰。虽然在旁人眼里,王文西是一名实干型的古籍编辑,但在编辑之路上与自己当年挚爱的学术研究渐行渐远时,他的心底也埋藏着不舍和遗憾。“如果能把这些简牍类图书尽量做得更专业、质量更高,从而方便专家学者后续进行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我们作为编辑也算是尽了自己的一份心力了。就我个人而言,保持着与自己所学的秦汉史专业这样一丝一缕的联系,内心多少得到了一些慰藉,也可以说是一种救赎。”
2024年,岳麓书社出版《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考古发掘报告》《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研究》,总计6册,共443万字,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项目、简牍高质量整理出版工程项目、《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成果。2025年将出版《湘乡楚简选编》《长沙坡子街秦简》《益阳兔子山简牍·九号井发掘报告》《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文字编》《张家界古人堤东汉简牍》。
王文西告诉记者,“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项目在2018年立项时,长沙简牍博物馆的首任馆长、当年的发掘领队宋少华先生早已退休,健康状况欠佳。然而只要身体还行,他都坚持回单位上班,专注于主编考古发掘报告。由于用不惯电脑,宋先生坚持用楷体手写书稿,岳麓书社把手稿转录成电子文件后再交给他校对。其间,宋先生多次补充文字和图表,书稿反反复复经过了编校团队和他本人的数轮编校。他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也深深地感染着王文西,为了工作常常熬夜的两人,自然而然成了忘年交。有一天晚上11时许,还在改稿子的宋少华给王文西打了个电话,说最近身体实在有点吃不消,跟他商量想请假回河北老家休养一段时间。王文西听了心里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老人家长期抱病坚持工作,一定是医生强制要求他休养,他才迫不得已停下手头的工作。”新书发布会上,宋少华和王文西当着一众专家学者的面约定——略做休整后着手撰写《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考古发掘报告》。“宋馆长已经八十岁高龄了,他自己也说这个报告可能是他这辈子的最后一部书稿了,真的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想到这里,王文西的心里漾起一阵暖流,“这些年一路走下来,长沙简牍博物馆第二任馆长李鄂权研究员、湖南大学简帛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陈松长教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均明研究员等专家学者也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我们为他们做好服务工作的同时,也在学习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敬业精神。这种敬业精神在各行各业都是共通的”。
从2013年布局、2018年发力至今,岳麓书社在出土简牍出版领域渐入佳境。《里耶发掘报告》《湖南出土简牍选编》均获评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提名奖,《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获评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二等奖、湖南省政府出版奖,《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选粹》获评全国古籍出版社百佳图书奖二等奖。岳麓书社的人才队伍逐渐壮大,从该社走出去的青年人才邱建明2023年选择回归,从王文西手中接过了文博考古编辑部的重担。目前,岳麓书社承担了多个出土简牍类国家“十四五”规划出版项目、《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岳麓书社将在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文旅厅和湖南出版集团的指导下,联合多家简牍发掘、存藏、研究单位,共同实施《湖南出土简牍集成》出版工程。“从2025年开始,我们的出版规模和出书速度会进入一个逐步提升的阶段。”王文西感慨道,“《里耶发掘报告》是我到岳麓书社后接触的第一本书,也是我和简牍出版的缘分的开始。今后在这条路上我可能会一直做到退休,这样想来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中西书局:错位发展形成高地
2010年重新组建的中西书局,成立不久便拿下了备受学界关注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和“肩水金关汉简”两个出版项目,高起点奠定了其在战国简和秦汉简整理出版领域的“江湖地位”。2015年后,主动寻求合作的机构越来越多,中西书局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
据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兼中西书局总经理秦志华回忆,当年为了拿到“清华简”项目,中西书局做了充分细致的准备工作,前期设计了多个出版方案,还提前联系印刷厂上机进行试印,通过不同纸张、开本、装订方式的效果对比,才最终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成熟的出版方案,从而打动了作者团队。从2010年开始,中西书局以每年一辑的频率推进《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出版,从交稿到出版常常不到半年,这样的出版效率是很多出版社无法想象的。2024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推出第14辑,这批材料预计两三年内可全部出齐。
近日,中西书局出版的《睡虎地西汉简牍·质日》引起了业界关注。2024年11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孝感市考察了云梦县博物馆。云梦县,得名于“水天一色”的古云梦泽,睡虎地秦简和睡虎地西汉简牍先后在这里被发现。目前,对睡虎地秦简的整理出版工作已基本完成,睡虎地西汉简牍的整理出版工作则正在推进中。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合作编著,中西书局出版的《睡虎地西汉简牍·质日》就陈放在云梦出土秦汉简牍展的成果展示区。
《睡虎地西汉简牍·质日》的出版要从2016年11月说起。当时,秦志华和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的陈伟教授在上海碰面时,达成了出版意向,此后这个项目交给了中西书局一编室主任田颖。据田颖回忆,从2017年4月到5月的两个月时间里,为了提高传统胶片的电分精度,他们联系了多家排版公司和印刷厂,之后又花了四个月时间反复试样打印和调色,综合多方因素才最终确定了图版的印刷颜色和放大倍数。
田颖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攻读硕士学位时,正好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集中出版的时间。“当时,我一直在看《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学习了不少知识。”从2016年开始参与编辑《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六辑时,田颖就和作者团队建起微信群,便于随时沟通稿件问题,尤其是不便文字输入的字形图版问题,有时晚上十一二点还在讨论。她清晰地记得,2017年1月,担任整理项目负责人的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在微信群指导大家如何统稿。“之后我才知道当时李学勤先生还在病中,但他仍然关心着这个项目的进展,还在亲自看稿。”前辈的敬业精神令田颖十分感动,激励着她在简牍整理出版之路上一路奋进,“微信校稿”的工作习惯也被延续至今。“其实我是比较幸运的,前辈在做简牍图书时是处于探索阶段,很多坑已经踩过了。我接手项目时,中西书局已有比较成熟的出版流程和案例可以学习参考,跟整理团队的合作关系也更加紧密,再加上全员上阵,社领导亲力亲为,工作起来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难关了。”田颖说。
自成立以来,中西书局还陆续出版了《肩水金关汉简》《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悬泉汉简》《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选粹》等大批简牍类整理报告及相关研究著作,其高效和高质广受好评。中西书局为什么能在简牍整理出版领域快速崛起?秦志华如是说:“一些大社无法把简牍整理出版作为工作重心,往往只有一两个编辑在做,同时还要兼顾其他的出版门类。而中西书局是个小社,我们举全社之力去做出土文献这个板块,从项目编辑、分管领导到美编、技术编辑和相关的发行营销人员一起上阵。因此,我们完成一个项目的精细化程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秦志华1998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上古社,2000年底就担任了重大古籍整理出版项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责任编辑。二十余年他在简牍出版领域持续耕耘,其专业能力备受业内肯定。然而,秦志华坦言自己早期做书时有过因为图版问题导致整本书报废重印的教训,这让他铭记在心。此后的工作中,他严格要求自己和团队一定要把出版的前期工作做到位,从开本、版式、图片到装帧、用纸、制版、印刷,每一个环节都要把好关。
简牍尤其是湿简离开饱水环境后极易朽化变形,为了长期保存,有的须经过特殊的脱水处理,但脱水前后简牍的状况会有差别,只有最初出土的时候所拍的照片才是最接近原貌的。“我们要做的是让印出来的书能尽量保真,在开本设计和调色上尽量还原简牍的原貌,并且保证其呈现效果比实物要好,从而让研究者能够更好地使用。”秦志华告诉记者,在中西书局当编辑的一大福利就是能有机会去考古现场、实验室或博物馆的库房亲眼看到简牍的状况,“这些年我们从南到北看了不少实物,对简牍出版的理解和认识在同行当中算是相对比较深的。因为只有亲身感受到简牍刚刚出土时的样子,了解它经过脱水处理以后呈现出来的样态,了解它在博物馆里存放的现状,我们才知道以后做成书时如何以更好的状态去呈现它。这样的一手经验是很难得的”。
2000年特别是2010年之后,考古文博界和高校、学术机构合作整理的项目越来越多。“曾任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的张德芳先生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他任职期间邀请了几家学术机构一起参与西北汉简的整理,而不是将简牍材料秘不示人。”秦志华指出,这种开门整理、开门编撰的方式是非常值得提倡和鼓励的,如果只依靠一家机构去做,整理的人力、时间都无法保证。他相信,《简牍高质量整理出版工程实施方案》的出台可以推动多家机构合力提升简牍出版工程的质量。
目前,简牍高质量整理出版工程正在稳步推进中。有了一代又一代古籍出版人的前赴后继,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千年简牍在纸墨书香间“复活”,化作烛照中华文明的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