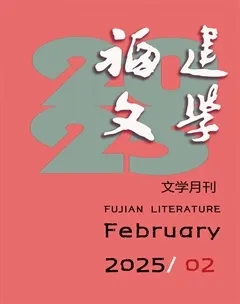樱桃园
第 一 夜
先是冻雨。
中午开始的,持续到傍晚。整个世界一直扑簌簌地响个不停,半透明的冰粒,花椒大到黄豆大的半透明冰粒,夹杂在逼近零度的水滴里,接连不断地掉下来,在地上积聚了将近一指深。六个人在集装箱工棚里打扑克,四人一组,另外两人候场,等待出现输家。铲车司机一直心不在焉,经常出错牌,让跟他打配合的对家很恼火,用很脏的粗口问候他。他心不在焉地原样问候回去。铲车司机知道,自己的心不在焉,不单单是因为持续不断送进耳朵里的扑簌声导致的。一台小太阳取暖器在几人旁边认真地摇着头,散发橙红的光,给他们送去热量的同时,也将他们的半边身子照成橙色。室外,在零度水滴的黏合下,冰粒慢慢融化、板结,形成一层坚硬的壳,牢靠地罩在大地上,就像是乌龟的壳。铲车司机中途出去撒尿,踩在坚硬光滑的冰壳上,脚底下刺溜了一下。他想起他的那只草龟。是到南方头一年,在工地即将填平的水塘捉到的。一个溽热的夏天的傍晚。后来养了七八年,最后两年周身乌黑发亮,住在一个红色水桶里,跟着他在长江下游两岸从一个工地搬到另外一个工地,后来带着一起回到老家。婚后,她说怕那东西,他就带到河里放生了。是去工地的路上,装在一个无纺布袋里面(每天都要开心“点”,袋子上印着糕点店的广告词),骑着摩托来到河边,将其放进刚好能淹没龟壳的浅水里,结果它义无反顾地游向深处,跟乌黑的河底融为一体。
天色慢慢暗下来的时候,温度也愈来愈低,小太阳开始有些吃力。几人烟也抽得更密,集装箱平整的天花板上飘浮了一层淡蓝的烟,仿佛初冬笼着一层晨雾的平原倒置在他们头顶。铲车司机再次输掉牌局,起身出门。他用平时一半的步幅慢慢来到运河边。几台大型机械,包括他驾驶的那台铲车,默然趴在开膛破肚的冰冻的大地上,身上蒙了一层半透明的冰。扑簌簌的声音就是在这时候开始消失的,鹅毛大雪悄无声息地无缝接力落下来。他从棉皮夹克胸前的口袋里掏出那张照片,一张皱巴巴的照片,看了一眼,又塞回去。一艘货轮经过,满载的散货上也是一片白。有个上年纪的船民穿着破旧的军大衣,顶着雪,用铲子费劲地清理船舷上的冰。他知道,今天晚上这路况回不去了,就给她发了条消息。接着在大雪里点了根烟,看着鹅毛大的雪花落在运河不起一丝波澜的水面上,被河水无声吞没。
一根烟没抽完,她回了条消息:知道了,注意安全。他没再回她,直到后来在集装箱工棚里躺下时也没回。躺下去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将会再次梦到那片林子,就像过去这些天那样。所以,当次日早上,就是被雾气笼罩的枝条,湿漉漉的触感还残留在他的手掌和腕的一瞬,铲车司机在半梦半醒中知道,他可以从最近一段日子的任何一天醒来。慢慢睁开眼,头顶是从一扇小窗透进来的灰白的天光,还有那片倒置的平原,烟气早已散尽。蒙在现实世界上的纱幔开始往下滑落。他终于知道自己处于何时何地。穿衣,出门站在没到小腿肚的雪地里,用脚拨开雪,底下是坚硬的冰。旁边是几棵女贞树,树叶上都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在阴郁的晨光里微微发亮。他想起梦到的那些树,浓重的雾气将它们打湿,树皮和叶片上似乎也有这样的光。
开始干活。
两辆挖掘机继续去挖那片坑。他开上那辆铲车,开始清理作业通道。各种施工车来来回回,不多久就将雪和冰碾成坚硬的整体。铲车司机花了整整一上午,才勉强清理出一条贯穿工地的作业通道。午饭后,大家又到工棚里待了会儿,抽烟,刷手机。手机上漫天是城市让冻雨和大雪弄瘫痪的消息。一点钟继续干活。他加入那两辆挖掘机,将挖出的土转运到堆放区。将近两点的时候,接到老板的电话,让他将铲车开到门口,等会儿有拖车过来带他转场。这边的工地怎么办?他问。那边先放一下,老板在电话那头说,口齿不清,明显还有昨晚的宿醉。想再问什么,已经挂了。老板是铲车的产权所有人,快五十岁了,老家也是王家营子的。年轻时,大概二十多年前,开始到长江下游两岸的苏锡扬镇等地打工,开挖掘机、铲车、推土机,打拼许多年,赚了一些钱。那时候钱值钱,老家像他一样赚到钱的还有几个,有人纸醉金迷,挥霍掉了,有人继续追加投资,行情不好的时候就亏了不少。别人指点老板买铺子,老板听人劝,把赚到的钱回老家市区买铺子,一间间买。再后来就离开南方了。铲车司机十七岁就在南方干工地,驾驭各种工程机械,也跟老板干过。老板回老家,他就跟别人干。再后来,他接到老板电话,老板说在老家又买了几台机器,缺人手。他就回来了。
拖车一个多小时后姗姗来迟。铲车司机将铲车开上拖车,然后又将自己的摩托推上去。他坐在副驾驶上,看着覆盖着一层冰壳的路面,问拖车司机,现在是去哪个工地?拖车司机算是半个熟人,扭头看了他一眼,还能去哪,去市区清雪去——全市的铲车现在都被调到市区清雪去了,你知道不?
不知道,铲车司机说。
其他许多夜晚之一
铲车司机曾无数次想象过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也就是说,尽管是当下这样一个结果,导致这个结果的,到底是有着怎样的缘起和开端,他搞不清楚。他本来可以去问她。他相信,只要他问,她一定会一五一十把事情都告诉他,就像是从竹筒里往外倒豆子。相识七年,结婚六年,孩子五岁了,他相信自己对她有足够的了解。他甚至觉得,她早就想让她的秘密暴露在他面前。可是他不想说出来,他不想让她知道,他已经知道了。他想起那只缓缓游向深处的草龟,墨色的身体最后和深色的河床融为一体。她爱看书,这一点是介绍人在介绍他们认识的时候就跟他说过的。他不太能想象得出来,爱看书是一种什么感觉,就像他不能想象其他很多事情一样。一个像他一样职校都没念完,在窗帘店上班的女的,怎么会对书那么感兴趣?他对所有有文字的东西都不感兴趣。刚认识的时候,两人去约会,在公园的长凳上,她拿出一本书,说,你念给我听,怎么样?他接过来,试着往下念。其实并没有不认识的生僻字,但他发现自己根本不能把上面的文字连成一串流畅地念出来。那是关于一个男人睡前跟一根蜡烛较劲的段落,他费了好大的劲终于念完一页,带着结束一段长途跋涉的神情看向她。她笑了,下回不为难你了。事实上他后来还试着给她读过,是在她生气的时候,他会摸起手边最近的一本书——而自从两人结婚后,家里最不缺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书,为此他专门在客厅的边柜上为她打了一排书架,他分不清这些书和那些书有什么区别——翻开,读下去,不管上面是什么,只要读下去,不用刻意假装,只要如实去读下去,不用三分钟,就能听到她在旁边抱着胳膊强忍但总也忍不住地扑哧一笑。后来,这个方法渐渐不奏效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孩子出生以后?她让他戒烟,他答应好多次,也试了好多次却是总也戒不掉?还是他那一次醉酒当着她娘家人发酒疯?还是……他想不起来了。可能是这些事情的叠加吧。他不善言辞,但这些道理他都懂。婚姻生活让他慢慢接近婚姻的真相。只有当你泡在水里,而不是站在岸上时,你才能真正感受到水。这是他某次给她读一本关于婚姻方面的书的时候,随便翻开读到的。他从不读书,但奇怪的是,那些说不上多但也绝对不至于太少的为她读书的过程,几乎每一次读的东西都能在他的记忆里留下点什么。但这完全没有改变他对书本,对读书这件事天然的排斥。但那天为什么要走进朝南卧室,走向飘窗上那些用一块蕾丝边碎花布盖起来的一摞摞书?她用那块蕾丝边碎花布去隔绝灰尘和斜射进来的阳光,现在他觉得,更可能是为了隔绝他的目光。但将本来就不会吸引他注意力的东西用一块醒目的蕾丝边碎花布遮盖起来,是不是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也就是说,遮蔽这个动作,让本来不引人注目的事情变得突出。那是个深冬的午后,阳光把空气和光秃秃的树梢过滤成金色的齑粉(是的,技校毕业的铲车司机不会使用这个词汇,但是,那天阳光被筛成那种细碎的颗粒物落在蕾丝边碎花布上时,在他心里产生的就是这种感觉),他躺在朝北卧室的单人床上,从半掩的朝南卧室门看到里面落满金色齑粉的房间,感觉到有种神秘的力量将他从床上拉起来,于是他推开朝南卧室门,走进去,走向飘窗。蕾丝边的碎花布让他觉得很舒服,他忍不住伸手去摸,那块布就从那堆书上滑落下来,掉到地板上。他弯腰捡起来,把布抓在手里,柔软的布像是软体动物一样蜷缩在他手里。将它重新铺上去之前,他随手从那些书里面拿起一本赭红色的精装书,翻开。他看到了那张照片,照片上,她和一个看上去比他们大一些的男人,脸颊紧贴在一起,男人的胳膊紧紧环在她的腰上,另一只手和她的一只手紧握在
一起。
还有她脸上的,他从来没见过的笑容。
第 二 夜
拖车是在将近五点的时候到达河滨路的。铲车司机先将摩托车推下来,停到辅路,再将铲车缓缓开下拖车。已经有一辆铲车在作业了,一个比他大很多的司机,将牢牢贴在沥青路面上的冰壳从地面上铲起来,推成堆。靠边停着一辆绿色渣土车,铲车不时将刚刚成堆的冰雪混合物一铲一铲装到渣土车车斗里。跟现场工作人员完成简单的对接后,铲车司机开动机器开始干活。
刚过九点,路上就没什么人了。铲车司机一根根抽烟,很快烟盒空了,他到路对面的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里买了包利群。还没到午夜,整个城市就已经沉沉睡去,只有遍布全市的除雪队伍彻夜未眠,机器的声音闷闷地响彻整个城市上空。抽烟休息的时候,将机器熄火,能够听到远处街道上热火朝天的声音。不时有满载冰雪的渣土车从旁边驶过,因为路滑的原因,变得格外温顺,不知去往什么地方。两点钟的时候,有人送来热粥、榨菜和茶叶蛋。四点的时候最后一根烟也抽完了。铲车司机透过车窗看到那家写着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里漆黑一片,只有“24H”的灯箱还亮着。他不死心,走过去,摸到玻璃门上挂着锁,只好忍着烟瘾继续工作。快七点的时候,天开始麻麻亮,他感觉眼前的世界出现重影,旁边从覆盖着冰盖的路面上小心驶过的私家车越来越多。他撑不住了,将车靠近绿化带停好,趴在方向盘上打盹。刚一趴下,也可能是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他感觉不出来这中间的区别,他再次跌进那片湿漉漉的林子里。
是一片水汽缭绕的林子。
分不清是黄昏还是清晨,也可能是某个雾气一直不愿意退去的白昼。枝干叶片全部让水汽浸透,湿漉漉的,泛着微光。他走在下面,枝头凝聚的大颗水滴不时掉在他的裸露的皮肤上。长满密密匝匝卵形树叶的枝条都很低,树与树之间的距离说不上很近,但抵不过枝条像鸟翅一样张开,他不得不伸手去拨开叶片,不让它们撞在脸上。他不知道这片林子有多大,他觉得应该不大,因为不时能听到说话声从某个地方传来,从说话人语气可以推测,那里一定是林子以外的地方,因为没有人能在这片林子里如此从容。可是,每当他往说话声传来的方向走去,说话声就越来越小,最后完全消失。声音消失不久,当他感觉沮丧的时候,声音又从他来时的方向响起。正当他在这样的来回往返中奔波,气喘吁吁,感觉自己将要永远被困在这片林子里时,远处传来某种体量很大的动物从枝叶间穿过的声响,还有粗重的喘息声,一起朝他靠近。他站在原地不动,那匹灰色的马再次来到他面前。而他是那么地怕马这种动物。
他醒了。有人敲车门。睁眼看到是昨天对接时那个穿反光服的。他打开车门,探出身子,对方站在地上仰头跟他说没找到轮换你的师傅,这样吧,你把车开到辅路停车位上停好,回去好好休息,六点过来吃晚饭,晚上继续。
铲车司机踩着积雪去往摩托车的路上,经过河滨公园那棵巨大的广玉兰。它合抱粗,树冠上堆积着散乱的冰雪,如同一座白色山丘。他在树下停下来,想抽根烟,摸了半天才想起夜里已经抽完了。便抬头望向那棵树。说是城里最老的一棵广玉兰。是她告诉他的。那是他们头一次见面,就在这棵广玉兰后面的临水步道边。他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十分钟,刚下到临水的步道上,就看到她如介绍人所说的那样,穿着西瓜红白碎花连衣裙,坐在不远处一张长椅上,手里捧着一本书。他朝她慢慢走近。是个初夏的黄昏,阳光洒在她身上,也洒在他身上。当他走到她身边站住时,她抬起头,眼睛看进他的眼睛里。铲车司机感觉有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巨大且柔软的东西在他心里慢慢展开。
可是现在,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进家门的时候,她正带着闺女在阳台上看雪。因为大雪的原因,学校全部停课了。怎么现在回来了?她问。马路除雪,干了一通宵,他说。闺女过来要他抱,他刚伸手,闺女被她拦住,别抱了,一身烟味。他把闺女从她手里拉过来,一把抱起来,余光里她转过头望向窗外。他用脸上的胡子去蹭闺女的脸,闺女咯咯笑,往后躲。快去睡吧,她说。他搂着闺女,淡淡地看向她,没说话。
铲车司机躺在床上并没有马上入睡。倒不是因为那个一直纠缠他的梦。过去的一整夜,他觉得猝不及防,又觉得是命中注定。慢慢地,后者占了上风。所以,早上站在那棵广玉兰下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定了主意。他现在已经不在意那个梦。或者说,他已经想到了杀死那个梦的办法。
昨天傍晚机器开动不久,刚往前清理了几十米,一个穿反光服的跑到铲车旁边,往上伸长手臂,朝他摆手。他将车停下,拉下手刹,推开车门,大声问怎么了。你下来一下,穿反光服的大声说。他下意识往后看了一眼,他刚才清理过的地方,有个男人蹲在地上,半俯下去,像是在柏油路面上发现了金矿,或者其他什么罕见的东西。他将机器熄火,跳下车,朝那边走过去。快要走到那个男人身边时,街上的路灯亮了。男人从地上抬起头,暖黄路灯光照在他脸上。那张脸就像货架上的哈密瓜一样展示在铲车司机面前。男人从地上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路灯将其影子投下来,压在铲车司机的身上。不是履带造成的,男人边拍掉手上的东西边说,履带不是问题,主要是铲斗,你看地上的坑,是铲齿造成的。你跟他们说,操作铲车时要注意点,别硬碰硬,不能为了铲雪把路面都给破坏了。好的,穿反光服的说,我让他们干活时小心点——不过你也知道,上面催命似的,让抓紧把路清理出来。一码归一码,雪要铲,路面也要保护好,男人说,然后望向铲车司机,问,你有什么问题吗?穿反光服的人转头看到铲车司机一直死死盯着男人,仿佛要将男人钉在空气里。放心,绝对没有问题,我一定都给交代好,穿反光服的边说边捏了一下铲车司机肩膀。男人转身离开,走向停在路边雪地里的一辆黑色汽车前,离开前丢下一句话:你们什么时候让我放心过。
其他许多夜晚之二
二十多年前,她十七岁,在南方一家羽绒服厂打工。她从西北老家一个干旱缺水的山村出来,坐了两天三夜的火车,来到南方濒临长江的那座城市,长那么大,她第一次见过那么多水,离她那么近。在羽绒服厂上班的那几年,她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步行三公里来到江边,坐在江边看江水,看江里来来回回的轮船。与故乡相反的东西,恰恰也解了她的思乡之情。因为路途实在遥远,在那座城市的五年里,她只回去过两次。听广播是到了那里的第一年就养成的习惯。第一个月的工资,四百七十三块,买了个飞燕牌收音机,花了四十八块钱,这两个数字她记得很精确,即便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之后每个晚上,睡前她都要把连着收音机的小耳机塞进耳朵里,常常醒来的时候,落在枕前的耳机还在响着早间新闻。第一次知道他的存在是第三年。她记得当时是非典过去不久,三个月的停工让订单积压,经常加班。她上完一个通宵,睡到下午两点多,在床上打开收音机,听到节目主持人正在念一首诗:“……是一匹骏马/它衔走了昨晚最后一片叶子/离我而去……”后来和诗人相见时,知道这首诗的稿子被他弄丢了,只剩下这几句,她在半梦半醒间记了下来,记了二十年。那是个诗歌节目,每周播出一期,除了选读知名诗人的作品,还会选读几首诗歌爱好者的来稿。那个人的名字就是跟在那首只剩残句的诗作后面的。从那往后,她每周都会在相同时间收听这个节目。她发现,那个名字经常出现在节目里。她还发现,无论是跟诗歌爱好者的作品,还是跟那些诗人的作品相比,她更喜欢他写的诗。这恐怕是冥冥中注定的,她说。她并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但是她被他的诗吸引了。大概是听到他名字的第三次吧,她在本子上,用潦草的字迹将他的诗作迅速记下来,节目结束后,她第一时间用工整的字迹抄在一个硬面日记本上。两年时间,她记下来他的约四十首诗作,大部分都是短诗。那是她离家后的第四年,她在一个吹着冷风的阴天来到江边。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她没回去,留下来加班,赚取双倍工资。省下来的路费,加上加班费,一进一出,这些钱对她贫困的家庭来说挺可观。她来到江边,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一面想念家乡贫瘠干旱结满冰霜的村庄,一面读日记本上她誊抄下来的诗,突然一个念头跳了出来:她要去见一见他。后来的人生中,每当遇到需要做出重大决定的关头,她都会来到水边。过完年,她开始实施她的计划。她先试着给电台写信。一共写了五六封信。每封信接着的都是漫长的等待。最后可能是被她的锲而不舍打动,电台给她回了一封简短的信:因为涉及个人隐私,不能将对方的联系方式给她。她没有气馁,开始积攒假期坐绿皮车去电台所在的省城。第一次吃了闭门羹,毫无意外。第二次还是没有找到她想找的那个人。终于在第五次上门的时候,在门口等到了那位电台主持人,一个快五十岁的牙齿焦黄的矮个儿男人。她难以相信读出那些漂亮诗句的低沉的声音来自他。等她从主持人的手里得到那个电话号码的时候,她没有立刻联系他,尽管怀揣着那个电话号码步行去往火车站的路上,她从无数个公共电话亭边经过。回厂里的火车上,开始落下当年的第一场雪。那年春节,她回了趟老家,回去前给父母买了部诺基亚手机,也给自己买了部。大年三十夜里,在老家的土山上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那个号码。电话那头响起一声“喂”,低沉的声音,跟她想象过的一模一样。就在那一刻,她知道某种全新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被建立起来,它没有形状,可以是任何形状,没有色彩,可以是任何色彩,没有气味,可以是任何气味,没有温度,可以是任何温度。她说,你知不知道,为了找到你,我走过了怎样一段路?然后她就哭了。他在离她打工地以北几百公里外的一座小城市,当然,相对于她的家乡而言,那里是如假包换的南方。他们在接下来的半年里,从每周通一次电话,到后来五天一通,三天一通。当最后每天都要打电话的时候,两人决定在一起。尽管两人之间有着外人看来不可弥合的鸿沟,她,一个西北大山里来的打工妹,他,一个刚毕业的道路工程专业的市政道路见习工程师,竟然成了一对恋人。她从服装厂辞职,来到他所在的城市。不久两人结婚。他们没有受到他家里任何人的祝福。她到一家窗帘店上班。一年后,两人的儿子出生了。三年后,她开了自己的窗帘店。没几年,她的窗帘店成了全城最大的一家。在窗帘店渐渐风生水起的同时,她又成为当年打工的那家服装厂羽绒服品牌的地区总代理。两样生意叠加在一起,每年都能给他们的家庭赚取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婚后第十二年,他们在城市西南方向的别墅区购置一套独栋别墅。又过了几年,他们将儿子送到国外读高中。儿子很给父母长脸,后来获得了国外一所著名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他则一边继续做他的道路养护工程师,一边写诗,还获得过一两次影响力不小的诗歌奖项。诗人在为数不算多的几次采访和发言中说,自己之所以能一路坚持下来,离不开妻子的支持和鼓励。他们的爱情在这座城市特定圈子里被很多人传颂,很多人没有见过他们,但也都听过他们的故事。她也会主动把他们的故事讲给其他人听,这后来成了她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乐趣。整个故事在她的一遍遍讲述中也越来越丰满,越来越动人。知晓他们故事的人当中,当然包括她的员工们,还可能有员工的亲友们。这让她在事业中得到某种额外的尊重。唯一令人遗憾的是,这已经不是诗歌的时代,他的诗作从来没有获得过广泛的认可。他的诗集是自费出版的。厚厚的一大本,赭红布面精装,内页开头印着当年那首只剩残句的诗作。
他还记得,那首诗的标题,叫《樱桃园》。
第 三 夜
下午两点,闹钟准时将铲车司机叫醒。醒来时家里静悄悄的。桌上有她留下的字条:去店里上班,孩子送外婆家了,冰箱里有饭,你自己热。很好看的铅笔字,天光透过玻璃杯,在纸条上投下一个边缘迷糊的光斑。他没开冰箱门,他知道自己没有耐心把冰箱里的饭菜放到灶头上,或者微波炉里,站在旁边等待它们慢慢变热。可能以后也没这样的机会了。
简单洗漱后,铲车司机出门,骑上摩托车,先到小区门口那家超市,来到厨具区,从悬挂在货架上的刀具里,挑了一把水果刀。刀柄是木头的,上下两片,用两个铆钉将刀片紧紧固定住,握在手里很趁手。他想象着这把刀划开喉咙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或者说插进躯干上的某个部位。结果他很满意,觉得那就是他想要的感觉。然后到隔壁青海人开的牛肉面馆吃了份炒饭。等待炒饭端上来之前,他从纸巾盒里抽出长长的一段面纸,将那把刀的刀刃小心地包裹起来,裹了一层又一层。裹的时候,他仿佛又看见血洇透层层叠叠的面纸,像桃花一样绽放。一盘炒饭下肚,他感觉很踏实,对自己要做的事情又增添了一些笃定。他在摩托车前抽了根烟,再次摸出棉皮夹克胸前口袋里的照片。其实不用再次确认,昨天晚上,当那个男人在路灯下抬起头的时候,他就认出来是他。这张照片从一开始锋利到能割破手,到被他摩挲到近乎柔软,他已经将上面的每个细节都刻进脑子里,不可能有任何差错。昨晚他骑着摩托车跟着那辆黑色汽车,穿街过巷来到城市西南方向的别墅区,最后眼睁睁看着那个男人走进一栋房子里。他本可以在当时就让一切有个了断的。他为自己当时的软弱羞耻了一整夜。
等他把事情办完,会不会遭受到别人的同情?他不需要同情。他害怕被同情,自从他早上在广玉兰树下下定决心之后,他希望他的行为,得到憎恨,遮天蔽日的憎恨,就像前天的那场冻雨那样。这想法让他有种畅快的感觉。这么多天来,他头一次有这种感觉。他骑着摩托车出发时,不时从忙个不停的环卫工人、除雪车、铲车旁边经过,还有满载冰雪朝城外方向奔去的渣土车。他挺好奇的,这么多雪,堆放在一起,该是多么庞大的一堆啊。他在脑海里想象了一下,得到了一个让他自己有些吃惊的结果。他为自己在这样的关头还能想这些没边的事情感到高兴,平时他是个挺无趣的男人,他听到过她和朋友这样说起过他,他当时就在旁边,抽着烟微笑。
铲车司机来到那个小区门口,像昨晚一样将摩托车停在人行道边的雪地里,脱下大衣,挂在车头。进小区时,门卫亭里的保安在空调下打盹。他绕着那栋房子,以及旁边的几栋,走了一圈,最后在斜对着那栋房子正门的一棵海桐球后面停住。一人多高的球体,可以将他完全挡住,如果他愿意的话。他点了根烟,边抽烟边注意门口。如果不出意外,那个男人最终会在他前面十几米远的停车位上停好车,走下来。到时候天色可能已经开始变暗,就像昨天晚上一样,他当时就站在行车道对面,离那个男人只有五六米。也就是一个箭步的事,他就可以近身。他在脑子里盘算着。这时一个高高瘦瘦的女人出现在客厅窗口。厚重的窗帘从两侧将那片大玻璃窗挡住了一些,那个女人的身影时隐时现。有两次,凑到玻璃前,往外打量。铲车司机下意识地将身体往海桐球后面躲,不过立刻也就知道,女人看的是外面的雪。时间一点点过去,午后似乎要露头的太阳被浓密的阴云完全挡在后面,现在是一个阴天。铲车司机觉得有些冷,不由自主一根接一根地点烟。他缩着脖含着胸,两只脚左右交替跺在冰冻的地面上。夹烟的手开始不听使唤,寒冷顺着手指往胳膊里钻。他把半截烟头丢进海桐球,把手插进兜里。烟头像一个坠崖者一样从冰冻的枝叶间滑落下去。
大门开了。女人身穿一件鲜绿色羽绒服,将大门在身后带上,朝小区门口走去,地上很滑,她走得很慢。他不由自主跟了上去,跟得也很慢。出门右拐走几步就是公园入口。女人拐进公园,往深处走去。白色的公园,每棵树,无论是常绿的还是落叶的,都如同冰雕。女人踩着没到小腿的积雪,从冰雕一样的树下走过。铲车司机跟上去,看到公园入口处是一块临时摆放的告示牌,提示路滑,请勿入园。他绕过告示牌,朝前方的女人走去,女人身着鲜绿色,在白色的背景里很显眼,铲车司机不需要保持太近的距离也不会跟丢。女人在起起伏伏的白色里穿梭,铲车司机的目光也在起起伏伏里穿梭。每当女人在公园里走过一段曲折迂回的路线后,他只需挑一个最近的路线,找一棵灌木或一个宣传牌将自己藏在后面,继续用眼睛跟上去即可。公园看上去不太大,可是女人迂回着走,走得又慢,似乎尽头遥遥无期。这让他有些失去耐心,他觉得自己在这个女人身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这个女人不是他此行的目的。当他准备放弃的时候,又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发现女人不见了。他慢慢朝女人最后出现的地方接近,那里是座栈桥,架在一个冰冻的人工湖上。他走上桥,看到在湖中间的位置,那个女人正努力从冰面上往桥面上攀爬,尽管不高,甚至能到她的腰部,可是桥上太滑了,桥面上全部是雪和冰,没有着力点。女人也看到了他,朝他求救,帮我一下,声音里有着不言而喻的恐惧。他踩着女人的脚印走到她跟前,弯下腰,朝女人伸出手。弯腰的时候,能感受到口袋里那把水果刀的存在。女人抓住他的手,抓得很紧,铲车司机胳膊一用力,女人整个人来到桥面上,趴在雪地里。
铲车司机脚底下一滑,从栈桥另一侧跌进冰湖。
当铲车司机从断裂的冰面下钻出来,女人朝他伸出手,他没去接。水其实不深,刚没过腰,他站在水里,被刺骨的冰水围绕,被破碎的浮冰环绕,冰凉的湖水从他的头发上顺着眼皮、脸颊、耳郭、脖颈往下流,他感觉到自己长久以来从来没有如此清醒。他感觉刀子所在的位置发出灼人的热量,几乎要把他烫伤。快过来,我拉你上来,女人跪在栈桥冰冻的桥面上跟他说。他花了一小会儿才弄清她的意思,趴到桥面上,把那把烫手的刀子插进还没被破坏的松软的雪里以及下面的冰层里,他似乎听到刺啦的冰块迅速破裂的声音。就在他往上攀爬的同时,女人拽住他湿淋淋的衣领,他一下子来到桥
面上。
铲车司机洗了个热水澡,在二楼属于那个去国外念书男孩的房间里换上女人给他准备的干净的衣服,都是那个男孩的旧衣服。除了袖子裤腿稍长一些,基本还算合身。他看到书桌上那个男孩的照片,对着镜头露出两片整齐的牙齿,除了闺女以外,他还没见过谁的笑容这么灿烂。想到闺女,他不禁露出微笑。他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忍不住伸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脸。
女人给他泡了一杯咖啡,滚烫,他捧在手里,坐在茶几边小口小口喝进肚子里,这才觉得发自肺腑地温暖起来。铲车司机边喝咖啡边望着前方。视线尽头、客厅深处是一个书架,尽管是阴天,巨大的落地窗还是透进足以将书架上的东西照亮的天光。是一排整齐的书。他站起来,朝书架走去。都是同一本书,赭红色布面精装,很厚,他抽出来一本,翻开,看到如下内容:
……
是一匹骏马
它衔走了昨晚最后一片叶子
离我而去
……
他认出来,就是他在自家朝南卧室飘窗上看到的那本书。
这是我先生的诗集,女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他身后。他是个诗人,女人说,声音里有种很克制的自豪感。铲车司机握着那本书,在原地静立了一小会儿。仅仅是一小会儿,已经足以让他做出一些决定。他回过身指向茶几上的空杯子对女人说,可以再给我来一杯咖啡吗?
没问题。女人转身离开。
铲车司机走到大门前,穿上自己那双湿透的棉皮鞋。离开的时候,他将门扇轻轻带上,几乎没有发出一点儿声音。
当天晚上,在马路上进行除雪作业时,铲车司机两只脚在那双湿鞋里一直没有焐热,到天亮时完全冻木。
尾 声
5月初的某个傍晚,铲车司机,不,现在应该是叉车司机,正骑着摩托车行驶在返回城区的路上。结束了六个通宵的道路除雪作业后,在跟着拖车将铲车运到运河港三期工地的路上,打电话跟老板说自己不干了。老板也没多做挽留,三天后就找到顶替他的人。他趁家里没人时,把那张蜷曲的照片放在餐桌上,用玻璃杯压住,从家里搬了出来。他给摩托车油箱加满油,漫无目的地到处闲逛了半个月,几乎走遍周边的每一条路,最后决定重新找一份工作。经过啤酒厂门口的时候,看到啤酒厂张贴的招工海报,招的是糖化工。他花了些时间向人了解糖化工是做什么的,觉得挺有意思,就过去面试。啤酒厂的招工人员得知他曾经有十几年的工程车驾驶经验时,问他会不会开叉车。他当然会。工作人员便把他带到仓储部,让他试开叉车。他好多年没碰过叉车,竟然没生疏,几个来回后便展示出令人惊叹的操作技巧。仓储部负责人当场决定录用他。尽管觉得事情有些近乎反讽,他还是答应了下来。夏天就要来了,啤酒厂正在加足马力生产,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包装好的瓶装和罐装啤酒离开生产线,他的工作就是将这些啤酒从生产车间的临时码放区叉起来,转运到仓储车间,整齐地码放好。他发现他有点喜欢上这份工作了,相比之前的铲车驾驶工作,这种对尺寸的精确要求,让他觉得有种踏实的掌控感。他酒量不行,啤酒不过两瓶而已,但他很喜欢啤酒厂里麦芽和啤酒花发酵后的味道。
他后来再也没梦到过那片雾气蒙蒙的
林子。
现在他知道了,那应该是个樱桃园。
回到正题。叉车司机骑着他的摩托车,沿着连接城区和开发区的宽阔平整的马路往前开,沐浴着初夏的春风,突然觉得下腹一阵紧绷,几乎毫无预警,膀胱竟然到了承受临界点。他感觉一整箱啤酒摔在水泥地上,泡沫横飞。旁边正好是一面是由围墙和铁丝栅栏遮挡的征收荒地。他捏下刹车,将车速降下来,越来越慢,最后缓缓停在铁丝网一处豁口处。他停好车,摘下头盔,拔下钥匙,弓腰钻过那个豁口。一墙之隔,双脚踩到尺把高的荒草。目之所及,全是绿色。他沿着铁丝网往前走,来到一堵可以藏身的水泥砖砌就的实墙,一人多高,他对着墙上的水泥砖将体内多余的液体一气排光,忍不住打了个冷战。回过头,远处是一大片黝黑的垃圾堆,最显眼的是歪在垃圾堆里的一只破沙发,四只脚陷在黑色里,整体呈现一种让人舒服的倾斜角度,让他产生了坐上去的冲动。当然只是冲动而已。他朝那片垃圾堆走过去,在向垃圾堆走近的过程中,黝黑发亮的垃圾堆,渐渐呈现某种沙粒的感觉,也就是说,那种黑不再纯粹,是一种混合色。那些较小的黑色凸起的部位或下凹的部分遮挡住的形形色色的垃圾也显露出来。各种垃圾场里应该出现的垃圾,里面一样不缺。在某个特定的距离,他的面部和手背以及鼓膜同时感受到某种触碰,前两者是某种寒气,后者是某种流水注入空旷的深潭的叮咚声。这时他恍然大悟,原来那黑色的垃圾堆,实际上是冬天那场大雪的遗存。那些黑色的沙粒,实际上是还没化完的冰雪。
于是他再次想起那场冻雨和接踵而至的大雪。据说是本地自有记录开始,六十三年来最严重的一场雪灾。无数的蔬菜瓜果大棚在冻雨和大雪的重压下垮塌,那段闲逛的日子他常常会看到垂头丧气的农人站在垮塌的大棚里抚摩冻坏的蔬果。人民医院的门诊大厅五层楼高的玻璃屋顶也在那天夜里整个跌落到地上,将圆形问诊台砸得粉碎,所幸是后半夜,没人受伤,最后不了了之。雪灾过后,他在手机上刷到过几次以本地雪山为主题的视频,原来当时市区道路上铲下来的冰雪全都运到了郊区不碍事的荒地上,东南西北各有一座,其中以城东的一座最大,号称“珠穆朗玛峰”,那段时间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人前来打卡。如果没弄错的话,应该就是这里,后来渐渐被大家遗忘。他记得,当时视频上看到的雪堆,说不上洁白无瑕,但总体上还是呈白色的。没想到,一层层化成水后,沉淀下来的竟然是这些东西。一种近似悲哀的感受从他心底暗暗升起。不过叉车司机没有沉溺其中,他转身背对那片垃圾堆,朝那个豁口走去。
他知道,外面的世界,还在等着他。
责任编辑 杨静南
张灯,本名张永明,1987年生,江苏宿迁人,从事过体育、招商等工作,现就职于苏北运河。曾获首届泥石流文学奖提名奖。本篇为其首次正式发表处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