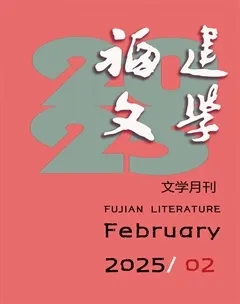赴宴
1
上完今天的课,离下课只有几分钟,她放孩子们出来玩。下午的课,越上越浮躁,她和孩子们都一样。出教室时她叫上那个总不会拼拼音的小女孩,坐在办公室门前带她读拼音。
校园宽大,校门口有棵大樟树,浓荫在地上圈了不小一片领土。围着操坪的是各样苗木,广玉兰、紫玉兰、四季桂、水杉、雪松,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观赏性植物,间隔栽种,学校环境因此优美,这是她去年8月第一次到此便决定留下的重要因素。越过三棵高耸的水杉,他走来了,提着平日常用的文件包。看来他的课也上完了,他就回家吗?在这里,只要课上完,没放学就回家是默
许的。
他坐下,在她前面约两米的地方,朝南,她是朝东。她周围一圈孩子。他们之间横着一条过水沟。她耐心教拼音,偶尔能感觉到他回过头来。她装作教得认真,不放过任何机会表扬小女孩。
上课铃响起,孩子们撒腿散了。她让小女孩也回教室。于是,从操坪到走廊,只剩了她和他。
她左前方有一棵水杉,安静立着,风过时枝叶也不怎么动。右前方是四季桂,除了一阵一阵施出香气,再不与人间相关的样子。她有些无措,不知该干什么。两米外这个男人,今天一天,她都没给好脸色,甚至他直截了当送来痴痴的目光时,她也迅速避开了眼神。
我该跟他说点什么了。她这样想,又确认一遍,是的,该说点什么。这时候她已起身,恰好看到办公室的录音机,中午被四年级一个鲁莽的孩子摔成两半,还放在那儿没人搭理。她就进去搬出来,放在腿上,翻过来倒过去看。
怎么把它修好呢?她像问自己,更像
问他。
怎么,摔坏了?他侧过脸,看她,笑着说。声音平静且温柔,没有对她今天的无理有所不满的样子。接着他又说,你今日啊,又是摔椒盒子又是摔录音机……
没等他说完,她即起身把录音机放了回去。办公桌上躺着一个材料本和一支笔,她抓起来,没有准备,脑袋里出现一句话,就写下了。要说没准备也不对,昨晚从他家回去后她就想给他打电话,有很多问题想问他,可这些问题和想问的冲动即刻被否决了。她想,还是不要节外生枝。
2
昨天,他请全校老师吃饭。
中午办公室没别人时,他认真地说,你一定要去啊,晚了你不敢骑车就让人送你回家。早几天他也提过,她没爽快答应。现在她还是犹豫的,不知此去妥不妥当。而他再三说,你一定要去,我请宝儿的老师吃饭啊,你是主角。宝儿是他的孩子,在她班上,可爱黏人,逗人疼。她于是答应,然后觉得,自己的犹豫没个模样,一句完整的推辞也没有。她有点害怕事情的走向。
要说,若最初就对他冷漠些,疏淡些,使发生交集的可能性控制在最低,也许是另一种情形呢。
第一次见他,印象不好。确定到这儿代课后第二天,也就是开学第一天,她早早到了学校,在办公室等着被安排工作。他进来得无声无息,突然的说话声吓得她身子一抖,请问,你是新来的老师吗?
她转过身,看见他,高高瘦瘦的,上身黑T恤,下身军绿色休闲裤,裤袋上挂着布条,布条穿着一串铜环,肆意得像个社会青年,她脑中浮现一个词语:吊儿郎当。可他鼻梁上架一副眼镜,有一些执着又谦逊的意思,矫正着她前一个看法。她并没明确意识到这一瞬间细微的冲突,只是感到不适,但礼貌又促使她迅速抛开这一点,去回答他的问话,是的,您是?
欢迎你!我是这里的代课老师,兼代理教导主任。他朝她伸出手,很真诚地看
着她。
教导主任好!她不太自然地把手伸过去,想着,教导主任还有代理的,还由代课老师代理,奇怪。
她把这疑问存在心里,听他的吩咐去总务处领取课本。
他是这个学校的老代课教师,代了八年,教五、六年级数学和音乐。因原教导主任去省城进修,学校其他教师不是年龄偏大就是才分下来的新手,校长就让他暂时代为处理教导处事务。他自己的意思呢?他主要是受兄弟(原教导主任)所托,硬撑。
开学不久,他和校长去镇上参加上学期期末统考表彰大会。课间老师们在办公室闲聊。有人说他今日又要满载而归,获奖专业户嘛,六年级数学全镇第二,五年级全镇第一。你一句我一句聊到他为什么能教好。几位老教师,都曾是他的老师,对他了解,说他是个怪才,讲课方式不拘一格,还带点剑走偏锋,课堂有生气,孩子们喜欢。据说有一回他讲课到兴奋处,不觉间跃上了桌子,学生并不诧异,照样听得投入。还有一回课间,学生做完操散去,他突然在水杉树下摇头晃脑、念念有词。有些孩子便停住了,转身看一眼,走回来,接着更多的孩子走回来,像骨牌似的朝他趋倒。细听,他在唱古文,用一种奇怪的腔调:“……屠惧,投以骨。一狼得骨止,一狼仍从。复投之,后狼止而前狼又至。骨已尽矣,而两狼之并驱如故……”他不仅唱,还扬手勾腿配以动作。孩子虽不全听得明白,但个个不愿走开。一位老教师说,他孙子后来上初中了,这篇《狼》背得最顺溜,他孙子还受了启发,用流行歌的曲调唱读课文,背得快。
代了这么久课,又能教,怎么不去考编?同是新来的那位教师问。
考什么编,他又没上过大学,那高中毕业证只怕还是假的呢。管财务的王老师玩笑似的说。
她只顾听,听得认真,心想他的教学方法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3
要请客,得早早准备,昨天他调了课,中午对她嘱咐完就回去了。
放学时,突然下起雨,老师们集中在大办公室前面,等他请的车子来接。她看见宝儿走在雨里准备回家,想叫住让他同车去,又犹豫了。来回踱了几步,终于还是招手,宝儿,等等,和我们一起去。
宝儿即刻掉头,跑回来,往她身边靠。管财务的王老师笑,我们看宝儿等下拉谁上车,拉谁谁就去,他肯定不拉我们。
王老师的话让她心里不安,跟老师们搭了两句话,转而去办公室改作业。宝儿跟着进去。她让他坐下,一边改作业一边和他说话。作业改完,她讲《犬夜叉》,反复学女主角,“犬夜叉,你给我坐下!”宝儿直笑。她又坐上旧风琴前的凳子,弹起《梁祝》。宝儿说,我爸爸也会弹这个。她回头给宝儿翘起两个嘴角。
从开学起,他就对她很照顾。
原教导主任的住处在大办公室隔壁,两间房,里面卧室,外面用作厨房兼餐厅、客厅。燃气灶靠前窗,摆放在碗橱上面,北边靠墙摆了三张课桌,上面有开水瓶、茶杯等。房中央有个炕桌架子,当餐桌。冬天罩上炕桌被,电炉挂进去,老师们下课便来烤火,但被上盖个桌面子,还是餐桌。他接管了外面这间,带着宝儿,还有三个外甥,每天早、午餐都在这儿吃。早餐学校管,午餐自己炒菜,饭在食堂蒸。他家不算远,晚上回去住。她呢,住镇上,不愿住校就罢了,午餐得在学校吃吧。他对她说,你跟我们一起吃饭,小李在王老师家搭餐,你到我们这儿搭。小李就是另一位新来的。
她本能地想拒绝他的好意,可她平时对其他人,也没学会拒绝,何况他是代理领导。再说,不能显得自己格格不入,看看这优美的校园吧,她是多么喜欢这里啊。
他每天很早到校,等到她来,他已把她的饭蒸了,早餐也领了。她从家里带来的菜是炒好的,玻璃瓶装着,一来就放在开水瓶旁边,中午他炒菜时热热就行。他看了说,你能吃多少,不用带菜来。她笑笑,还是天天带。
大家一起吃饭,有孩子们,热闹得很,吃起来也香。老师们闲聊时都说她长胖了。她以前真是太瘦了。她以前太不能吃了。她以前在另一所山区小学代课,吃饭根本是件痛苦的事啊。
那时候,所有老师都在食堂吃饭。每一餐他们都有特殊配菜,黄段子。除她之外的十位老师,有一对三十出头的年轻夫妇,其他都是四十五岁以上的壮年男女。在食堂,只要聚集起来,他们就离不开这一味佐料,让她无地自容。
没忍耐几天,她便独自开餐,在远离教师住宿区的教学楼二楼小隔间,她的办公室兼卧室。除非必要,从不和他们待在一起。她成了隐形人,开会、课间操等集体活动出现,其他时候,领早餐都会与他们错开,最早去,或最晚去。她住校,一个人的二楼清静也寂寞。本性有安静的一面,似乎更容易融入这种清寂,慢慢地,她除了讲课不再说话,嘴唇习惯在一切不必要的时候紧合,周末回家与父母交流也懒了,叫完“爸、妈”便无他话。嘴的懒,还殃及吃饭,常常是吃了第一口不再吃第二口,举筷放筷间完成了进食仪式,当作对一日三餐的交代。母亲目睹她的变化,日日提心吊胆,一学期结束,劝她辞职。这合她心意,虽是毕业后第一个单位,但她不想再踏进那里半步。她教得不好,期末统考,三年级英语全镇排名倒数第一,成了她工作生涯中第一个败笔。
这里一切不同,不,应该说,这里一切正常。学校与学校,教师与教师,竟有如此差别。以前那学校和教师,有点离谱,这里,是正常的。她也就变了个人,变成她倾向于成为的样子,年轻,有活力,而且她师范毕业,用老教师的话说是科班出身,前途一片光明的人呐。
可在她心底,依然没有十足的底气。全镇教师大会时,教育组领导曾点名批评过她呢,倒数第一,太不光彩啦。
现在,是新环境了,她要把这可耻的历史尽快翻篇。她同样教语文、英语、音乐。山里孩子对新语言的接受十分缓慢,她每天中午主动给他们补课,练习口语和听力。他呢,便主动承担了洗碗的活儿。原是一人洗一个星期,他说你都牺牲休息时间了,我洗个碗不应该吗?她笑着,依了。渐渐地,她竟还习惯了他每天帮她泡茶,到后来,他是领导这界限也不甚分明了。
4
这时候外面在喊,车来了。雨住了,太阳又出来了,斜挂天边。
车子一路逶迤。她沉默着,看窗外的远山和近树,溪水和稻田,天空,路和暮色。
山村风物与镇上不一样。镇上只一条稍微像样的街道,街上除了杂乱不堪的商铺与颜色斑驳、参差不齐的招牌,就剩光秃秃的水泥路,没有一棵树,甚至没有一根草。一年四季,只要不下雨就是灰尘漫天。季节界限模糊很多年后终于越来越清晰。先是春夏和秋冬不甚分明,春天不几天就是夏日,白花花的阳光与滚涌的热浪让人不敢出门;秋天呢,“天凉好个秋”才开头,突然就得架起炕桌,套上冬衣。现在怎么清晰?冬天的末尾是夏天,夏天的尽处是冬天,春、秋直接省略、隐没,这两季衣服也省了。
山村好,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呢!
她只管陷在自己的思绪里,偶尔,老师们的谈笑游进她耳翼,没停留又飘走,才让她记起不能太孤僻,便回过头来附和地笑一下。
她是去过他家的。去年开学不久,经过他家去另一老师家喝喜酒,回程他邀请同事们去玩。那时候与大家都不熟,她也迟疑。不过他盛情难却,所以大伙儿去,她就随着去了。
他家房子让她眼前一亮。一栋单层小别墅,有柱子,有台阶,有走廊,有护栏,还有绿化带和小花园。她觉得这就是一个小小庄园啊。在一个穷乡僻壤看见这个,她开怀不已,心想,在山沟沟里也能把日子过得
很美。
说到房子,这一路都是些两层楼房,在路边,在几块田的间隔间,在山脚下,在小溪旁。远观或俯瞰是可以的,是碧绿田野和绵延青山必不可少的镶嵌与点缀。但细看不得。它们一律建造得没有章法,像随意累起的积木,突兀又懒散地立在村野,仿佛大自然这块精美画布上的污点。它们都被贴满了窄窄的白色瓷砖,瓷面上深一道浅一道的污迹,也许是虫卵,也许是鼠尿,也许是屋顶长期渗水的痕迹。是了,这些房子都没有屋檐,瓷砖一贴到顶,下雨时,屋顶的水漫下来,沿窗户洗下去,墙壁和窗子都深受
其害。
绕过几重山坳,车子逼近他家。傍晚的天空下,那个绛紫色琉璃瓦的屋顶,显得格外有风度。她莫名有些激动,心头泛起甜丝。但立即,她意识到这是突兀和不该的,按捺下来。
车子在他家院子里停稳,老师们依次下车。待她下来,他母亲已经迎出。她随老师们走走看看。这栋小别墅整体是浅黄色的,瓷面锃亮,光洁如洗。屋檐以海棠红瓷砖镶边抱角。檐下整整齐齐晾一溜儿衣服。明蓝色立柱上,有梅兰竹菊四君子刻画。走廊很宽,边沿护着玫红色花瓶状栏杆。栏杆下一高一矮两排绿化带,高的四季桂,矮的黄杨。黄杨绿得喜人,好像刚被泼了染料,游跃着鱼鳞般的银光。登上六级台阶转身回望,院子开阔,一直延展到公路边。公路里侧的小园子成环状,侧抱西边偏房。园子里花草品类不一,她想,等下去辨认一番。公路外是一片平畴,种的全是水稻,蓬蓬勃勃。再远处是山,山外高一些的还是山。
往房间走,迎面是嵌着深灰色窗棂的窗户,玻璃擦得通透明亮,看得见里面的落地窗帘,被流苏络子挽着,垂在两边。左拐,正对大客厅。她抢先看见与上次不同的,客厅里不见了普通矮组合柜,多了一套崭新的黑木柜子和一套绿色皮面沙发。同时发现沙发的还有陈老师,她们相携进去。陈老师摸摸沙发,是真皮的吧?她没回答。她在想,这沙发的颜色和款式看起来好生养眼啊。
随之出了客厅,左拐,直走,经过两间厢房,到餐厅。视线往里,只见一个抛光红棕色实木橱柜竖在厨房与餐厅之间,一直竖上屋顶,印有鱼戏图的玻璃屏风镶嵌在护框里。柜台上的白色瓷碗中,装有自种的地黄瓜。此时,厨房里香气弥漫。多次邀请她来吃饭的那个人,他,正在招呼先进去的老师们。从一个老师的肩膀上看过去,他穿着白色围裙,满脸热忱。
您吃瓜呀,吃呀,很甜!他母亲依次给老师们分瓜。她接过一块,微笑致谢。然后,她感受到了他的目光。她却佯装不知,因为她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不愿像平时那样乖巧、礼貌地问候主人。她似乎有点恼,有点怒,这个男人,他的生活,丝毫不像往日里他说的那样。
餐厅挤下许多人,她有理由来到客厅歇息。坐上沙发,直面对面窗子。窗帘是清新的浅绿色,吊边绣有花纹,一分为二被络子挽着,垂曳到地,露出缩颈瓶形状的窗子。窗外一片苍绿竹林,竹叶随风沙沙作响。这些景象,本该叫人会心一笑。然而她没有获得宁静,却更添了一层愠怒。那竹叶的沙沙声,像喋喋不休的悄语,仿佛是对她的揶揄。
他母亲端了茶来,像先前请吃瓜一样,恭敬地托着茶盘。先到陈老师跟前,微微一躬身子,您喝茶呀。又移至她跟前,笑着,您喝茶呀。她赶紧起身,双手接过茶杯。
待老母亲出去,陈老师发话,真想不到,一个男人把家里收拾得这么干净。
象牙色大理石茶几,酱红色木地板,在灯光映照下幽微发亮。墙壁雪白,房顶中央百合花形玻璃吊灯洁净如新,洒下一束束粉淡的光芒。她心里奇怪的感觉浓烈起来。他曾有多少次对她说他是卑微的呀。他那样说时她对他便更怜惜一些,可是他明明活得如此精致。
她感觉到有点被他日常的话语挑逗过的味道了。
那竹叶们,窥见了她的心事,揶揄的正是这个。风经过了,所有的竹叶儿都知道了,这位初来乍到的姑娘,曾被这里的男主人日常的话语挑逗过。意识到这点,她再没办法内心波澜起伏,表面平静如常了。她蔫了,像一只在开水中烫过的茄子。
5
开饭。她和老师们一番谦让,陆续坐好。他父亲被请上正位,他母亲却怎么也不肯落座。宝儿坐在她与陈老师中间。他和他母亲一道一道上菜,都是乡村的菜品,但是配料讲究,装盘精美,看得出费了心思。上完菜,老师们的酒也斟满了。
她暗忖着,他会给我倒酒吗?她是希望的,也给他自己倒一杯,她便好敬他,或是他敬她。自然,他没给她倒,自己也没有,因为他不会喝酒,她亦不会。
他在几位男老师中间坐了,请酒请菜,没有过多的话,只有满脸谦卑与真诚,就像平时在她面前一样,叫人心生柔软的那种,第一面的“吊儿郎当”,一点儿也没有了。也许,这就是他的特质。她的眼神在他脸上流转一瞬。
男老师们离不了热热闹闹喝酒。老教师喝酒敬酒都很有风度,随意又不失礼。他们先敬他老父亲,后面就自由了,对这个一举杯,喝一口,对那个挥挥筷子,吃菜,不经意地对喝饮料的女士也抬抬盅,周到得很,不多时就把敬酒的礼数完成,之后稳如泰山,慢吃慢喝。小李老师则不然,初出茅庐,经验不足,越怕失礼越是拘谨,才起身准备敬酒,却被别人抢了先,弄得尴尬着反应不过来,幸好对方转过酒盅,朝他一扬,说一起一起。有人端着酒杯朝小李老师敬来,他正扶起筷子准备夹菜,慌忙间放了筷子,端起酒杯来,欠着身子,要站未站,赔笑说,谢谢,不当敬不当敬,神情极不自在。也罢,不再一个一个敬了。他大概是在心里这么权衡了,瞅着人家一轮敬毕,正儿八经站起来,双手举起杯子,郑重地说,我一起敬大家。等人家都端杯了,再郑重地说,先干为敬啊,然后仰头一大口喝下。
看小李老师,她就觉得极累了,庆幸自己杯子里没酒,不然这样敬,饭还吃得好吗?
即便不敬酒,饭也没吃好,没有食欲。陈老师再三让宝儿给她敬饮料,使孩子有些不自在。她深感疲于应付。老师们还在一轮一轮喝,敬酒辞一套一套,她听得云里雾里。他依然很少说话,只管添酒和请菜。见他主人也不敬酒,她就更为自己心安理得了。偶尔,她能感觉到他的眼神溜过来,又弹开。她心里更不是滋味。
好不容易把一碗饭塞进肚子,她谢席,起身离桌,从里侧走到外侧。
吃饱了吗?他抬头问。吃了很多,你多吃一点。她回答,接着却意识到说多了,恼恨自己笨拙。
走出餐厅,才知天色已暗,她要去辨认一下园子里的花草的计划只得搁下,进客厅坐着。少顷,陈老师也过来了。
饭后茶是他来送的。那边还喝酒,没人陪你们,也没电视看,线路出了问题,镇里还没派人来修,听听音乐吧。他说着弯腰放碟,起身离去时给她一眼。这一眼,天遥地远,山长水阔,叫人心惊。
蜿蜒缠绵的曲子,听得她心慌。她提醒自己注意表情,否则陈老师会察觉什么,可她笑不起来,脸上肌肉僵硬。
陈老师果真说,你怎么了?
……想回家。
6
跟陈老师进书房。
书架乳白色,不少书,厚厚的《全唐诗》、精装的四大名著,还有《丰子恺散文集》《声乐基础教程》《二胡基础教程》等等。她很快还看到了自己的书,《美学原理》《教育学概论》《百年孤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还有前几天她送宝儿的《声律启蒙》和《一千零一夜》。
她一直想看看他妻子,问宝儿,你家影集呢?宝儿从卧室找出影集。陈老师和她凑在一起。全是颇为陈旧的集体照。她搜寻他和女主人,没有。正懊丧不已,宝儿又递来三张照片。她看到一家三口。男人坐着,膝上抱着孩子。后面一个纤瘦的年轻女子,看得出是孩子的妈妈。细看那女子,皮肤白皙,眼神温柔,双手自然垂放在男人肩上。细看男人,格子衬衫,茶色眼镜,神情难掩一丝傲慢。
陈老师有一句没一句说话。宝儿,你想妈妈不?你妈妈一定很会赚钱。你们这房子,值钱呢。又凑到她耳边,建起来怕要一二十万吧,代课有什么钱,还不够日常
开销。
她还盯着照片,内心荒芜了,这才回神,却不知如何回应。然后她真的想家了,一阵一阵想哭。夜色还没完全下来的时候母亲就来电话,打在他家座机上。她从宝儿手中接过电话,母亲听见她的声音,只低吼一句,快点回来!母亲生气,她知道。母亲对他有天生的敌意,一直用鹰隼般的目光看他,当他有时候去镇上上网假装路过或找她借书时。母亲在对待他时完全没有她素有的礼貌与风度。母亲觉得她根本不应该去他家吃饭,用她的话说,你没吃过饭吗?
夜色已经完全下来了。老师们还在喝酒,他在招呼他们,餐厅的声音让她感觉没完没了。他偶尔过来一下,说,没关系,别担心,等下我送你。听他这样说,她就更想哭了,甚至突然泛起好多温柔。送我吧,送我我便是会哭的。
又进去书房,宝儿跟过来,她像在学校那样拉过他,抱着他,头靠在他的小脑袋上,那一瞬间,疲惫少了一些。
终于有老师出来,看见她站在立柱旁,说道,你怎么坐立不安!接着出来的老师也对她说同样的话。再是他母亲出来,拉着她和陈老师说,你们住下来吧。她说不出半个字,只感到身子不可抑制地下沉,像掉进了水里。
电话又响起来,她马上猜到是母亲。母亲的声音听起来竭尽全力在克制,毋庸置疑,她已经忍无可忍。母亲说请了人来接她。好,好,她满口答应,再不去想他说送她这事。她对母亲说,要接我的人快来!
老师都出来了。管财务的王老师最后一个,酒气扑扑,看她一眼,转向虚空,没来由地说,小李老师啊,你没好好敬教导主任酒,去县里赛课怕是要泡汤哦,新老师有两位,名额只一个,哈哈。
7
回到家,她有想给他打电话的冲动,想问他,你还在期盼什么?
最终没给他电话,她害怕那是他放纵的借口。接着她开始担心未来。
她没想过今天会是这样的态度,原想坦然面对,像从未发生过什么,像初相识,像他是小李老师是王老师是其他人。可她不坦然。当他们上完课,上课铃又响起,近处操坪上只剩他俩的时候,她觉得该和他说点什么了。
她脑袋里出现一句话,在材料本上快速写下:已经那么幸福的人,为什么招惹我?!
她撕下来,要去给他。走到门口却停下了,拿着纸的手指抓拢,纸随之皱起,往她手心里缩,她把它团成一个球,包在掌间。然后她重新拿起材料本和笔,走到旧风琴前,摸了摸琴键,合上琴盖,材料本铺上去,准备再写。
这一次,她坚决有力,白纸红线之上,出现了三个字。
写完她心里突然安静了,周围的世界也像失了声,直到她仿佛听见《梁祝》的曲子充盈在她周围的空气里。接着,曲调中掺进了不和谐的声音:“一狼得骨止,一狼仍从。复投之,后狼止而前狼又至。骨已尽矣,而两狼之并驱如故……”
她起身,把纸折好,走出办公室,把信递给他,接着骑上了她的玫红色女式摩托车,“嘟”地开出了校门。风扬起了她的
黑发。
责任编辑 杨静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