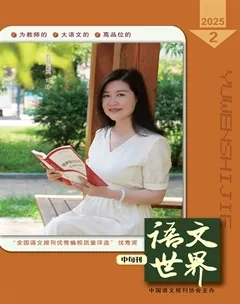《红楼梦》中称谓语的语用艺术
摘要:从语用学视角分析《红楼梦》中称谓语的运用,可以事半功倍地理解人物形象。对《红楼梦》称谓语运用的案例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实现语言积累的目的,还可以结合称谓语的多维运用功能,完成对学生思维能力与审美能力的培养,以及传统文化认同感的培育。
关键词:红楼梦的语用学;称谓语的功能;言语行为案例
在文本解读的过程中,有一类看似小众但却意义非凡的对象容易被教师所忽视,这就是文本中的称谓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无论是为了表现礼仪还是为了表现等级,无论是为了反映人际关系还是为了表达风俗习惯,都会借助于称谓语来进行。因此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借助于称谓语来进行观察与研究,不仅可以让学生了解这一语言现象,而且可以获得更多的文化认知。教学经验表明,借助于经典名著中的称谓语研究,可以更好地达成这一目标。
古典名著《红楼梦》中的称谓语使用案例众多,均极具典范性,是人情世故的反映,也有言语交际、语用技巧等隐喻。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其称谓语更含有作者创作的艺术技巧。因此,在开展整本书阅读教学中,有必要从语用学角度,梳理、分析、学习《红楼梦》中的称谓语使用艺术。
一、对《红楼梦》称谓语的范围界定
尽管学界对“称谓语”的界定不尽统一,但田惠刚的界定颇受众人认可。田惠刚认为:称谓系统由广义称谓语系统和狭义称谓语系统组成,狭义的称谓语系统是由人类在社会交际中使用的各种称呼语构成;广义的称谓语系统是泛指一切人和物[1]。
依据这样的界定和《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需要,我们主要以人物称谓语的语用功能为解析对象,在兼顾狭义称谓语的同时,以广义称谓语为个案,对其语用功能进行简要分析。
二、对《红楼梦》称谓语的语用思路分析
首先,语境给予称谓语的影响,多会涉及称谓语于语言交际角色认同、称呼对象是否在场、言语交际动机等多个层面。在动态视角下分析语境对称谓语的影响,才有可能掌握称谓语的使用技巧。俗话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人”与“鬼”的交替出现,意味着由静态语境到动态语境的转变,也意味着语境对称谓语选择的影响。
其次,需要用“言语行为”理论审视称谓语的交际功能。“言语行为”理论的精髓,主要体现在对“言语”(称谓语)与“行为”相互关系的理解上。称谓语的“言语行为”可从三个层面上理解:一是在特定交际场景中,称谓语的字面意思;二是在特定交际场景中,称谓语暗示的真实交际意图,即选择某一称谓语的原因;三是称谓语给予言语交际的后续影响。无论是否理解称谓语所示的交际意图,称谓语均会对交际产生影响。体现在小说创作上,就是文中的语言描写对人物性格的暗示,对小说情节发展的影响等。
再次,称谓语的语用预设。称谓语使用多是通过某种预设关系来实现的。当交际者预设的关系不被对方认可的时候,人物之间的言语交际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在小说创作中,就是故事情节变得复杂曲折。如:“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给了二三十两银子,难道太太就不依你?”“你舅舅”这一称谓语的背后,是赵姨娘的一种预设。然而,赵姨娘的预设却没有得到探春的认可。正是因为探春对“你舅舅”这种称谓的不认可,才激发了探春的愤怒,继而有了两人矛盾关系之语:谁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才升了九省检点,哪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我倒素习按理尊敬,越发敬出些亲戚来了……
从语言运用层面分析,探春与赵姨娘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因探春对“你舅舅”这种称谓语所示亲属关系的不认可造成的。
三、《红楼梦》称谓语的语用功能
(一)语境干涉的称谓语
对“语境”干涉下的称谓语,不能狭隘地把“语境”理解为称谓语出现的“上下文”这一客观要素,而是要从广义的层面上,把其理解为影响言语交际的各种主客观要素的组成,以及这些要素的更替。例如,交际双方的学识修养、境况、职业及交际意图、交际策略等主客观因素。
分析语境称谓语的干涉因素,还离不开动态语境称谓语干涉情况的分析。如: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当下贾母一一指与黛玉,“这是你大舅母,这是你二舅母,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妇珠大嫂子。”
语境可以干涉交际称谓语的选择。黛玉进贾府之后,外祖母对其最先使用的称谓是“心肝儿肉”这一俗语。外祖母为什么不选择较为正规的称谓语,如“外孙女”,而是有意选择这一俗语呢?究其原因,恐怕与贾母要向众人展示她对黛玉的疼爱有关。从审美的角度讲,这一次家人的团聚,再现了他们生活的温馨之美。
语境干涉下的称谓语,往往会被赋予文化传递的功能。称谓语其实就是一种称呼而已,但在语境干涉下,称谓语就会被赋予众多功能。如“大舅母”“二舅母”“先珠大哥”“珠大嫂子”等称谓语的潜台词,是对贾家家族成员的揭示。在历史文化语境下,这些称谓语都是对封建等级关系的暗示。从“大舅母”到“二舅母”的介绍顺序看,其实就是长幼关系的说明;从“先珠大哥”到“珠大嫂子”的介绍中,也可以看出封建社会里男女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对于“先珠大哥”而言,黛玉心中的陌生感不亚于“珠大嫂子”。因此,阅读《红楼梦》,必须借助称谓语,才能获取小说文本传递的文化思想信息。
语境中的称谓语还会彰显交际者各方的社会地位。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有差异,长幼尊卑更不同,这些都可通过称谓语进行暗示性说明。
称谓语通常可分为正式称谓语和略带戏谑之感的称谓语。而且,略有戏谑感的称谓语也不尽都一概具有贬义。如贾母笑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称呼,只见众姊妹都忙告诉他道:“这是琏嫂子。”
贾母口中的“泼皮破落户儿”,众人口中的“凤辣子”“辣子”“琏嫂子”等称谓,都指向王熙凤一个人。正是因为贾母的喜爱,她才能在这稍显非正式的场合里,把王熙凤称之为“泼皮破落户儿”。外祖母的地位绝非众人可比,于是贾母告诉黛玉称之为“凤辣子”即可。尽管有外祖母撑腰,黛玉也仍然感觉到“凤辣子”称谓不能出于自己的交际口中。于是,为了缓解交际中的尴尬,众姊妹才要黛玉称之为“琏嫂子”。
(二)言语行为理论下的称谓语
言语行为理论指导下的称谓语使用,需要关注称谓语的字面意思,字面意思的理解要在特定语境中完成,要透过字面意思,揣摩称谓语背后的真实交际意图。而对于那些“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交际语,真实交际意图的揣摩更为重要。
“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
分析这段称谓语的交际意义,需要从字面意义谈起。“老祖宗”这一称谓有两种意思:一是指一个家庭的祖先,二是指一个家庭里辈分最高的人。如果脱离小说文本语境的限制,就无法对这两种含义进行取舍。
称谓语的背后是交际意图,交际意图的背后是人物性格的暗示。在小说创作中,称谓语使用情况往往会与语言描写整合在一起,通过语言使用反向推导人物性格特点,这是语言描写的主要功能之一。通过人物语言描写来鉴赏人物形象,是把握人物思想性格的基本方法和途径之一[2]。
王熙凤是一个精明的女子,其“精明”的性格特点,可从她对称谓语的选择上来解读。“外孙女”与“孙女”是完全不同的称谓,本不可混用。况且,在如此重要的场合,王熙凤也不可能出现使用上的错误。但王熙凤在此却偏偏要颠倒事实,用否认的方式,假意称黛玉为贾母的“嫡亲孙女”,这是为何呢?原来,王熙凤是要借黛玉进贾府的机会,在讨好贾母的同时,拉近自己与黛玉的关系。为了讨好贾母,王熙凤先夸了一番黛玉的美貌,在做好铺垫之后,才说“竟是个嫡亲的孙女”。为了拉近自己与黛玉的关系,王熙凤还借助“妹妹”这一称谓语,把众人再次引入到对“姑妈”去世的回忆之中,她是要借助自己对妹妹的同情,拉近自己与黛玉的心理距离。
(三)交际预设中的称谓语
交际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取决于称谓语的预设功能能否实现。在称谓语承担的诸多预设功能中,称谓语对交际双方关系的预设最为常见。
在现实生活中,敬称的选择多是着意提升对方的身份。但在文学创作语境中,敬称承担的预设却不止于此。当林如海要委托贾雨村把林黛玉送往贾府的时候,林如海用“贱荆”一词称呼自己逝去的妻子。在这有违日常称谓语的背后,除了林如海有求于贾雨村之意思外,还与作者要表现林如海对黛玉的爱怜相关。
称谓语的预设功能,只有在获得交际双方认可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如,因而里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说:“刚刚的倒了一个‘巡海夜叉’,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索性连夜里偷着吃酒玩的工夫都没了。”在此语境中,若读者不知道“巡海夜叉”与“镇山太岁”两个称谓语的确切含义,他们是很难体验到众人心目中的那份牢骚感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在《红楼梦》这一经典名著当中,作者通过丰富的称谓语来表达这具体语境下的人物情感与情绪,这也给当下的高中语文教学尤其是写作教学带来深刻的启发:在课文尤其是经典课文当中涉及丰富称谓语的时候,要将其中的教育资源充分挖掘出来,要引导学生去解读这些称谓语,并且结合自己所处的生活场景或具体情境,去思考称谓语的运用,要在自己写作的过程当中研究称谓语的运用。如此学以致用,可以让学生知道称谓语的价值,从而也就可以彰显出其教育意义。
总之,《红楼梦》作为一部经典名著,其解读价值是丰富的。针对于看似是一个不太起眼的研究着力点,但真正以其为研究对象,却可以窥探其中的风土人情与人生百态,从而可以丰富对该著作的理解。在具体的教学中,阅读、教学《红楼梦》,需要结合具体语境和具体案例,才能引导学生掌握好其称谓语的玄妙和语用功能。这不仅有益于学生语言积累,也有益于学生把握人物形象性格特点,感悟古典小说创作的精彩语言艺术。
参考文献:
[1]田惠刚.中西人际称谓系统[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2]麻清珍.从人物语言角度析王熙凤形象[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23(36):54-56.
作者简介: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实验中学语文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