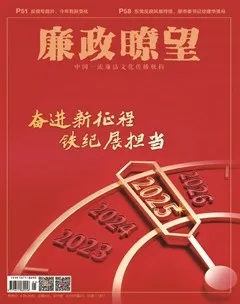错位迷局,贫困生争议背后的评选困境与破局之思
2024年11月,浙江大学一名接受贫困生补助的学生在朋友圈晒出国内外旅游照,引发热议。11月23日,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通报称,已取消其受资助资格。
贫困生资助标准是什么,获得助学金的同学能否旅游,这些同学可以买电子产品么?这些争议随着近年来人们消费习惯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受到越来越多的讨论,贫困生应该有着怎样的消费水平,人们看法不一。
大学生助学金争议由来已久,目前,国家对贫困生的资助包括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三部分。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都明确,参评者应属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前者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后者则根据学生家庭困难程度进行分档评选。学生持《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于每年9月向高校提出申请,该助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尽管评选章程明晰,但几乎每年都有学生对评选结果提出质疑。这些质疑的根据是什么?评选过程如何才能做到既合规又令各方满意?质疑者、参选者、校方以及社区工作人员都给出了不同的看法与见解。
“假贫困”泛滥,夸大填报情况就能评上贫困生?
“我们宿舍6个人都申请并评上了贫困生资格,其中还有4个人评上了助学金。”
今年11月,随着学期过半,高校贫困生认定结果陆续公布,来自四川某高校的大一学生梁雨欣发现,包括她在内的一些普通家庭学生都评上了贫困生,使她对贫困生的评定标准感到不解。“我家是正常家庭,虽然说不上富裕,但之前我也不认为属于‘贫困’,因为开放申请贫困生资格时,我发现室友都填了贫困生认证申请表,有人跟我说这个表填了也没坏处,何不申请试试看,我也就和室友一起申请了。”
然而,在梁雨欣填表时,她发现,大家并非都如实填写家庭情况。“我有好几个室友都夸大填写,所以我也就夸大了。”梁雨欣告诉记者,在她们班,一些像她一样每月至少有1500元生活费的同学在夸大家庭困难情况后,也顺利通过了民主评议,获得了贫困生补助资格。

一名家在四川,曾就读于江苏某高校的学生林炜俊告诉记者,其父母年收入在12万元左右,在几乎全班都申请助学金的风气下,他也跟风提交了家庭情况调查表。之后其班长私聊林炜俊,询问其家庭收入是否多填了一个“0”,班长透露,大部分同学在家庭年收入一栏填写的数额不超过5000元。“我当时觉得有点离谱。比如我室友就填写的家庭年收入4000元,他是江苏本地人,平时和我消费水平差不多,甚至比我还要好一点,我爸在外打工,妈妈主要照顾家里、种地,也做一些零工。在我的认知中,室友的家庭年收入怎么也不可能是4000元。”
采访中许多同学向记者反映这类情况并不少见,但几乎无人举报。“因为真的太多了……似乎已经是默认的状态了,没人想着去改变。”在吉林上大学的杨丽丽告诉记者,按照贫困生认定标准,她的家庭经济情况也符合,但她没有选择申请贫困助学金,“我妈妈说过还有很多比我生活更困难的人。我对我的生活是满足的,在这种情况下还申请贫困补助对于我来说是不正直的行为,看到贫困生认定表下面的‘情况真实’承诺,我在道德层面不接受违心填报的行为。”
除了夸大贫困情况跟风申请,“造假”现象还可能存在于评议环节。在广东上大学的王可阳向记者提到,自己所在学院贫困生认定小组学生代表故意修改他人提交的贫困生评定调查表,并将自己与另一名同学的家庭经济情况改成符合贫困生认定标准,最终评上了贫困生。直到第二年贫困生认定机制修改,申请人的贫困生评定调查表要求附电子签名,部分贫困生的原生家庭情况与上一年不一致,学生代表的行为才被曝光。
评议代表因私利或为他人牟利而操作贫困生名额归属一事并非个例。“民主评议”如何保证公平性,评议小组如何被监督,这些都是一些同学提出异议的理由。一些学生认为,评议过程为保护申请人隐私不会公开,这给了评议小组操作空间。在某社交平台上,一位博主对贫困生认定这样质疑:“评议小组都由同班同学组成,同学之间关系有亲疏,如何保证评议小组不为关系好的同学说话?”
量化难,监督难,评选机制仍有漏洞?
今年10月,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的通知》,提高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从2024年秋季学期起,将本专科生(含预科生,不含退役士兵学生)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3300元提高到3700元,具体标准由高校在每生每年2500—5000元范围内自主确定,可以分为2—3档。而国家励志奖学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生从二年级起可申请,每人每年5000元。
北京某985高校辅导员崔成告诉记者,该校贫困生资助标准今年核定为三档,第一档要求学生家中需有重大经济困难,如低保户、家庭主要劳动力有重大疾病或主要家庭成员为残障人员,抑或存在单亲家庭或孤儿无其他亲属资助的情况;第二档则为家庭经济状况较差,年收入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的同学,该档学生家庭成员中有疾病或残疾,但经济负担相对较轻,又或家庭供养两名以上在校学生,经济压力较大。“第一档最好认定,因为该类人员基本有国家各类保障证明,第二档争议一般也不大,家庭情况证明也较好提供。”崔成告诉记者,一些认定争议主要存在于第三档,该档资助的同学为,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年收入略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家庭成员中有轻微疾病或残疾,对家庭经济有一定影响,经济压力较大,“这一档也将家庭生活费用较高,但尚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同学纳入资助标准,一些人认为,家庭生活费用较高不好判定是否为超标准消费,且尚能维持基本生活的标准也很模糊。”

崔成表示,第三档评选标准很难量化考虑,所以多依靠民主评议小组综合该同学在校消费情况和其提供的材料来判断。“但一些同学的消费情况比较模糊,不同学生提供的材料信息量也有差异,能提供多项证明的同学肯定更有优势。经过评议小组评定后该结果还会上报学院进行二轮审核,之后学院还要上报学校贫困生认定委员会再次审核。”崔成告诉记者,其所在学校为部属高校,贫困生补助名额较多,并不按班级分配名额,最终的贫困生认定数量会由全学院通盘考虑。“现在许多学生家庭情况都还可以,近几年获得贫困生认定的学生数量都不多。”
除了量化标准问题,记者发现评选程序也并非没有漏洞。崔成以及一些已经获评贫困生资格的同学告诉记者,因为学院负责相关工作的老师人手不多,且申请贫困生补助的学生总体数量多,学校在核查方面只能做到确认贫困证明材料是否有出具证明的单位鲜章,并不会联系学生生源地的民政部门、乡镇、街道办事处或父母所在单位一一确认。学校虽然能通过信函索证,但此方法核实成本过高,各高校一般都没有这样复核,除非有人举报或公示期间有人提出异议,学校才会进一步复核。
此外,记者咨询天津某街道办干部,对方表示,街道办是不会给学校的贫困生认证表盖章的。“首先,街道办只能开已认证的低保户证明,其他证明不能开。其次,盖章需要核实学生所填信息,社工部对社区职责有明确规定,社区不能随意去核实证明。”
在调查中,不止一名受访学生向记者提到,有非贫困生托关系盖假章领助学金的情况。有基层干部向记者表示,社区会有托关系盖章的情况,不过,不同学校的表格不一样,也没有明确的贫困生认定标准,盖与不盖很难把握,“也有一些家长闹,说不盖就是为难人。”
名额错位,怎样认定才能精准定位贫困资格?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学校贫困生名额多,甚至“用不完”,而另外一些学校却存在名额不够用的情况。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陈永杰长期研究大学生失业、大学贫困生等方面问题。他发现,助学金也有“地域差异”。“除了国家助学金是按照统一标准下发到各高校外,其他助学金均存在一定的校别以及地区差异。在宏观层面,这种差异与贫困生在不同高校中的分布规律并不相符。目前高校针对贫困生的帮扶资金并非按‘人头’分配,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按学校的‘层次’分配,这就造成不同类型高校在资金发放问题上的空间错位。”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名额的“挤占”与“浪费”也体现在此处。在贫困生资助资源有限的高校里,有办法盖到章、能获得更多证明的同学,通过各种方式挤占贫困生名额。而在贫困资助资源相对充裕的高校里,非贫困生占领空缺名额领取贫困助学金也成了普遍现象,学生们大多对此习以为常。
采访中有老师认为,由于我国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各地人均GDP收入差别较大,各高校难以用统一的贫困生认定标准进行量化,一直以来各高校的贫困生认定工作,基本是依据教育部意见的基本原则、认定依据、工作程序等相关要求,立足于各自院校贫困生资助工作的实际需要,自行出台一套贫困生认定方式、方法与标准。目前各地高校在认定程序上有一定的“自由发挥空间”,但大多数高校是按照程序规定进行“固定动作”的审核,可能存在不深入、不严谨的情况,要破除大学生贫困认定乱象并非易事,还得从细化明确认定机构职责,并统一规范高校认定程序和制度入手。
一些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出台了具有差异化的实施办法。2023年广东省颁布《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其中提出,组织认定环节规定“交叉审核”,认定复核环节实施“全面复核”等办法。记者注意到,该办法制定了各院校贫困生认定的规范标准与监督制度,如联动各级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乡村振兴、残联等部门为高校贫困审核提供有效数据资源支撑,定期或不定期对二级院(系)进行监督检查,规定完善第三方的监督检查制度等措施,旨在降低认定成本并保障贫困认定的精准规范化操作。而针对贫困认定程序中学生的“失信”行为,办法提出建立健全失信行为的惩戒机制,明确学生资助资金申请、认定过程中相关责任人及申请学生主体的法律责任。
此外,有高校老师也向记者反映,在今年国家出台《关于调整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的通知》后,一些高校也在积极探索完善精准认定贫困生的模式。在贫困生认定程序中的认定环节,除民主评议和信函索证的认定方式外,高校也正在结合个别访谈、大数据分析、量化评估等多元认定方式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精准度。
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学生资助体系,但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在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和加大投入力度的基础上,仍需做好多方面工作。一些负责贫困生认定工作的老师也向记者反映,许多高校正探索从“保障型资助”体系向“发展型资助”体系的转型。“这种体系强调受助学生在受助过程中的主体性,通过劳动获得报酬,并提升自身的素质与技能,有利于受助学生的长期心理健康。”一名来自中部某985高校的老师表示。(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