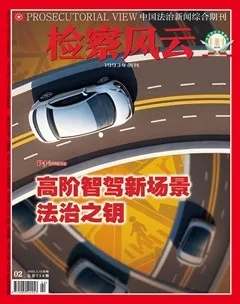论行刑反向衔接中不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

随着轻罪治理时代的来临,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检察机关对于轻微刑事案件的起诉秉持着审慎克制的态度。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自2019年到2023年,不诉率从9.5%升至25.5%。但不起诉仅意味着不用承担刑事责任,针对被不起诉人的行为仍然可能需要追究其行政责任,这就需要行刑反向衔接机制的介入。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内涵和价值取向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内涵
所谓“一事不再理”,是指就特定被告人之特定犯罪事实,只应受到国家一次性追诉,国家不得重复追诉相同被告人的同一犯罪事实。在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的表现便是同一案件之禁止再诉,包括判决确定前禁止再诉(即禁止重复起诉)和实体判决确定后禁止再诉。对于一事不再理的生效时间节点,一般认为一事不再理与侦查阶段无关,相关的理论探讨也都聚焦于起诉及之后的审判阶段。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价值取向
一事不再理原则以保障人权为价值取向。随着现代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公民的人权意识已逐渐加强,每个公民的权利都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维护,被追诉人也不例外。一事不再理避免被追诉人再次经历刑事诉讼程序所带来的不便,使被追诉人尽快回归正常生活。如果检察机关可以就同一行为对行为人反复追诉,这就会导致被追诉人可能反复经受包括逮捕、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刑事诉讼作为一种国家强制性活动,其启动与进行势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被追诉人的正常生活,司法机关应依法使用刑事司法权不给公民个人权利造成不必要的损害,以实现国家公权力的自我限制和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
“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分析
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具有其理论正当性,但能否适用到行刑反向衔接中需要深入研究和讨论。笔者认为,行刑反向衔接不应当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理由如下:首先,一事不再理原则对行为人的保护开始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时。换言之,对于不起诉的案件,检察机关后续是可以提起公诉的。既然还能追究刑事责任,那么追究其行政责任也自然可以,因此在行刑反向衔接中没有适用一事不再理的余地;其次,从一事不再理的价值取向和公平原则来看,在行刑反向衔接中也不应当适用一事不再理,具体论证如下。
从权利保障方面看
行政处罚程序对公民权利的限制远小于刑事诉讼程序。
程序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主要表现为强制措施的适用。在理论上,根据作用对象的不同,强制措施可以分为对人和对物两大类,前者主要是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后者主要是限制公民的财产权。
在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方面。行政机关主要适用盘问、传唤、保护性约束措施等限制程度低的行政强制措施,很少适用立即拘留这种限制程度高的行政强制措施。刑事侦查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传唤、拘传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采用刑事拘留,刑事拘留期限也往往满30日并且除刑事拘留外还有逮捕羁押措施。
在限制公民的财产权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三十二条的规定,行政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期限最多为6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则没有规定刑事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最长期限,司法实践中查封、扣押、冻结措施通常伴随着不起诉书的作出或判决书的生效被解除,查封、扣押、冻结的期限短则数月长则数年。
由此可见,行政处罚程序对公民所造成的限制,无论是在人身自由还是财产权方面都远不如刑事诉讼程序。除此之外,反向衔接是一次性的,即行政处罚程序也只会启动一次,因此行为人在反向衔接之后其生活即可回归正常。
从事实认定方面看
行政违法事实的认定难度低于犯罪事实的认定难度。
从证据审查角度看,刑事诉讼先严格规定刑事侦查的程序要求,然后将违反程序要求获取的证据分为可补正和不可补正两类,对于无法提供补正和本就不可补正的证据予以排除。相比之下,行政处罚程序一方面对于行政调查的适用条件、适用手段、适用对象、适用期限等方面的限制较少,另一方面对于证据进行审查也并不如刑事诉讼严格,从而保留更多的证据来认定行政违法事实。
从证明标准来看,刑事诉讼中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有着最高的证明标准,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在行政处罚领域,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没有规定行政处罚程序的证明标准,但实践中的具体运用通常是低于刑事诉讼中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这也是与行政处罚对个人权益影响程度相适应的。
由上可知,行政违法事实的认定难度是低于犯罪事实的。那也就是说,在检察机关因证据不足而对被追诉人决定不起诉后,并不意味着对其行政处罚同样缺乏证据基础。行政机关完全可以依据公安、检察机关已经收集、固定的现有证据,再根据需要调查收集其他证据,然后依法对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
从合理处置方面看
行刑反向衔接中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将违背公平原则。
此处的公平原则是指:“实施行政处罚必须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特定的行政主体在决定和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平等地对待当事人各方,平等、公正地适用法律﹐同样事项同等对待。”所以,如因一事不再理原则否定行刑反向衔接,将导致行为处置的不公平。例如,针对某一犯罪行为,检察机关因犯罪情节轻微而酌定不起诉。在没有反向衔接的情况下,对行为人将没有任何实质性惩罚。但是,如果该行为危害性更低一点而不构成犯罪,则相应机关将对行为人施以行政处罚。这就导致了危害性更重的行为因检察机关不起诉而惩罚缺失,更轻的行为则被处以行政处罚。由此可见,如因一事不再理而否定行刑反向衔接将违背公平原则,造成处置结果的失当。
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关于一事不再理的规定。相反,无论是再审制度还是重新起诉制度,均肯定了对于同一犯罪行为的重复追诉效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的情形包括: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因此,在由“刑”到“行”的行刑反向衔接领域,不应该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编辑:沈析宇" " 17555627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