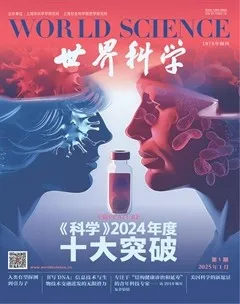科学侦探的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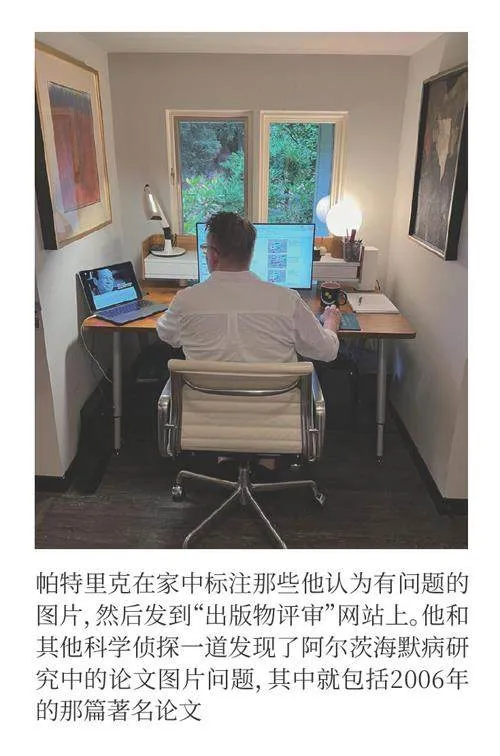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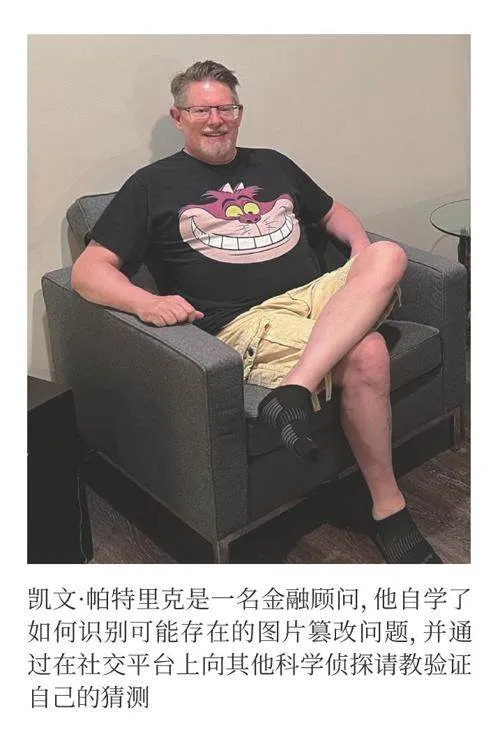
当一篇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论文接受审查时,纠正科学记录意味着要与更大的问题作斗争。
2023年7月一个闷热的日子,一群志同道合的数据专家围坐在布拉格老城历史悠久的“金老虎”酒吧的一张桌子旁。他们在互相调侃谁看上去最像中世纪的人,空气中洋溢着一股温和但又带着点愠怒的情绪。这个数据专家小组正在讨论科学出版物中篡改图像、伪造数据的问题。没过多久,就有人拿起一部手机在众人中传阅,屏幕上是一张黑白图像,篡改痕迹颇为明显。酒过三巡之后,他们离开了酒吧,沿着铺满精致石板的街道前行。众人心中满是之前基本只能在网上分享的挫败感。“这就是一个有毒的垃圾场,”其中一位网名为“扁椿象”的意大利科学家这样评价科学,“不再和好奇心有关,纯粹就是一份工作。”
这群人就是媒体口中常说的科学侦探,来自美国、乌克兰、新西兰、英国等各个国家,致力于揭露科学文献中潜在的造假行为。
参加这次布拉格聚会的人,以及其他未能到场的人,各有所长和偏好。有些人热衷于揭露统计数据作假;有些人则热衷于寻找篡改的图像;有些人是本专业的学者;有些人则是义务参加侦探工作的普通人。不过,他们所有人都卷入了一场没有终点的科学核心之争。在这场斗争中,发表论文的压力和名利的诱惑催生了无数有问题的图像和统计数据,更严重时甚至会动摇相关研究的支柱。这个问题在诸多科学领域都存在,只不过有些领域受到的影响更大。“阿尔茨海默病最火的那篇论文是假的。”夕阳西下,“扁椿象”在离开“金老虎”酒吧的路上说。这个观点并不新鲜,在场的所有科学侦探之前都听过。
他质疑的那篇论文2006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内容支持了一种理论:某种淀粉样蛋白的增殖会导致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所谓的“淀粉样蛋白级联假说”(ACH)。这个理论吸引了数十亿美元进入缓解阿尔茨海默病的抗淀粉样蛋白疗法。
然而,15年后,一些科学侦探注意到那篇论文中某些关键图像存在问题。换句话说,核心数据可能造假。在这些质疑声出现后,这个领域的科学家就那篇论文的重要性开始唇枪舌剑。有些人认为,支持ACH的里程碑式发现已经不再可靠了。还有些人则坚称,从来没有把涉事论文当作支持ACH的证据。
无论如何,没有人可以否认,成千上万的科学出版物引用了那篇论文。于是,在科学侦探们眼中,这篇论文大获成功更加凸显了调查科研论文中篡改行为的重要性。“当我们查看被引用论文,尤其是那些被引用了几百次、几千次的论文时,我们需要做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让读者更容易地发现其中的问题。”在范德比尔特大学从事阿尔茨海默病研究,同时也亲临一线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神经科学家马修·施拉格(Mathew Schrag)说。更正或撤稿就是满足这个需要的操作,同时也符合科学规范。
实际上,对这篇论文的质疑揭示了一条多年来始终在侵蚀科学诚信的裂痕。而提出这些问题的科学侦探更是觉得,他们做的不只是小小地纠正错误,而是在为更大的真相而战。新西兰业已退休的知觉心理学家大卫·比姆勒(David Bimler)——他之前曾化名斯莫特·克莱德(Smut Clyde)——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都希望科学的理想能够恢复到更接近过去的样子。”
至于他们是否能为这个理想做到点什么,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群科学侦探是受一位名叫凯文·帕特里克(Kevin Patrick)的金融顾问的邀请在布拉格聚会的。和这次聚会的其他成员不同——除了比姆勒和扁椿象之外,还有以识别被篡改图像闻名的伊丽莎白·比克(Elisabeth Bik)和其他数人——帕特里克没有科学背景。他说,虽然投资工作偶尔会要求他关注医药股,但实际情况是多年之后的一次偶然事件让他发现了一个追踪有问题、不可靠论文的网站“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据帕特里克回忆,他很快就通过“撤稿观察”找到了另一个叫“出版物评审”(PubPeer)的网站,在那里,他见到了一篇又一篇论文篡改图像的例子。
阿尔茨海默病最早报道于1906年。当时,一位名叫阿洛伊斯·阿尔茨海默(Alois Alzheimer)的德国精神病学家观察到有个病人的精神状态从偏执发展到好斗再发展到迷糊。在她去世后,阿尔茨海默在她的大脑中发现了奇怪的斑块和缠结。之后,更多类似的病例接踵而至,于是到了1910年,阿尔茨海默病被正式列为一种疾病。我们常说的“痴呆”是各种认知障碍的总称,它们都与年龄高度相关,而阿尔茨海默病是最常见的一种痴呆病症。
1984年,两位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叫作β淀粉样蛋白的蛋白质(Aβ),它们正是淀粉样斑块的主要成分。这个发现催生了一种观点:Aβ是导致神经元死亡的缠结的成因,因而也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标志性特征。这就是所谓的“淀粉样蛋白级联假说”。在许多研究人员看来,这个假说为解决阿尔茨海默病问题开辟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并提供了一种潜在的治疗途径:抑制Aβ的产生,就能阻止病情恶化,甚至可能逆转病情。
这个理论让科研界和产业界人员都为之着迷。生物科技公司“雅典娜神经科学”和制药巨头礼来公司培育出了携带人类淀粉样蛋白突变基因的小鼠。它们的大脑内满是斑块,并且丧失了记忆能力。《纽约时报》一篇令人震撼的报告指出,小小的雅典娜神经科学公司凭借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如果能开发出有效的阿尔茨海默病药物,可能带来每年10亿美元的收益——或许将成为“咆哮的老鼠”。很快,科学家、制药公司和投资人都在ACH的研发竞争赛道上全力以赴了。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个方向。范德比尔特大学神经科学家马修·施拉格(Matthew Schrag)就是持怀疑态度的人之一。施拉格拥有医学学士和博士学位,很早就进入了范德比尔特大学记忆和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中心,并且在2010年代中叶开设了自己的研究实验室。他还在耶鲁大学细胞生物学系接受过一段时间的科研训练。在那里,科学方法的严谨令他心醉。
2022年,那篇2006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论文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审查。那时,施拉格就已经意识到,不利于ACH的证据远比支持它的证据有说服力。首先,被视为阿尔茨海默病标志性特征的淀粉样斑块在非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大脑中同样可能出现。另外,没有任何研究证明,淀粉样蛋白的积聚是人类记忆障碍一定会出现的前兆。
更为重要的是,事实摆在眼前:ACH主导了阿尔茨海默病研究领域近20年,但完全没有开发出能够逆转、阻止乃至有意义地减缓这类病症进程的疗法。没有任何临床试验证实靶向β淀粉样蛋白能够阻止或是显著减缓阿尔茨海默病的进程。尽管如此,制药公司仍在前赴后继地推出没有任何实际产出的候选药物。
2021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在一片争议中批准了一款名为“阿杜卡努单抗”(Aducanumab)的Aβ靶向药物。这个决定导致三位参与药物审查的科学家辞职。其中一位研究人员、哈佛医学院教授阿隆·凯赛尔海姆(Aaron Kesselheim)称:“在我的印象里,这应该是FDA最糟糕的准药决定了。”
在此之前,阿杜卡努单抗的制药商已经因为这款药没有表现出良好疗效而停止了临床试验。然而,研究人员之后又对更大的数据集做了分析,结果显示,这种药对接受剂量较高的患者有积极影响。FDA咨询委员会强烈反对批准阿杜卡努单抗,但决策层没有理会。他们基于阿杜卡努单抗可以消除淀粉样蛋白质斑块这个事实就加速批准了这种药物,而不是因为它可以延缓阿尔茨海默病的进程。当时的FDA神经科学办公室负责人比利·邓恩(Billy Dunn)于2023年离职并进入了普罗塞纳制药公司的董事会。这家公司正在研发数款阿尔茨海默病药物。以施拉格为代表的研究人员担心,以这样的方式批准这样的药物会让学界、产业界越发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看来是死路一条的ACH上。
在FDA批准了阿杜卡努单抗后,施拉格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们一直期待阿尔茨海默病研究领域能够有所调整,到目前为止,证明ACH正确的证据压根就不存在。”
施拉格在2022年把目光投向了“出版物评审”网站,搜索可能含有他正在评判的图像的阿尔茨海默病研究。就这样,他找到了几篇相关论文,进而发现了2006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那篇著名论文。
这篇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一种名为Aβ*56的β淀粉样蛋白,并且断言,体内这种蛋白质含量过高的小鼠无法回忆起此前它们熟知的环境信息——恰如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再也找不到原本熟悉的回家之路。主持这项研究的是明尼苏达大学神经科学家西尔万·莱斯内(Sylvain Lesné),当时,他正在大名鼎鼎的研究员凯伦·阿什(Karen Ashe)的实验室里做博士后研究。自论文发表后,许多学者都把这支团队的实验结果看作支持ACH的重要证据。支持者们称,这个结果充分表明,淀粉样蛋白过多会导致认知障碍。
科学家通常会追踪论文的引用次数,因为这能粗略地表明论文中的研究是否有价值。莱斯内的那篇论文被引用了2300多次,而且论文中的图像更是其研究结果的关键。这些图像表明,认知受损的小鼠大脑中存在Aβ*56蛋白。相关的蛋白质印迹研究结果以及其他图像也证明了这一点。
施拉格向美国联邦政府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毕竟,资助这项研究的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同时也向《自然》杂志表达了自己的担心。之后,施拉格又把同样的疑问报给了《科学》杂志。《科学》杂志征询了多位图像分析专家,询问他们是否支持施拉格的结论。结果,这些专家给出了肯定的答复。2022年7月,《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查尔斯·皮勒(Charles Piller)撰写的文章,主题就是阿尔茨海默病药物研究以及莱斯内的论文。施拉格在《科学》杂志上现身后,帕特里克便联系了他。于是,科学侦探这个边缘领域便开始同主流学术界联系起来。对科研诚信的追求使他们肩负起了一项共同使命。“我们不是怪人,”施拉格说,“我们不是只会躲在地下室里,在互联网上给别人找麻烦。”
随后,媒体大范围报道了阿尔茨海默病论文造假事件,但纠正相关科学记录的行动未能迅速开展。
2022年6月,莱斯内的导师、那篇论文的通信作者凯伦·阿什(Karen Ashe)回应了“出版物评审”网站上的数条评论。阿什当时是,现在也是备受尊敬的神经科学家。1996年,她率先开展研究,通过基因工程培育出了产生过多淀粉样β蛋白并且表现出类似痴呆症状的小鼠。学界也普遍认为她是阿尔茨海默病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另外,虽然莱斯内是那篇论文的第一作者,但阿什监督了莱斯内对Aβ*56的研究,并且对那篇论文的有效性负有责任。
“出版物评审”网站的用户注意到阿什愿意回应关于那篇论文的问题。阿什拿出了数张当时递交给《自然》杂志的原始图片,并且称图片的异常源自出版流程。比克认为,这个解释在某些图片上确实说得通,因为把它们转换成可出版的格式必须经过一些可能会产生细微但影响科学准确性的数字处理。然而,这个说法无法解释其他一些图片的问题。
在《科学》杂志报道施拉格等人注意到的问题之前一周,《自然》杂志在那篇论文的线上版后附上了说明,称“本杂志已经注意到有关文中部分图片的疑虑,现正在调查”。“出版物评审”网站上的其他评论还指出了更多问题。比克在一幅图片上发现某些图案出现了多次,仔细查看后认为是某个区域复制粘贴的结果,因此,整张图片都不可信。
“出版物评审”网站的用户还提出,莱斯内其他几篇论文中的图片也存在篡改的问题。按照比克的说法,其中一篇论文似乎更是直接照搬了另一篇的图片。阿什没有回应这些评论,莱斯内本人同样也没有。施拉格希望期刊方面能迅速撤回这些论文。“这绝对非常重要。”他说,同时强调“作为一个严肃的科学研究领域,我们需要坚定立场,纠正存在明显错误的数据”。在施拉格看来,2006年发表的那篇论文无疑是错误的。
这件事最终在2024年年中发展到了顶峰。2023年6月,施拉格针对阿什的一项重复研究做了分析。2024年5月,阿什发表了回应。她承认“数据歪曲了”,但她仍然坚信,她和同事们所做的实验以及在2024年3月发表的相关论文再现了原始工作的发现。因此,为了科学记录的准确性,他们要做的只是修改,而非撤回。
不过,施拉格的态度同样坚决:他坚持认为新的研究结果不支持原来的结论。比克同样要求撤回那篇论文,理由很简单:无论重复实验结论如何,那篇论文本身包含被篡改的内容,因而是不可信的,就应该撤回。最后,阿什告知“出版物评审”网站,《自然》杂志的编辑不同意修改论文的方案,因此,她和除莱斯内以外的所有其他作者一致决定撤回那篇发表于2006年的论文。
2024年6月24日,在“出版物评审”网站上首次出现针对那篇论文的质疑后大约两年半,《自然》杂志撤回了那篇论文。有媒体向《自然》杂志询问了整个时间框架。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期刊公共宣传部负责人迈克尔·斯塔西(Michael Stacey)作为应对这起事件的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的调查遵循既定程序,包括与作者协商并在适当情况下寻求同行评审和其他外部专家的独立建议。另外,还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调查所需时间,比如在有必要的情况下等待相关机构的调查结果。”与此同时,明尼苏达大学也自行审查了这篇论文,结果是未发现存在学术不端行为。
施拉格认为,如果相关科研人员都严格遵守科研诚信,那么ACH的热度很早之前就应该消退了。他说:“我认为,这已经更多地演变成了一次政治事件,而非科学事件。”
2023年1月,FDA走加速审批通道批准了另一款淀粉样蛋白药物“仑卡奈单抗”(Lecanemab)。按照2022年年底发表在《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与治疗》(Alzheimer's Research amp; Therapy)杂志上的研究结果,与服用安慰剂的对照组相比,服用仑卡奈单抗18个月的患者认知能力下降程度较轻。
然而,在施拉格看来,仑卡奈单抗进入市场恰恰凸显了阿尔茨海默病研究领域摆脱ACH的紧迫性。他说,这个假说根本就是错误的。尽管包括施拉格在内的许多研究人员都认同,淀粉样蛋白确实很可能是诸多致病因素之一,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施拉格的观点。2024年1月,百健公司宣布停止研发和销售2021年获批的备受争议的药物阿杜卡努单抗,将研发资源集中在仑卡奈单抗上。2024年7月,FDA批准了同样针对淀粉样蛋白的药物多奈单抗(Donanemab)。在仑卡奈单抗和多奈单抗的临床试验中,多位患者出现了脑部肿胀或出血的症状。甚至,有3名试验仑卡奈单抗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死亡。
科学侦探们仍在寻找那些长期受到认可的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2023年年底,施拉格、比克、帕特里克和哥伦比亚大学神经科学家杨沐(Mu Yang,音译)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提交了一份极为细致的报告,详细说明了卒中研究员贝里斯拉夫·佐罗科维奇(Berislav Zlokovic)的研究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克明白,这样的投诉或许不会激起多大的浪花。毕竟,2023年年末,纽约城市大学已经终止了对王厚彦(Hoau-Yan Wang,音译)的调查——这位阿尔茨海默病研究员此前领导了多项有关阿尔茨海默病药物的研究。尽管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在2024年夏天指控王厚彦在申请科研资助时捏造、篡改数据,但纽约城市大学没有对调查流程及结果做任何评论。至于明尼苏达大学对2006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那篇论文的审查,一位发言人称,“没有发现与这些图片相关的学术不端行为”,但由于州法律的限制不能披露更多细节。
当被问及对明尼苏达大学给出的结论有何看法时,比克表示难以置信。她说:“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会得出那样的结论。根据我本人和其他学者的专业观点,这些照片一定被篡改过。”比克还补充说,这个结果似乎想要表明有关那篇现已撤回的论文的问题并不是“大不了的事”。
她说:“然而,这真的是件大事。”
饶是如此,科学侦探们仍然锲而不舍地继续着他们的事业。2024年7月,他们在葡萄牙波尔图聚会。而现在,他们正谋划着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第三次夏季峰会。
资料来源 Undark
本文作者杰西卡·瓦普纳(Jessica Wapner)是一位出版过大量作品的记者、作家和制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