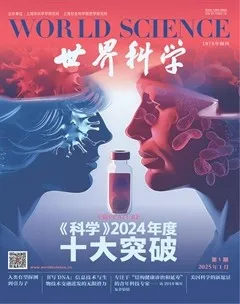客观审视星舰成就背后的科学传播
北京时间10月13日晚,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研发的重型运载火箭——星舰——进行了第五次发射试验。俗称为筷子的发射塔机械臂成功地回收了一级火箭,基本达到了此前的预期。这一进展已选作2024年《科学》杂志年度十大突破之一。
星舰的每一次发射,在国内媒体和社交平台上都能引起相当极化的争论。一种声音认为,星舰发射总有纰漏,甚至在第一次发射时,马斯克本人还在SpaceX公司的发射大厅庆祝成功时,国内部分媒体发帖标题直接用的就是“星舰升空后爆炸”。而另一种声音则在赞美星舰取得进展的同时,声称中国创新再次落后。
实际上,不论是对星舰以及SpaceX的可回收火箭等探索技术的不屑,还是表现出自我菲薄心态的所谓“马吹”,都缺乏对航天科技进展的客观理解,因而既难以合理地确定星舰技术创新的意义,也缺乏对中国航天科技进展的合理认识。而造成这种心态背后的原因,与我们的航天科普甚至广义的科学传播不无关系。
客观看待星舰成果
无疑,星舰发射取得的进展非常值得肯定。我们面临的星辰大海中的未知因素太多了,虽然在中美激烈竞争的大背景下,SpaceX的进展甚至会形成对于中国航天的相对优势,但包括星舰技术在内的每一次进步,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拓展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例如,迄今为止,我们对气候变化及其灾难性后果的认识,大量来自美国宇航局(NASA)的卫星数据。近年来,随着中国气象卫星、探测卫星及其地面站技术的进步,中国日益精密的监测强力支撑气象服务,为全球防灾减灾、气候治理等提供中国智慧。
在一定意义上,马斯克的星舰最主要的突破体现在节约成本上,即通过用民用器件或按照民用原则研发的器件替代部分高端航天元件降低整体开发成本,以及用快速迭代升级大量测试的方式提升研发速度,降低研发成本。基于中国航天企业在可回收火箭方面的快速追赶以及中国工程技术在近年来的突破性进展,星舰取得的突破对于中国航天业并非遥不可及。
既然如此,星舰的技术突破就算不上值得点赞的创新了吗?或者,中国从追赶可回收火箭到可能的追踪星舰发展的技术路径,体现的不过是中国航天科技的追赶能力而不是创新能力吗?两种看似对立的说法其实都很片面,也都没有从航天科技的特定视角看待创新。
从机制创新到工程创新
虽然如上所述,SpaceX的火箭回收及重载火箭技术最大的创新点在于快速降低成本,但它仍然是了不起的创新,因为它完全突破了全世界航天业界70年来的“舒适”运作方式,用颠覆性的资源组织模式推动着技术发展。
与基础科研的创新重在突破性的发现不同,航天领域的发展需要举国之力,涉及大量资源组织调配,自然也会形成一种超稳定的资源分配和科研组织模式。马斯克以私营公司的形式撬动了巨大的沉淀资源,这不能不说是航天领域极为重要的突破。过去几年来,SpaceX不断创新工艺路径,尝试新的材料与新的应用方式,在符合经济性的同时大幅提高火箭有效载荷,这些对于航天领域来讲,都是了不起的成就。
当然,如果美国航天业界的决策者或NASA的管理层不大力鼓励私营公司承担发射及其他航天任务,光靠马斯克,再有想象力和创新精神,再不遗余力地投入,SpaceX也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实际上NASA的慷慨订单而不是马斯克的个人资产才是SpaceX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证。
另一方面,中国航天的追踪式发展是否创新性就弱了呢?并非如此,原因在于,像中国发展原子弹氢弹时有关核裂变核聚变的原理早就被发现和测试过一样,航天发展也不是要实现从零到一的科学原理突破,而首先在于能在自身资源许可的范围内实现发射或完成空间探索任务。
西方对中国航天技术的封锁即便在中美、中欧科技交流蜜月期也没有停止过,中国的航天事业仍实现了大量的工程创新。虽然这些创新在世界范围内算不上从零到一的革命性进程,但对于得不到现成技术、成熟材料和具体工艺路线的中国航天自身而言,这些工作都要从零开始。因此,中国航天工程取得的每一项重大成果,都是重要的且值得骄傲的创新成就。
此外,在被卡脖子的情况下,不能责备中国航天为什么较少类似马斯克和SpaceX所采取的新举措新尝试,实际上,两者所处发展阶段并不同。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已经处于探索出具体发展路径的阶段,而中国航天还处于很多发展条件不充分的现实中,最合理的逻辑是通过工程创新完成他人已经走过的路,并尽可能降低成本。实际上,在跟踪发展的基础上,中国航天已经在月背着陆等方面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就,这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国面向客观现实,探索航天技术发展模式的可行。
对航天科学传播的启示
实际上,除了星舰不断取得突破对中国航天技术和路径发展带来启示外,SpaceX公司乃至整个美国的航天科普,也有很多启发。
航天事业不仅关乎国家科技实力和国际地位,更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如卫星通信、导航定位、天气预报等均离不开航天技术的支撑。通过科普吸引公众对航天事业的关注和认识,激发社会对航天科技的兴趣和热情,有助于形成促进航天事业发展的积极的舆论氛围,进而为航天事业的持续发展奠定认知基础。
长期以来,航天成就常与国家科技进步的形象挂钩。我国一直以来都比较重视航天科普,航天科普相比十几年前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科普内容和形式越来越生动,比如引进动漫,结合调侃等娱乐化形式。但如果想通过航天事业促进更多公众投身或支持星空探索,目前的科普内容就显得不足够了。我们自然要为取得的一项又一项成就喝彩,但我们还需要行业专家引导公众看到各项成就的背后。比如:引导公众思考“不同研发机制的优劣势”“不同国家发展航天的思路和策略的异同”。再比如:“为何选择今天而不是遥远的未来推动这件事?”“为何我们获得少量的月壤,是一件划算的事情?”引导公众深入探讨甚至理性质疑,避免公众对我国航天进展的认识仅停留在“喝彩然后坐等下一次旗开得胜”的层面上。
毫无疑问,公众需要真正的航天权威专家引导——客观、精准地评点各国航天事业的进展和意义甚至发展趋势。但由于受到各种制约因素,比如,科研人员做科普缺乏认可和激励机制,这导致在我国航天科普队伍中,真正懂得航天技术的专家并不多,所以有些重要进展的科普内容很难把握关键部分。此外,航天领域还比许多研究有更多保密要求。
反观SpaceX和马斯克本人的做法,不仅重视移民火星的航天使命的渲染,通过各种渠道来展示自身另类做法的合理性,还通过各种个性化手段来搭载商业利益,比如把一辆特斯拉汽车发射到太空中。在宣传策略上,也会通过各种噱头来吊足航天爱好者的胃口,更不用说马斯克本人打造人设吸引流量的做法。通过这些举措,让航天发射甚至变成了一个开放的信息互动系统。
构建开放的公众可以参与的传播系统,使公众有更多机会参与专家之间对各种路径选择的探讨,让公众认识到科技发展有很多权衡和选择,引导公众提升理性质疑的能力和素养。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仅仅需要航天科学传播工作发生改变,它也关系到对公众与科研关系的深入思考和科学传播的范式转换。要把传播理念从给公众传授知识、传递信息转变为促进公众的参与。在一定意义上,航天科普因其在科学传播中占有的重要位置而应该成为这种转换的引领者之一。毫无疑问,这样的改变不但不会削弱公众对航天事业的支持,还能让社会各界更有可能参与航天事业的进程,使得航天事业不仅继续服务于国家社会的经济物质发展,也能更好地成为启迪民众思考和探究的平台。
本文作者贾鹤鹏是苏州大学三级教授,获得康奈尔大学科学传播专业博士学位,担任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理事。曾任中国科学院《科学新闻》杂志总编辑并获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荣誉。发表60余篇核心期刊论文,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及多项省部级课题。2019年他创办了苏州大学科技传播团队,致力于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传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