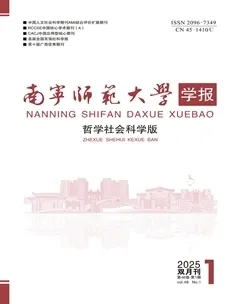在城市流动人口中做人类学调查
编者按:袁同凯教授是南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教育人类学、民族教育与教育政策研究,是福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兼任教育部“全国民族教育专家委员会”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组副组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民族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国家民委项目多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5部、译著2部。袁同凯教授曾先后多次深入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有着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并长年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教育人类学、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等课程。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的灵魂。聚焦城市问题、在城市开展田野调查是当代人类学发展趋势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人类学家的研究视线已经由乡村社会逐渐转向都市社会,关注都市里的边缘群体及其与主流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进城务工农民是较为特殊的城市流动群体,由于他们特殊的社会身份和生活境况,给人类学调查增加了一定的难度。本刊特邀袁同凯教授分享他在城市中开展流动人口研究的宝贵经验,探讨如何“进入”城市场域,切近复杂的城市流动群体,从而有效开展当代人类学的田野研究。
[摘 要]传统上,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往往是相对孤立的异族村落或社群,人类学研究要求研究者自然地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之中,参与当地人的日常活动与社会生活,从而感受他们的所思所想,体悟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和看法。但是,随着人类学研究对象的转换,如何以传统的人类学方法研究都市居民的社会与生活,便成为当代人类学者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本文以入户访谈个案为例,探讨在坚持传统人类学方法的基础上,有效进行城市流动人口人类学调查的经验反思,包括以坦诚谦逊的态度“进入”田野,运用“个人生活史”的田野技术开展研究。此外,提出提升田野资料真实性的诸种途径,包括与被调查对象长期共处、保持与调查对象的良好关系、观察调查对象的行为及所处的对话情境,以及向调查对象核实田野材料的准确性等,就田野资料的真实性问题进行了尝试性讨论。
[关键词]人类学田野调查;城市流动人口;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异文化研究;城市场域
[中图分类号]C912.4;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7349(2025)01-0001-11
一、人类学方法与异域文化研究
徐嘉弈(以下简称“徐”):袁教授您好!您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问题,先后多次深入民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收集、分析了大量民族地区的教育人类学案例,积累了丰富的田野经验。可否请您分享一下对在异文化中开展人类学研究的心得?
袁同凯(以下简称“袁”):你好!我常常说,田野训练造就了“真正的人类学家”,而且人们普遍认为真正的人类学知识均源自于田野调查。决定某项研究是否属于“人类学”范畴,实际上就是看研究者做了多少“田野”1。
由于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原因,传统上,社会与文化人类学者通常深入偏远的“他者”群体中进行田野调查,对一个村落或社区进行全面或专题性研究,用功能观点来解释文化现象和变迁,认为文化和社会制度都是满足人类基本和衍生需求的机制。因此,人类学者往往主张通过揭示村落或社区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人们的生活、思想和感情。大多数人类学者相信,通过对小型社会单位的透视,人类学者比其他任何领域的学者更容易深入到被研究者中,体会和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避免本身文化价值观和主观规范的制约,从而较为开放地吸纳“本文化”之外的现象和事物2。费孝通先生认为,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就在于它可以深入到人际关系的深处,甚至进入语言所难于表达的传神之意3。
从历史上来看,人类学最初为了解殖民地人们的生产生活与风俗习惯,开始进行殖民地文化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人类学的传统。从学科方法上看,人类学之所以依旧坚持研究异民族,是因为异民族在文化上与我们不同。正因为其不同,才不会被“想当然”的材料和风俗习惯所蒙蔽1。而研究我们自己,经常有想当然的情况,容易有因为过于熟悉而被疏漏的地方。举一个李亦园教授分享过的例子。台湾地区移民社会中童养媳婚姻这一重要的婚姻现象,最早是美国人类学家武雅士(Arthur P.Wolf)发现的。通过深入村落进行调查和研究,他认为多数童养媳婚姻的夫妻感情不好,其结果对台湾地区的人口变迁有很大影响,由此可以认为这是乱伦禁忌的一个来源。就是说,童养媳因为从小养在一起,像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因此到了结婚之后,总有一种和自己兄弟姐妹结婚的感觉,好像是乱伦似的。这是早期芬兰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G.Westermark)提出的乱伦禁忌假说。但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童养媳婚姻太常见了,也就把它当作“想当然”的现象而忽略了。研究异文化,必然是因为不一样,才会觉得特别,才会发掘出来。从异民族的研究中得到人类学的基本训练,发现其中的方法,再回过来研究本民族,就不一样了。正是通过这种研究,对异民族和异文化的研究,才能发现一些特殊的、不为想当然所左右的东西。只有这样,研究过异文化后才研究本民族应是最合适的步骤2。对此费孝通先生也曾有过生动的描述:“生长在某一文化中的人,好像鱼在水中,很不容易得到一个客观的态度。而客观的态度是观察所必需的。研究本身文化需要一些训练,训练的方法就是多看几个和自身不同的文化组织。”3
徐:我们关注到,近年来您的研究视野也包含了剧变中的城市场域,这与您之前的研究有较大跨度,请问您对“以城市为田野”有怎样的新思考呢?
袁:长期以来,人类学者以研究相对封闭的、小型无文字的异文化为己任,试图通过对异民族的社会与文化研究来反观我们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认识我们人类自身。正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拉克洪(C.Kluckhohm)所说的那样,“人类学为人类提供了一面巨大的镜子,使人类能看到自身无穷尽的变化”4。人类学研究最基本的目的,是通过比较和研究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的社会与文化来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我们自己的社会与文化。早在20世纪初期,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米德(M.Mead)对萨摩亚青少年教育的研究就为美国教育者反思当时学校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面对全球化的强大浪潮,人类学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日益凸现出来。人类学家必须走出小型的简单社区研究的范畴,扩大自己的研究视野,在更大的时空背景和社会、经济体系中去探讨和分析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当代人类学的任务在于尽可能忠实地展示各个社会群体在适应全球化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多样性,从而促进跨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尊重,减少人类群体因文化差异而引起的纷争与冲突。人类学家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反思,并结合历史的、宏观的社会学方法,更加注重在地方性社区从事长期实地调查的方法。
二、在城市流动人口中进行人类学调查
徐:人类学家走出小型的简单社区开展研究已成为当代的研究共识,而走向我们熟悉又陌生的都市开展田野调查却并非易事。您认为,在城市中开展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挑战在何处?
袁:通过“世界体系的视角”(World-system perspective)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昔日的研究对象早已开始参与区域性的、全国性的甚至世界性的活动1,许多地方文化所反映的是它们各自在更大体系中所占据的经济与政治地位。随着族群的迁移,人们在新的地区重新结成群体,重新建构他们的群体“形貌”,民族志中的族群呈现出一种流动性,不可能再有从人类学描述中反映出的地域特征。也就是说,在世界各地已不再有人类学家所熟悉的研究对象,族群不再具有地域上、空间上的同质特征。随着当代世界体系一体化的发展,一方面,人类学似乎决定放弃其传统的地域上的固定社区或地方文化的陈旧观念,而去领会和理解人、物和观念都在急速转变并不愿固守故土的相互联系的世界。但同时在回应其他学科置疑其“田野”时,人类学比以前更加注重在地方性社区从事长期实地调查的方法2。目前,许多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已经由乡村社会逐渐转向都市社会,关注都市里的边缘群体及其与主流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我所关注的城市流动人口“农民工”便是这样的群体之一。进城务工农民虽然生活在都市里,但由于种种制度或结构性因素,使他们难以真正融入都市人的生活之中,始终处于都市生活的边缘,他们的根仍旧在农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流动群体。由于这种特殊的社会身份和生活境况,他们往往对闯入他们生活中的陌生人持谨慎态度。这无疑增加了人类学调查,尤其是入户调查的难度。
徐:面对城市场域的独特挑战,当代人类学研究者应该以何种姿态进入田野?对这一问题您是否有相关的心得与经验可以分享?
袁:其实,这个问题涉及人类学者在田野中的自我定位问题。传统上,人类学者为了使他们的文本叙述显得客观、科学,他们往往有意回避论及自己获取田野资料的过程或路径3。20世纪60年代末,尤其是海姆斯(D.Hymes)的《重塑人类学》(Reinventing Anthropology)问世以来,人类学界开始反思民族志的田野工作1,主要讨论人类学者如何描述他们所研究的人们和对“他者”的想象。20世纪80年代后,马库斯(G.Marcus)、库什曼(D.Cushman)和克里福德(J.Clifford)等人类学者对传统民族志的叙述架构及描述的权威性等方面提出了批评,主张人类学者应该把自己在异文化中展开田野调查的经历纳入叙述架构之内23。为证明资料来源的正确性和可靠性,人类学者有必要叙述他们搜集资料的过程4。人类学者可以以一种“反观”的写作手法将他们作为参与观察者的经历融入他们的民族志描述中,使写作者自身的田野经历也成为读者批评的内容之一。如,“叙述民族志”和“自白的描述……试图让读者置身于田野调查者的工作场景,从而判断田野资料的正确性和可靠性”。这些反观性文本可能对全面地反思当地人的文化、研究者和当地人之间突如其来的相互交往是有裨益的5。在此,我们不妨借用称作“民族志者的路径”(the ethnographer’s path)这一概念,即研究者参与当地信息提供者社会网络关系中的轨迹。桑耶克(R.Sanjek)认为这种网络信息有助于读者自己去评价田野资料的正确性。除了网络关系的“大小和范围”,桑耶克认为人类学者有必要公布被观察的信息提供者的所有信息,包括诸如性别、职业、年龄等人口资料,还应披露人类学者通过一个信息提供者结识另一个信息提供者的实际网络路径6。对人类学者与其所有关键信息提供者之间社会网络关系的多维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学者获取资料的过程7。
徐:人类学者在田野调查中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进入”。请问您在研究城市“农民工”这一群体时,是如何突破“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界限与藩篱,“进入”其中,从而有效开展研究的呢?
袁:首先,就是告诫自己抱持一种坦诚、谦逊的态度。人类学者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他具有一种能以坦诚、谦虚的行为与信息提供者建立直接密切接触的能力8。在人际关系淡漠的都市进行入户访谈,我们往往会遇到被信息提供者拒之门外的尴尬情景,这使许多初次试图进行入户访谈的研究者感到气馁和沮丧。但如果我们能够进行换位思考,信息提供者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陌生人来敲我的房门,并要求进屋来访谈我,我想我也会找种种借口予以拒绝,至少不会轻易让他进来。问题的关键要看我们通过何种路径、何种方式获取信息提供者的信赖。在这里,我分享一个入户开展调查的案例。
2022年五月初的一天下午,我们来到天津市南开区R居委会,由于“五一”长假,当时办公室里只有一位女同志在值班。我们向她说明了来意并出示了相关证件,表示我们希望在她们辖区找一名外来务工人员,最好是拖家带口的。她说她走不开,要我们留个信,等8号上班后,她再转交给居委会主任。8号上班后,我们一大早又赶到R居委会,正好遇见居委会主任,但她上午脱不开身,要我下午两点以后再来。下午两点半我们准时赶到,她处理完手边的事之后,与另一个居委会的中年妇女一道陪我们去找一户姓刘的民工。由于她们也不认识这户人家,又叫上了小区的片长——一位老太太,她带我们直接敲开了刘家房门。当片长和居委会主任向主妇小芹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之后,她牵着七岁的女儿,倚靠着门框,警惕地上下打量了我们好一阵子,没有丝毫让我们进屋的意思。我们试探地问能否让我们进屋坐坐。她看了看片长和居委会主任,一连问了她们好几遍:“他们是南开大学的吗?”我们连忙拿出工作证,她仔细地翻看了一遍,似乎还是不太放心。在居委会主任一再保证后,她才很不情愿地把我们领进她的家——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破旧平房。
小芹的家坐北朝南,没有窗户。家里没有什么家具,布局很简单。一进门的右边摆放了一张双人床,它几乎占去了整个房间的一半面积;房间的南面并排摆放了一张简易的写字台和一个双门小衣柜,在衣柜和床之间只有能挤过一个人的空间,写字台下面,有一把椅子;在进门的左手边还有一个折叠式简易小方桌,40厘米宽,30厘米高,此外,紧贴着床和门口还放了一把破旧的椅子。房间里显得十分拥挤,来了客人,只能坐在那张旧椅子上或双人床的床沿上。
进门后,小芹请我们坐在靠门口的椅子上。不难看出,她神情紧张,怯生生地问我们在大学里教什么课、有多少学生、家住哪里等。我们诚恳地一一作了回答并再一次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来意。由于初次见面,她又有很强的防范心理,我们没有向她提任何问题,只是想让她尽快地信任我们。根据人类学家做田野时的经验,孩子是初次访谈时最好的话题。于是,我们便将话题转向了她的孩子。她只有一个女儿,叫苗苗,今年七岁,在南开区E小学读一年级。孩子天生唇裂,似乎挺严重的,因为她吐字相当含混。这无疑增加了孩子这个话题的难度。好在孩子很天真,不停地向我们问这问那,还主动拿出自己的作业本让我们看。于是我们与小芹就自然而然地聊起了小苗苗的学习情况。她说苗苗的学习还可以,只是最近英语有些跟不上。我们当时就暗自想,机会来了,我们可以以教孩子学英语为名来证明我们的诚恳,同时也能证明我们真的是教师,而不是什么骗子或坏人。我们让苗苗看着课本读了几个单词,她的发音含混不清,根本听不清她在读什么。我们试着教她读了几遍,可是效果不明显。这时小芹说自己只是初中毕业,英语学得也不好。现在她只能每天督促孩子写单词。很明显,她的方法不当。我们给她讲了一些如何提高孩子学习英语的方法,如孩子刚刚学英语时,要让孩子多听多读多背,要多为她创造说英语的机会,不要强迫她拼写单词等等。看我们讲得头头是道,她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谈话也自然起来,不再像我们刚进屋时,时刻都在提防着。我们大约谈了一个小时,话题基本上都是关于我们和孩子的学习情况。临走时,我们许诺过几天再来,如果她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带一个女研究生来,让她帮助小苗苗补习英语。听了我们的话,小芹显得很激动,好像遇到了救星似的,连连说好。她主动给我们留了电话号码,并要我们下次来时,提前给她打个电话,她好到巷子口来接应我们,以免我们找不到她的家门。我们出门后,小芹和孩子把我们送出那迷宫似的窄小巷子,一直到街上。在街头拐弯处,我们看到她们还在朝我招手——她们真的希望我们能再来。
通过这次入户访谈,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在城市流动人口中进行人类学调查的难度,同时,也深切地感悟到费孝通先生在其田野笔记选录《芳草茵茵》中所说的箴言:“在实地观察中最重要的精神是坦白和诚实”1,坦白和诚实能赢得信任。
徐:如您所说,面对城市场域,以及“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与之进行有效的交往是田野调查成功的关键。因此,请您谈谈您在这个过程中又运用了何种田野调查技术呢?
袁: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个人生活史(Life Histories)对于人类学者理解其研究的对象如何感知世界、对应社会变迁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23。尽管生活史是一种口头的历史叙述,但它清楚而又广泛地记载了一个人的生活。通过我的研究发现,在都市流动人口中进行人类学研究,访谈个人生活史是获取翔实资料的重要有效途径之一。
那次访谈回来后,由于工作繁杂,几乎忘了再次探访小苗苗的承诺。两周后,小芹打来了电话,问我们怎么还不去她家,说小苗苗几乎每天都要问她,那两个叔叔怎么说话不算话啊。我们感到很愧疚,赶忙做了解释,并答应第二天(刚好是星期六)早上九点半一定准时赶到。当天下午我们给小苗苗买了一套南开区一年级第二学期语文、数学和英语的复习试题,并在市场里买了5公斤品质上乘的香蕉和苹果。第二天早上九点半,当我们和研究生小汤赶到小芹所在的棚屋区时,小苗苗和她妈妈早已在巷口等候了。
进屋后,我们发现小屋子比我们第一次来时显得干净多了。小苗苗一点也不认生,一见到小汤就不停地与她交谈起来,一口一个大姐姐,叫得特别亲切。小芹解释说,她们家平时很少来外人,她丈夫由于工作的原因,每天一大早离家,晚上很晚才回来,平时家里就只有她和小苗苗两人。她说,自从上一次在家里被陌生人诈骗后,她现在几乎不与陌生人接触,与房东和邻里也只限于见面时点点头、打个招呼而已。那还是他们租住楼房时发生的事情。一天中午,有四个人来敲门,两男两女,打扮得像电工。他们叫开门后,说楼房的电路有问题,需要检修。他们的着装看起来也挺像电工,其中两个男的手里还拿着钳子等工具,女的手里也拿着本子和笔。他们进屋后,随便看了看线路,说需要收取80元的检修费。因为房东家住得很远,平时物业公司来收费都是由她先垫付,事后房东再还给她,当然这次亦不例外。但是,当她到楼下问其他家户时,除了一家本地人也交了所谓的检修费外,其余的人都没有交。她和这家人意识到有问题,便急忙跑下楼,发现那四个人早已溜得不见踪影。他们马上拨打110,来了两个民警,询问了一下事发时的情况和嫌疑人的相貌特征,随后就走了。难怪那天我们来时,尽管有居委会工作人员的介绍,她还是那么谨慎。
由于屋子太挤,小苗苗拉着小汤到院子里玩。我便和小芹闲聊起来。小芹32岁,家在四川农村,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了一年。因为她姑姑家在成都,第二年她就到成都投靠姑姑,想找份工作。但由于只有初中学历,只在一家餐馆找到一份做面点的工作。就是在这家餐馆,她结识了现在的丈夫,他当时只是个小学徒。他来自四川巴中市兴文镇,属于大巴山区,曾是革命老区,自然条件差,生活艰苦。初中毕业后,他就到省会成都边打工边学厨师。他们结婚后,在成都租了一间小屋,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不久他们便有了小苗苗。由于川菜在成都的竞争相当激烈,小芹的丈夫经朋友介绍只身来到天津,在一家川菜饭馆做厨师。一年以后,小芹也来天津做工,当时孩子还小,留在乡下爷爷奶奶家里。小芹的丈夫来天津后每月有4 000多元的收入,小芹自己在一家餐厅做面点,每月能挣2 000多元。为了孩子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环境,他们决定将小苗苗从四川农村接到天津来上学。为此,他们在南开E小学附近租了一间一室一厅的楼房,经过多方联系,小苗苗终于踏进了南开区E小学的校门,走进了宽敞明亮的教室。为了照顾家庭,小芹放弃工作,在家里专心洗衣做饭,每天接送孩子上学。一学期后,由于小芹没有收入来源,加上孩子上学的开销又大,他们不得不搬到了现在这间不足十平米的破旧平房里。这间平房每月租金只有400元,比以前住的一室一厅便宜很多。但就算这样,他们的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后来听小汤说,小苗苗讲,她妈妈平时很少给她买冰棍吃,更别说其他零食了。她说:“妈妈说了,我们要多存点钱,等存够了就给我做手术。妈妈还说,我上学还要花很多钱,让我不要和别人家的孩子比,我和他们不一样。”
这次,小芹不再避讳小苗苗残疾的事。她说小苗苗的唇裂相当严重,连上腭骨都是裂开的。她说:“既然我们生下她,就有责任养育她。因为她天生残疾,我们更应该细心地呵护她。我们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好好培养孩子,让她将来成人后能自食其力。”从她说话时的表情,我们可以看出她为小苗苗倾注了所有的爱。正如她所说的那样,他们的收入几乎全部都花在孩子身上,他们已经给孩子做了两次手术,等条件允许时,他们还要为她再做一次修复手术,而每次手术的费用都高达数万元。这对于一个靠打工为生的家庭而言,确实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或许是因为小苗苗有唇裂缺陷,或许是因为社区的人文环境不好,小芹平时很少让小苗苗出门玩耍,除了去学校,小苗苗几乎很少走出自己的家门。小芹生怕孩子受欺负,更怕孩子学坏,耽误学习。小苗苗觉得老师不喜欢她,说老师平时上课从来不让她发言。每当老师提问,她都会举手,但老师从未让她回答过问题。据小芹说,有一天小苗苗放学回来后,哭着对她说:“妈妈,我们转学吧!我不想在这个班里上学。老师和同学都不喜欢我。”小芹说:“不管孩子有什么缺陷,作为一个老师,都不应该歧视孩子。”为此,她感到很苦恼。她问我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给老师送点礼物或请班主任老师吃一顿饭。对此,我没有作明确的回答,因为我们的确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改变老师和同学对小苗苗的看法和态度。说实在的,请老师吃一顿饭,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于家里只有一个人挣钱、供养三口人在城里吃住和一个孩子上学,同时还要攒钱为孩子做大手术的家庭而言,花销几百元去做一件他们并没有十分把握的事情,确实值得掂量掂量。
值得提及的是,在我们的想象中,进城务工的农民整日忙于挣钱,大都不关心他们孩子的学习成绩。但是,这次入户访谈证明我们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个案中的这家人非常关心孩子的学习。人类学者在初次接触被研究者时,往往会以自己的文化视角来观察当地人的文化,这种视角可能会影响到观察的结果。因此,人类学要求调查者长期沉浸在所调查的人群中间,做深入细致的访谈,体验当地人的生活,观察当地人的行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当地人的社会与文化,也才有可能验证一些先入为主的理论假设。
徐:无论是民族地区,还是城市场域,其中展现的丰富与幽微的文化肌理都需要长时间的研究、分析方能逐步切近。不管多么优秀的田野工作者,如果他们只进行过短期的田野调查,他们对其所研究的文化的理解往往都是表面的。任何文化都极其复杂和微妙。我们花一生的时间才能了解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很小部分,何况要了解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自己的异民族的文化。那么,您认为人类学者如何才能获取对异文化的深入理解,以便我们能够像理解自己的文化一样来正确地解释异文化呢?
袁:首先,人类学要求调查者与被调查对象长期生活在一起,这是人类学者确保资料真实性(veracity)的最好策略。随着反复地考察一个社会或文化,研究者会越来越多地了解该文化,那些看似难以理解的行为和观念会逐渐变得清晰易懂。长期的研究还可能提供一种真正的民族历史观——一种既关注研究者自身生活又关注被研究者生活的视角。我们有可能从当地人成长和扮演不同的生活角色的过程中看到他们生活的趋向。这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建构和影响当地人生活的核心文化价值和文化行为。早期人类学者往往认为部落社会或传统文化在受到“文明”冲击之前是静态不变的。实际上,所有的文化都会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变迁。长期的田野工作可以使人类学者从暂时的稳定性中把握住永恒的脉络,从而更好地理解文化变迁的趋向和动因1。但是这种方法在当代研究中却日益衰落。眼下人们更倾向于所谓的聚焦民族志(focused ethnography)研究。与传统民族志相比,这种民族志具有明显的优势,即以最少的花费获取最多的资料,而且民族志研究的主题越明确,所需田野调查的时间也就越少。但问题是,此类基于短期田野调查的民族志研究能否如实地反映复杂的社会现实2,仍旧值得商榷。毋庸置疑,在田野中生活的时间越长,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当地的社会与文化,研究者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纠正一些自己想当然的问题,也就有更多的可能性将田野者自己的田野经历转化为地方性知识。
其次,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保持良好的参与角色关系也是确保田野资料真实性的有效途径之一。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所有的民族志叙述都是局外人的观点、局内人的观点以及他们之间互动的结果。因此,局外人参与局内人活动的程度和性质、局内人参与研究的程度和性质以及研究过程中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的分工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实际调查中,通过与局内人的合作,可以拓宽局外人的社交的范围,从而弥补局外人角色的不足之处。此外,局外人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民族志材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同时也可能会影响人类学者的敏锐性。为此,确立巧妙的角色关系对人类学田野调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关系可以在更加宽广的社会情境下为研究者提供更多接触局内人的机会。但是,正如A.Stewart所言,在认知上,文化并不是由人们“阅读”的一种孤立体系,而是不均匀地弥散于行动者之间,每一个行动者都基于他或她自己的经历、知识和意向以符号和象征的形式赋予文化独特的意义3。也就是说,人类学者仅仅通过访谈行动者还不足以了解他们的文化。此外,文化的“表演性”(performative)也远胜于其“报道性”(informative)。因此,人类学者不仅需要观察各种文化表演,而且更需要亲身体验文化。因为文化不是同质的,而是弥散于不同的社会情境之中,因而,人类学者需要在不同的情境下体验被研究者的文化。
再次,观察人们说话时的行为以及说话时的情境也是确保田野资料真实性的有效途径之一。即使最优秀的信息提供者都很难准确地表述其群体的文化与行为,而且人们所说的与他们实际所做的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研究者有必要亲自进行直接观察。人类学者一致认为,好的方法应该包括访谈中的观察和记录,更重要的是对人们说话时行为的观察和记录1。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我们必须区分人际互动所发生的社会情境,特别关注那些在人际互动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信息提供者的行为。
最后,让当地人对描述他们生活的民族志文本进行反馈也是确保田野资料准确性的有效途径。当他们阅读我们所写的文本时,“他们”即当地人可能会展现出完全不同于作者的观点2。这些分歧有助于我们仔细核实田野资料的准确性,而且可以提供一些我们洞察研究者与当地人之间关系的新资料,同时也有助于维持研究者与当地人之间的关系。
现在,我们依旧与这户人家保持着联系,关注着他们的生活,尤其是小苗苗的学习情况。我们似乎成了他们在这个大都市中惟一值得信赖的人,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他们都会主动与我们联系,听听我们的看法。我们从他们那里获取的,不仅仅是一些关于他们这个特殊群体的资料,而且是他们的信任。我们确信,通过这种途径获取的资料是可信的。作为千百万个散居或聚居在城市角落里的民工家庭之一,他们的家庭生活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个群体在都市中的生活境况。从这个入户访谈案例中,我们认为在城市流动人口中成功地进行人类学调查,确保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关键要看我们如何介入这些对城市人抱着疏远和怀疑态度的人群、如何取得他们的信赖以及如何与他们建立密切的关系。
徐:感谢您为我们分享了在城市开展田野调查的诸多经验,为更多人类学学子和青年研究者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研究思路与方案。
袁:谢谢!
[责任编辑:玉 璐]
[收稿日期]2024-11-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南各民族中的健康知识体系及相互交流研究”(24BMZ096)
[作者简介]袁同凯(1963—),男,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南开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云南大学西南联合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徐嘉弈(1996—),女,南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
[引用格式]袁同凯,徐嘉弈.在城市流动人口中做人类学调查:兼论入户访谈案例的启示及田野资料真实性问题[J].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6(1):1-11.
1参见Kay Milton的Environmentalism and cultural Theory:Exploring the Role of Anthropology in environmental Discourse(London:Routledge1996年出版,第2页)。
2参见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页。
3参见费孝通:《芳草茵茵——田野笔记选录》,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
1参见李亦园:《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版,第97页。
2参见李亦园:《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版,第99页。
3参见费孝通:《芳草茵茵——田野笔记选录》,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4参见马广海:《文化人类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1参见Conrad P. Kottak的Anthropology:The Exploration of Human Diversity(New York:The McGraw-Hill Companies1997年出版,第7页)。
2参见费孝通:《芳草茵茵——田野笔记选录》,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3参见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页。
1参见Dell H. Hymes, ed的Reinventing Anthropology(New York:Random House1969年出版)。
2参见Marcus,George和Dick Cushman的Ethnographies as Texts(载于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82年第11期,第25-69页。
3参见Clifford, James和George E. Marcus的Introduction: Partial truths载于In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年出版)。
4参见Bronislaw Malinowski的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New York:Dutton1961年出版,第2-3页)。
5参见Alex Stewart的The Ethnographer’s Method(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Inc1998年出版,33页)。
6参见Roger Sanjek的Anthropology’s Hidden Colonialism: Assistants and their Ethnographers(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Press1993年出版,第398-400页)。
7参见Alex Stewart的The Ethnographer’s Method(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Inc1998年出版,第36页)。
8参见Paul Radin的The Italians of San Francisco:Their Adjustment and Acculturation(San Francisco:R and E Research Associates1970年出版,第6页)。
1参见费孝通:《芳草茵茵——田野笔记选录》,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2参见Chan, Anita,Jonathan Unger and Richard Madsen的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Californi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84年出版)。
3参见黄树民:《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1参见Fowley Don. D. and Donald L. Hardesty的Introduction载于Fowley Don D. and Donald L. Hardesy:Others Knowing Others的Perspectives on Ethnographic Careers(London:S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94年出版,第4页)。
2参见Alex Stewart的The Ethnographer’s Method(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Inc1998年出版,第20页)。
3参见Alex Stewart的The Ethnographer’s Method(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 Inc1998年出版,第24-25页)。
1参见Alex Stewart的The Ethnographer’s Method(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Inc1998年出版,第26页)。
2参见Alex Stewart的The Ethnographer’s Method(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Inc1998年出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