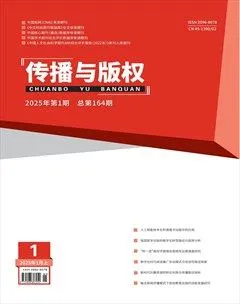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形象的影视化传播路径探索
[摘要]在文旅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影视剧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媒介形式,对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城市形象的传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文章以《去有风的地方》和《我的阿勒泰》为实证案例,深入剖析这两部作品的景观建构策略和文化传播机理,揭示其如何有效挖掘并打造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形象,旨在为该地区的文旅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案例,进一步推动其经济社会发展。
[关键词]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形象;《去有风的地方》;《我的阿勒泰》
一、“他城空间”的反凝视:异域景观与生态美学的融合
《去有风的地方》和《我的阿勒泰》均聚焦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打破了传统大众对边缘地理空间的偏见性凝视,在鲜活展现地方特色风貌的同时,也书写出蓬勃发展的地方活力新篇章。阿多诺曾经提到,文化工业生产的标准化以及文化工业产品的商品化、拜物性直接导致文化产品个性的泯灭与创造性的枯竭,并最终导致“反文化性”[1]。而《去有风的地方》和《我的阿勒泰》采用“反文化工业”的方式,重塑作品个性,再现文本创造性,实现了“文化性”的复归,并依托地域特性重塑“情境”,让影像景观具备灵动性,这是重塑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形象的关键。
(一)审美消费景观中的生活情境重塑
后现代社会中的景观呈现混杂性与规制性的特征,其被划分出模块,不同的模块受到各具目标性的发展话语制约。德波由此提出关于景观的“情境的重构”(ConstructedSituation)理念,即通过对规约性景观条例的反抗,在作品中重建并复现“艺术性的生活瞬间”[2]。《去有风的地方》和《我的阿勒泰》在展现地方性文旅资源、推动乡村振兴及促进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均融入了源自社会、审美及消费话语中的各类景观元素,以生动可感的生活情境为贯穿线索,重构了影像中景观的呈现模式。其中,《去有风的地方》运用象征性色块描绘多样生活情境,巧妙融合自然光线,精准还原大理白族聚居地的色彩韵味,并生动呈现云苗村的稻田、梅子园、马场等田园景致。相比之下,《我的阿勒泰》实现了从主体记忆到物质复原的情境跃迁,将李娟记忆中的新疆阿勒泰风貌在荧屏上进行呈现:辽阔草原、葱郁牧场、无垠沙漠与悠然羊群共同勾勒出独特的异域风光,陌生化视觉元素与强烈视觉冲击突显了阿勒泰的城市空间。
(二)地域发展生机中的时代美学流变
《去有风的地方》和《我的阿勒泰》均承载深刻的时代使命,前者致力于探索乡村振兴的多元化路径,后者则聚焦描绘民族共融的丰富多样的民族志景观。在既定的命题框架中,尽管两部剧集所呈现的景观蕴含社会、审美以及消费方面的“预设”特性,但同时,这些外在属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掩盖了地方景观的内在生命力。对此,影视创作者深入地域核心地带,挖掘其内在发展逻辑,旨在构建一个纯粹且内在的地方发展体系,同时阐述流变的时代美学话语。具体来说,《去有风的地方》融入大理的自然风光、淳朴的风土人情以及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为新时代乡村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更深刻构建起乡村生活图景。其中,云苗村的自然景观,如洱海的波光闪烁、马场的绿意盎然等,串联起村民的日常生活,展现他们依托自然条件构建的朴素劳作方式与独特的村落生态环境。云苗村的影像情境构建深入运用了色彩这一“感受形式”,依托富有地方特色与民族风情的色彩表现手法,构建起云苗村相对当代视觉范围的“核心幻象”[3],即从灰蒙蒙的工业化城市向色彩斑斓的乡村空间的非线性转换。而《我的阿勒泰》敏锐洞悉了“慢生活”的意蕴,深刻反思都市化进程对人心灵的冲击,倡导回归宁静生活的真谛。影视创作者如同德勒兹笔下的“游牧者”,深入阿勒泰的每一个角落,直接感知其蓬勃的生命力[4],并在影像中予以重塑,使阿勒泰从一个边缘的“他城”转变为充满归属感的“我城”,实现了边缘空间坐标的解域,进一步增强作品的生态感知力。《去有风的地方》和《我的阿勒泰》所塑造的西部边疆民族生活风貌,在中国影像市场中并非稀有,但它们广受欢迎的核心在于都从当代城市居民的视角出发,对边疆的空间美学进行了全新诠释。剧中角色许红豆与李文秀均带着中心城市的审美观念踏入边疆,她们背负着城市空间的种种压力,当骤然置身于大理与阿勒泰时,这种城市与异域空间的强烈反差为这些自然环境赋予了更加蓬勃的生命力。影视创作者在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构建一种有别于内陆城市的美学空间,看似在塑造一个疏离于时代的“乌托邦”,实则是将时代的主流情绪作为切口,运用逆向思维来满足当代观众追求反叛的心理需求。
二、“精神原乡”的再想象:良好生活的社会性情感转向
《去有风的地方》和《我的阿勒泰》将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壮丽景观精心雕琢成一种独特的影像产品。在此基础上,两部剧集还深入挖掘西部边疆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得影像超越单纯的视觉呈现,成功建构深邃而迷人的“精神原乡”集体想象。这一想象空间从理想化的乡村风貌延伸至广袤无垠的边疆地带,彰显浓厚的人情味与对价值的不懈追求,形成一种双重叙事结构。“精神原乡”的文化策略使得“新疆阿勒泰”“云南大理”逐渐概念化,将影像文本置于社会、文化等要素构成的“大文本”中,实现了文本与现实的“互文”,进而将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塑造为观众所向往的“乌托邦”[5]。
(一)交流经验复归下的治愈性联结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中指出情感的重要性,其认为情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涵,在弥合“分裂”的同时加速“凝聚”,这一与理性处于二元对位框架的元素构成了《去有风的地方》和《我的阿勒泰》的重要修辞手法[6]。具体来说,《去有风的地方》从北京这一现代都市出发,描绘了许红豆在高压工作与挚友离世双重打击下的“主体性分裂”状态,即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压抑了人性的情感层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云苗村的有风小院,它成为许红豆及众多同样身心俱疲的现代“分裂主体”的庇护所[7]。这些角色无论洒脱或挣扎,都在各自的旅途中寻求自我成长与修复,而有风小院提供了一个温暖的情感空间,让具有不同价值观与生活态度的个体在此相遇,彼此的故事交织成一张理想交往的情感网络,体现了都市人心灵的普遍轨迹。正如本雅明所言,“讲故事的艺术”正逐渐消逝,而“交流经验”作为故事的核心,其缺失正是现代社会分裂症候的体现[8]。《我的阿勒泰》直面而非逃避现实生活的挑战,将镜头转向遥远的阿勒泰,彰显了张凤侠、巴太等北疆人民的勇敢与从容,通过个体间的互助行动强调交流经验对重建现代生活伦理秩序的重要性。马尔库塞批判的“需求异化”现象在许红豆和李文秀等角色的经历中得以体现,她们在机械化生产中逐渐沦为单向度的人,失去了批判与追求的能力[9],因此她们选择前往西部民族边疆地区寻求心灵的慰藉,这一过程不仅实现了“交流经验”的重构,也完成了对城市生活的批判性反思。
(二)多元价值谱系下的差异性主体
当文艺作品将西部边疆民族地区作为表现主题时,往往会出现客体化的创作倾向,即主观性地夸大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空间独特性和地理边缘性,将这些边缘性的异质元素转化为奇观式的观赏对象。在此过程中,边缘性的称呼取代了主体性的构建,同一性的融合则取代了空间差异性的显现。这一现象深植于“景观—政治”(LandscapePolitics)的辩证关系中,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谁掌控地域景观以及谁决定地方景观的展现方式[10]。从最为本真的价值尺度来说,地方居民的生活实践与地方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塑造了地方的主体[11]。《我的阿勒泰》展现了纯粹内在性的地方性格,当地多民族杂居的风土人情和游牧生活的艰辛塑造了地方坚毅而乐观的民族性格,剧集通过展现哈萨克族和蒙古族的转场习俗,构建了一种民族性格外显的生活图景,这种性格特质与阿勒泰辽阔壮美、野性十足的自然景观紧密相连,成为影响李文秀价值探寻之旅的重要因素。而《去有风的地方》正是通过描绘外来者与当地人的差异关系网络,彰显了地方伦理秩序的现代兼容性。剧中角色的一举一动都深刻展现了大理白族善良与勇敢的价值观,这些广受认可的价值观持续激发地方文化的活力,并在多样性中引发观众的情感共振。
三、“狂欢仪式”的叠意指:多元参与主体的自发式入场
《去有风的地方》和《我的阿勒泰》聚焦构建真实的城市影像,激起了关于地方文化传播的大众“狂欢”。地方城市形象的媒介再塑成为这场狂欢化文化传播热潮的关键,它将影视剧中形成的媒介关注转化为实际的在地游览,在重塑空间布局的同时,也激发了多元主体参与地方性文化建设的热情。
(一)媒介仪式空间中的在地体验
影视剧对城市文化传播具有双重建构作用,一方面,影像作为媒介不断生成与地方城市有关的想象性符号,如:《去有风的地方》构建了大理云苗村这一乌托邦式的“精神原乡”,它在与时代进步的话语相融合的同时,也回归到传统的人情社会中;《我的阿勒泰》通过慢生活的秩序重新构建了价值追求的符号体系,这两部剧集都蕴含顺应时代情感的特征,实现了对地方想象的塑造。两部剧集生成想象性符号的过程契合詹姆斯·凯瑞提出的“媒介仪式空间”理论,当观众进入这两部剧集的仪式空间时,他们会带着对实地空间理想的想象,而当这些期待在现实未能如愿以偿时,真实地方与媒介所塑造的城市形象在生产层面便会出现偏差,这常常会导致地方原有的特色与性格被虚构的城市形象所取代,进而使得现实空间中的地方结构更加边缘化。在两部剧集的传播过程中,影视创作者凭借敏锐的洞察力,深度挖掘并彰显城市文化,突出城市的独特基因,从而在传播的起始阶段就有效预防了形象错位的产生,缩小了媒介仪式空间与实体城市间的差距,并通过展示现实城市丰富多维的历史形象,增强了影像空间的吸引力。《去有风的地方》通过展现大理地区独特的建筑、服饰、美食以及非遗文化,打造了一个充满诗意的仪式空间。依托该剧的广泛影响力,大理市凤阳邑村成为网红打卡地,而剧中的扎染坊通过开展线下体验活动,使游客能够亲身体验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助力美丽乡村焕发活力,并激发更多观众参与实地体验的意愿。《我的阿勒泰》巧妙融合文化元素、旅游景观与引人入胜的情节,在新疆特色旅游景区的背景下,通过深入探索新疆地理、历史、文化及生活方式的独特魅力,唤起观众对未知世界的憧憬与向往。互联网平台更是助力了媒介仪式的传播热潮,如短视频平台上“那远山呼唤我,曾千百次路过”歌词的流行以及“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文案的兴起。两部剧集将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景观以影视化的方式具象化地进行呈现,满足了大众对远山旅游的向往,进而在旅游经济复苏的消费趋势下,将媒介诉求转化为实地的消费增长。
(二)城市互动场域中的形象认同
《去有风的地方》和《我的阿勒泰》的成功,关键在于大众文本意义的创造与互动重构。其中,《去有风的地方》作为大理旅游的标志性宣传案例,是华策(厦门)影视有限公司与地方政府紧密合作的结果。大理文旅部门在取景、场地协调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特别是在主要场景凤阳邑村的改建上,村委会的全力协助使得拍摄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借此剧热播的契机,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和旅游局积极推动文旅融合、深挖旅游资源、创新景点设计、规划特色线路,并提升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品质,有效满足了游客需求,为城市形象塑造及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同样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与阿勒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携手打造的《我的阿勒泰》“文旅合作新生态”,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典范之作。该项目围绕文化符号共创、生态基金共募、旅游专线共设、线下活动共办、会员机制共建等五大核心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旨在开启文本、影视、旅游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德布雷的媒介域理论认为,每一个媒介域都围绕最新的、具有支配作用的媒介组织起来,每一个社会都依赖当时主导的媒介域来构造自身的文化,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12]。影视剧作为当代社会主导性的媒介领域,在塑造城市形象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两部剧集所引发的文本互动,有效激活了不同观众群体的文本记忆,并在此基础上激发观众创造个人文本。
四、结语
影视剧作为大众文化艺术形式,凭借叙事魅力和传播效应,在地区文化旅游开发和城市形象塑造中占据核心地位。《去有风的地方》和《我的阿勒泰》推动了人文与情感叙事的融合,能够有效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发挥多维力量在城市形象建构中的协同作用,深化观众对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和人文精神的认知,进而有效传播地区特色城市形象。
[参考文献]
[1]卜亭亭.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研究[D].秦皇岛:燕山大学,2021.
[2]余燕莉.电影如何表征马克思主义?:对居伊·德波论文电影的景观批判及其潜能的考察[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2(02):14-22.
[3]陈学.生命与表现:苏珊·朗格符号形式美学思想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23.
[4]薛征.解域、脱节与生成:德勒兹电影美学的基本逻辑[J].文艺争鸣,2017(12):94-98.
[5]张兴华.影像与现实的互文:《去有风的地方》对云南文旅形象的塑造效应[J].电影评介,2023(07):109-112.
[6]都岚岚.情感的文化政治[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4(02):114-119.
[7]吴冠军.论“主体性分裂”:拉康、儒学与福柯[J].思想与文化,2020(01):180-201.
[8]郭广.本雅明的“经验”概念及其现代性批判意蕴[J].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2(01):289-298.
[9]李世书.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与双重解放:马尔库塞的生态批判与革命[J].江西社会科学,2016(06):18-25.
[10]陆兴华.如何在景观社会原创出政治与艺术?:从德波尔—阿甘本的景观批判出发[J].文艺研究,2010(07):29-38.
[11]向云驹.论“文化空间”[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3):81-88.
[12]朱振明.媒介学中的系谱学迹线:试析德布雷的方法论[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03):87-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