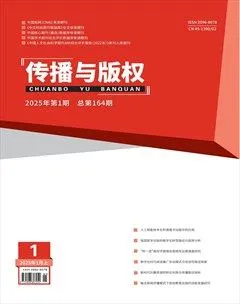美食纪录片中乡土文化空间的生产与价值体现
[摘要]文章阐述乡土文化空间的形成与《大地家宴》的内容表达,根据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生产三元辩证法,认为乡土文化空间的形成可以从“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乡村精神文化、乡村社会文化”等三个维度出发进行理论架构。基于此,文章对美食纪录片《大地家宴》中乡村文化空间的生产维度和生产结构进行探究,发现《大地家宴》乡土文化空间的生产聚焦在“家宴”的镜像映射,生产结构在“大地”的作者隐喻下呈现“生存—生活—生命”一体的交融式构造。从整体上来看,美食纪录片《大地家宴》在视听影像手段的加持下,通过对乡土文化景观的感知呈现,完成其乡土文化空间的价值体现。
《大地家宴》;乡土文化空间;生产;价值体现[关键词]
在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驱使下,基于地缘关系、血缘关系、情缘关系形成的乡土文化,已成为承载人们思想与信仰的重要载体,并揭示了一个共同而客观的空间基本轮廓。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在以传统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乡土文化形成的空间场域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效应,它把人类行为的基本属性或者基本特征纳入某种特定秩序,而这种特定的秩序便是人类对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乡村精神文化、乡村社会文化的直观感知。美食纪录片《大地家宴》通过展现不同地域的一席家宴,以象征着物态文化的当地各种代表性美食串联起民俗传统和精神文化,在相互观照中连接人们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并借助记忆中美食味道的再现释怀乡愁,承载习俗记忆,表现浓厚风情,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乡土文化空间。
一、乡土文化空间的形成与《大地家宴》的内容表达
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社会生产”理论认为,空间不仅是社会关系的载体,更是这些关系的组成部分,“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以及“表征的空间”这三个核心要素共同构成了空间本体论的三元一体社会理论框架[2]。在这一框架下,空间作为自为本身的存在,既保留了形塑社会关系的功能,又获得了与社会表征互动时所产生的特殊能动性。虽然列斐伏尔首次提出“文化空间”这一概念,但他并未进一步详细阐释。不过可以认为,文化空间的构建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源自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生成,而非固守于静态的物质形态或客观存在的实体。这意味着文化空间不仅反映了社会文化实践的多样性和非齐一性,也体现了人类行为本质中的选择性和创造性。具体来说,乡土文化空间的形成过程与社会实践密切相关。乡村是一种区别于城市的社会形态,乡土文化可被视为人类通过对乡村景观的感知和认同而定义和强化的文化形式。这一文化形式既包括对乡村自然生态的感知,也包含对其本质和力量的认同,反映乡土文化的独特性。乡土文化往往通过自然景观与传统建筑等形式展现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具有强烈的群体性和原生态特征,与华夏农耕文明密切相关。
在这一背景下,乡土文化空间的形成不仅是对乡村自然生态的感知,还受到乡村精神文化和乡村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乡村作为一个社会空间,不仅承载着日常生活方式和民俗文化,还蕴含着特有的社会文化价值。乡土文化空间的形成过程,正是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乡村精神文化、乡村社会文化交织互动的结果。乡土文化空间具有一种独特的“赋形”功能,即乡土文化空间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存在,也在精神和社会层面上不断被生产、定义和再创造,成为社会性现实的一部分。从价值载体的角度来看,乡村的文化价值不仅表现为它承载的物质空间,还包括其所代表的文化象征意义。这些文化元素通过日常生活、饮食习俗等形式得到传递和强化,成为乡土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与乡土文化紧密相连,它不仅反映了乡村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也传递了区域文化的特征和精神文化的内涵。因此,乡土文化空间的形成离不开饮食这一文化载体的支撑,饮食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成为乡土文化空间的实现方式之一。同时,饮食文化作为乡村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乡土文化空间得以实现的核心载体,反映了乡土文化的普遍性和地方性。基于此,通过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乡土文化空间的多层次构建过程得以明晰,揭示乡土文化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美食纪录片《大地家宴》中乡土文化空间的形成与呈现主要围绕“大地、归家、乡宴”等多角度展开,借助五位主人公的各自经历向外衍射,共同讲述了关于共享、大地、家乡、亲情及食物的故事,形成了特殊的表达形式。通过安徽伏岭的“十碗八”、宁夏隆德的“暖锅”、浙江青田的“石头宴”、广西尧告的“百家宴”、云南凤羽的“丰收宴”等,《大地家宴》在合理化的内容表达中,形塑“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乡村精神文化、乡村社会文化”等乡土文化空间形成的要素,并将美食所蕴藏的“文化主观性”“人物处身性”和“情感的触动与自觉”注入内容的表述,使乡土文化景观更易被感知,在人物跨越空间的情感延伸与重塑中实现对乡土文化空间的建构。
二、镜像与隐喻:《大地家宴》中乡土文化空间的生产逻辑
(一)“家宴”的镜像映射:《大地家宴》中乡土文化空间的生产维度
乡土文化空间的生产离不开“家”这一关键因素。正如钱穆所言,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之一切[3]。“家”既是文化状态,也是信仰心态,是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轴心,具有超越个体“小家”的广义内涵。文化通过融入社会实践和关系来确立自身权威,并接受“家”作为指令机制的约束。文化形成需要一种特殊的社会秩序,即人类通过增加各种可供利用的社会信息孕育文化生成,但信息供应的增加也带来控制压力,此时“家”作为增补机制调节信息准入,使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由此,“家”在人类社会关系和文化空间中具备不可化约的时间和空间属性,直接或间接嵌入文化空间的形成过程。在乡土文化空间的建构中,“家”占据核心位置,其自身话语秩序对乡土文化空间的形成要素产生深远影响。乡土文化空间与“家”高度关联,“家”既塑造乡土文化空间的结构,又在该空间的构建过程中不断完善自身,两者形成一种动态互构关系。具体而言,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乡村精神文化、乡村社会文化等关键要素均以“家”为核心,通过社会生产实践得以生成,“家”的位置也在乡土文化空间的不断构建中得以确立并发展完善。因此,乡土文化空间成为“家”的镜像,彰显二者在文化生成中的深度耦合关系。
就美食纪录片《大地家宴》而言,其乡土文化空间的生产维度将聚焦“家”的镜像映射转向聚焦以“家”为核心的“家宴”。“家宴”一词,通常意指家庭成员团聚共饮,或个人举办的宴会,与国宴等相对而言。如果说把“家宴”界定为一种“可表达的视觉之物”,那么这种“可表达的视觉之物”又会促使“可表达的感觉之物”诞生,这种“可表达的感觉之物”则可以被视为乡土文化空间。此时的乡土文化空间必须依赖视觉之物“家宴”的可视性才能在影像中表现,即“家宴”的镜像可映射出乡土文化空间的生产维度。综上所述,《大地家宴》中乡土文化空间的生成离不开“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乡村精神文化、乡村社会文化”三个维度,而这三个维度的展现和形成聚焦在“家宴”的镜像上并被映射出来。
乡村作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场所,为乡土文化的生成提供空间,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作为文化空间生产的物质基础,与乡土文化的形成密切相关。《大地家宴》中的故事发生在不同地域,通过不同的“家宴”形式映射了各地的乡村自然生态环境,如“十碗八”“暖锅”“石头宴”等宴席形式,承载着地域独特的“家宴”记忆和文化底色。乡村精神文化作为乡土文化空间的表征维度,涉及文化关系、伦理秩序、道德观念和地域认同等元素,这些元素共同塑造乡土文化的内涵。在《大地家宴》中,每一场“家宴”都反映了当地的精神文化,如安徽伏岭的“十碗八”象征成长,宁夏隆德的“暖锅”体现情感交融,浙江青田的“石头宴”展现创新精神,广西尧告的“百家宴”标志着地方文化的寻找,云南凤羽的“丰收宴”象征对“家”的回馈。事实上,乡土文化空间的生产维度实质上便是“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乡村精神文化、乡村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而这需要中介物来进行寄托。在美食纪录片《大地家宴》中,“家宴”充当这一中介物,它在传达“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乡村精神文化、乡村社会文化”的同时完成对乡土文化空间生产维度的镜像映射。
(二)“大地”的作者隐喻:《大地家宴》中乡土文化空间的生产结构
乡土文化空间的生产结构与其生产维度密切相关,可以通过“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乡村精神文化、乡村社会文化”的内在职能来分析。冯天瑜在《中国文化生成史》中将文化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与心态文化”[4],基于这一分类,乡土文化空间的生产结构可以被理解为“生存—生活—生命”三者交融的构造,其中,“生存”对应物态文化与乡村自然生态环境,“生活”对应制度文化与乡村社会文化,“生命”与行为文化、心态文化及乡村精神文化相关联。在《大地家宴》中,这一交融式生产结构通过“隐含作者”的创作隐喻得以表达。韦恩·布斯提出的“隐含作者”指在创作过程中作者通过编码传递思想的一种理想化形象[5]。申丹则进一步解释,“隐含作者”是在创作时通过特定立场对文本进行理想化编码的形象,它提供文本的解码路径[6]。换句话说,“隐含作者”在编码过程中选择能够引导观众解码的中心思想或视角。
在纪录片中,“隐含作者”的概念尤为重要,它是“真实作者”在创作状态下通过对事实的感悟形成的理想化形象,即通过构思、叙事策略和价值观念输出,“隐含作者”向观众传递信息。而在观众解码过程中,“隐含观众”与“隐含作者”之间形成互动。“隐含观众”不是个体或群体的存在,而是一种抽象化、类型化的存在,由作者主观意识预想出来,而真实观众则是由一个个客观存在的个体组成[7],这一群体通过对文本的感知与解读,反过来影响“隐含作者”的形象。《大地家宴》展现了乡土文化空间“生存—生活—生命”的交融结构,“隐含作者”通过对这些生产维度的深入考察,提出一种新的文化连接方式。在此过程中,“隐含作者”形象在与观众的互动中发生变化,实现多样化。因此,纪录片的创作不仅是编码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解码与反馈过程,展现了乡土文化空间多维度的生产结构。
在《大地家宴》中,“隐含作者”的角色象征为“大地”,这一隐喻契合了乡土文化空间“生存—生活—生命”三重交融的生产结构。一是“大地”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人与自然、土地及故乡的紧密联系,这与乡土文化空间的生成结构高度一致;二是“大地”在实践层面上代表了社会生产中的关系属性,对乡土文化空间的构建起到基础性作用。《大地家宴》通过“大地”隐喻呈现乡土文化空间的生产结构。例如:安徽伏岭村的“十碗八”体现了徽州传统与乡土文化的联系;宁夏隆德的“暖锅”反映了人与自然的情感纽带;浙江青田的“石头宴”融合了“石雕文化”和“饮食文化”,表现了历史与社会关系的变迁;广西尧告的“百家宴”展示了传统食材与烹饪技艺的再生;云南凤羽的“丰收宴”凸显了“大地”在新时代的社会意义。在纪录片中,“隐含作者”“大地”通过隐喻连接过去与现在、故乡与他乡,映射社会空间、关系与观念的变迁,体现乡土文化空间的“生存、生活、生命”三个维度。尽管在解码过程中“隐含作者”的形象可能发生变化,但真实观众依然能够感知乡土文化空间的交融结构,并理解其隐性中心。故此,《大地家宴》通过“大地”隐喻展示了乡土文化空间的多维度生产结构,揭示了文化与社会变迁的深层联系。
三、文化景观的感知呈现:《大地家宴》中乡土文化空间的价值体现
麦克卢汉认为,人类各类感知方式之间存在一种平衡关系,即“感知比率”。当某一感知方式占据主导地位时,其他感知方式的表达则会受到抑制,即视觉表现较为突出,而味觉、触觉、嗅觉等相对较弱,但可以通过视觉间接呈现。通过这种平衡,各种感知方式共同实现了麦克卢汉所提及的“感知比率”。在纪录片中,影像由线条、光线、色彩和声音等元素构成,其被人类创造和接收方式均为视觉和听觉途径,但是其所指对象并非仅限于视觉和听觉感知,还包括触觉、味觉和嗅觉等感知方式所体验到的内容。简而言之,影像所指涵盖了包括视觉在内的所有感知方式指向的目标。
基于此,《大地家宴》中乡土文化空间的价值可以通过影像的视听效果被感知。实际上,各种感知方式皆能体验到事物的某一方面,如味觉体验味道、听觉体验声音,这一方面正是相应感知方式所完成的目标。然而,各类感知不但接收对象,还传达所接收到对象的感知信息,因此,这个过程便需要寻找中介物进行寄托。中介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它产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实践关系和认识关系的桥梁和纽带”[8]。根据上文所指出的乡土文化空间的生产维度和结构,乡土文化景观便可成为这一中介物,对乡土文化空间的价值进行体现。景观这一词汇源自拉丁文,含义为“观赏、察看”,指呈现的可视景象或景色[9]。聚焦到《大地家宴》,其乡土文化景观主要涉及“物质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景观”两种类型,这两种景观类型在视听影像手段的加持下进行感知呈现,实现对《大地家宴》中乡土文化空间的价值体现。
《大地家宴》中的“物质文化景观”主要聚焦在各地的环境特征,在视听影像和内容表达中呈现“天人合一”的感知体验。中华文明的农耕文化激发起古人对自然生活现象的关注与反思,塑造“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与审美理念。《大地家宴》通过精细入微的镜头语言描绘了安徽伏岭等地的地理环境特色,展现了各地村民就地取材,将自然的馈赠通过精心的烹饪转化为“家宴”上一道道美食的生活场景,表达了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激之情,而这也正是对“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动诠释。此外,其镜头方式既包括稳定的固定镜头,也包括推、拉、摇等各种动态镜头,形成了以固定镜头为主、运动镜头为辅的拍摄风格,营造了身临其境的感知体验。在声音设计方面,其背景音乐和环境音效的巧妙融合,将“天人合一”的感知体验进行呈现,体现《大地家宴》的乡土文化空间价值。
《大地家宴》中的“非物质文化景观”则集中于传统民俗节庆和家宴美食制作技艺的展示。民俗节庆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以及凝聚民族集体意识的仪式化庆祝形式,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并展现出鲜明的族群情感认同符号特征[10]。《大地家宴》通过展现民俗节庆,深化了美食与文化、情感的联系,其中“家宴”均承载着历史的智慧与劳动的结晶,并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呈现精湛与独特的技艺。此外,《大地家宴》还通过情感化的叙事策略,将民俗节庆背后的动人故事与乡土情感紧密联系,进一步增强观众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总体而言,《大地家宴》中的乡土文化空间价值,在乡土文化景观这一中介物的承载下,得以全面而深入地展现。无论是“物质文化景观”所呈现的自然与人的和谐共生,还是“非物质文化景观”所展现的民俗节庆和传统技艺的魅力,《大地家宴》都通过视听影像手段将其进行呈现,使乡土文化景观反映乡土文化空间价值的本性,并通过自身的感知呈现完成对乡土文化空间价值的最终表达。
四、结语
近年来,以展现乡土文化为主题的纪录片不断涌现,引发了乡土文化创作热潮,这类纪录片以乡土文化为根基,形成系列化和体系化的创作主题,不仅具备丰富的影像文献价值,为乡土文化留下珍贵的影像档案,而且有效推动乡土文化的广泛传播,助力新时代乡村振兴。《大地家宴》以不同地域的家宴美食为纽带,借助各地乡村民俗传统和文化,唤起人们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形成独特的乡土文化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该类纪录片的创作视野。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4]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5]BOOTHW.IsTherean“Implied”AuthorinEveryFilm?[J].CollegeLiterature,2002(02):124-131.
[6]申丹.再论隐含作者[J].江西社会科学,2009(02):26-34.
[7]王东,李晓磊.隐形的权威:“十七年”文学中的隐含读者“工农兵”[J].文艺争鸣,2020(06):59-63.
[8]徐强.中介论[J].江汉论坛,2000(01):37-39.
[9]张一兵.颠倒再颠倒的景观世界:德波《景观社会》的文本学解读[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6(01):5-17.
[10]刘秀梅,董洪哲,韦雨生.情感认同与互动共享:基于SIPS模式的民俗节庆短视频传播研究[J].中国编辑,2020(08):8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