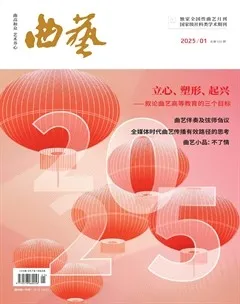青龙镇:上海最早的曲艺码头
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生活,是都市繁华的重要标志。而作为国际化的现代大都市,上海就是一座文化大码头,聚集着各种大型演艺中心和剧场。追根溯源、文脉流淌,其实早在唐宋时期,“海丝”名镇青龙镇,就孕育着上海的文化气质。
一、青龙镇有专业的文娱场所
唐宋时期,通江达海的吴淞江畔青龙镇,凭借天时地利等因素,成为古上海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考古发现的遗址表明,时有“小杭州”之称的青龙镇,至少在南宋后期,就已经出现了专门的文化娱乐区,设立于青龙镇三十六坊之一的平康坊。明正德《松江府志》曾记载,青龙镇上辟有瓦市,“平康坊,中亭桥西,有瓦市在焉”。当时的华亭县城却没有如此的文献记载,这表明青龙镇是上海地区最早出现“都市”娱乐区的文化重镇。青龙镇的瓦市,源自于商贸发达的市镇,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浓郁的商气、文气和人气,为青龙镇文化娱乐业的勃兴,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生态和基础条件。
当年的青龙镇,作为江南的大镇、重镇、雄镇和强镇,居民区与商业区相隔离的坊市制度被废除,商贸与城镇一体化,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出现了文化娱乐市场“瓦市”。瓦市又称瓦舍、瓦肆,始于宋代,是城镇演艺和娱乐的聚集区或商业娱乐中心。《梦粱录》曾解释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意,易聚易散也”。瓦市原本是临时性的文化和商贸集市,其中最吸引人眼球的是勾栏。勾栏就是栏杆、栅栏,街头艺人在空地上用绳子或者栅栏围起来,形成比较固定的演出场所。有一些勾栏比较豪华,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文化剧场,戏台通常高出地面,台口围着栏杆,戏台前部是表演区,后部是演员装扮和休息的区域。前后台之间,用屏风、布幔、台帐相隔。观众席则设在戏台对面和左右两侧,成三面围观的态势,具备了剧场的雏形。
据《青浦县志》所载的《青龙赋》记载,当年,青龙镇上的瓦市中,音乐、歌舞表演引人入胜,场面热闹非凡。“讴歌嘹亮,开颜而莫尽欢欣;阛阓繁华,触目而无穷春色”“杏脸舒霞,柳腰舞翠”,形象描绘出了青龙镇当年瓦市内女艺人在勾栏演出歌舞的真实情形。除了音乐、舞蹈,青龙镇的瓦市勾栏中有杂技、魔术、相扑、球杖踢弄、弄虫蚁、叫果子、装鬼神等传统百戏,有猜谜、合生等赌博性质的文字游戏,还有与文学关系密切的杂剧、木偶戏、皮影戏、说书、小唱、诸宫调等。讲小说是当时颇受欢迎的一种文艺样式,类似说书,内容一般是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历史之类的故事。小唱是用简单的方式演唱通俗歌词,是当时的流行歌曲。
瓦市中的文艺表演相对规范,而一些称为“路歧”的街头艺人,就在一片空间中随时而为即兴表演,不用交纳场租费,是街头文化的一种代表。他们不卖票,而是吸引路人观看,每每在一个节目结束或是演到了关键时刻戛然停息,向观众乞讨收费,然后再继续表演。
总的来说,青龙镇里的娱乐节目,都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形式,非常适合民众的艺术欣赏趣味,满足了人们赏心悦目的娱乐审美需求。
作为上海最早对外贸易的港口码头,青龙镇的瓦市海纳百川。不仅街市上“宝货富东南之物”,而且,“市廛杂夷夏之人”。西域的音乐与舞蹈,纷纷涌入青龙镇。前些年,遗址上出土的两件唐代釉腰鼓,便是很好的实物证明。多元融合的演艺活动,更好地满足了中外贸易商人和当地市民文化娱乐休闲的需求。瓦市勾栏的演出内容丰富多彩,包容了异域文艺,往往通宵达旦,吸引不少中外游客和民众追捧与观看。瓦市里的节目形式生动活泼,各种艺人的演艺活动,极大地满足了镇上各色人物、各个阶层,尤其是老百姓和商贾的需求。为了服务勾栏里的演职人员和观众,瓦市里往往还有饮食服务行业,还有医生、相士、卖百货药品、唱估衣(唱着歌卖衣服)、探博(赌博)、剃剪等各色服务。各种游民和江湖术士,在瓦市演艺的大环境下各自谋生。
青龙镇的瓦市,融汇了东西方艺人,营造了文艺样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共生共荣、多元融合的生动局面。打破了中外文化、社会阶层的隔阂。不同人群、不同种族、不同阶层,在这里相互交流,获得精神上的愉悦。这标志着当时青龙镇文化市场的成熟和文化娱乐业的发达。作为上海最早的“都市”文化娱乐的演艺码头,青龙镇瓦市对研究上海大众文化的历史源头具有重要意义。
二、青龙镇有良好的文化生态
南宋时期,临安(杭州)是南方文娱活动的中心,其勾栏瓦舍中的艺人和“打野呵”的“路岐人”经常流动演出并向四周辐射,影响并带动江南文娱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宋末元初的松江人丘机山就是一位讲史艺人,主要讲说《通鉴》,历数汉唐书史文传中的争战兴废。他主要活动于临安与青龙镇一带,行迹遍及江南,远至福州,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条和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条均提及此人。元末明初,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记录了他“宋季元初以滑稽闻于时,商谜无出其右”“遨游湖海间,尝至福州……”的行迹。
这里所说的讲史是一种讲说史书的文艺形式,类似于评书评话,主要讲述历史故事。商谜是一种以猜谜形式为特征、滑稽风趣的说唱艺术,一般由出谜语的“商者”,与猜谜语的“来客”两方表演,双方有问有答,反复斗智,其中有不少滑稽风趣的笑料。而像丘机山这样以讲史、滑稽、商谜闻名于世的艺人涌现,说明了青龙镇文化生态的良好。
文娱繁荣的景象也吸引了更多的文人墨客关注、投身其中。
元代词曲作家夏庭芝(约1300—1375)(字伯和,一作百和,号雪稂簇蓑,别署雪蓑钓隐、雪蓑渔隐,松江人),出生于华亭巨族世家,家中藏书甚富。渊源家学养成了他才华横溢的气质。当时闻名长三角地区的文学家杨维桢就曾是他的塾师。元末张士诚起义,占领松江,夏庭芝隐居于泗泾,将书室改名为疑梦轩。他交游很广,与当时的文人、剧作家、艺人接触颇多,戏曲作家张择、朱凯、朱经、钟嗣成等人都是他的同道友好。夏庭芝撰著的戏曲表演论著《青楼集》,被后世视为与《录鬼簿》同等重要的戏曲史专著。张择《青楼集·序》说他:“遍交士大夫之贤者,慕孔北海,座客常满,尊酒不空,终日高会开宴,诸伶毕至,以故闻见传有,声誉益彰。”《录鬼簿续篇》中,也列有夏庭芝,并称他“文章妍丽,乐府、隐语极多”。
夏庭芝著作的《青楼集》,记述了元代从北方到江南的繁华市镇中一些女演员的生活片断。专条记录的就有74人,如杂剧艺人珠帘秀、李芝秀,南戏艺人龙楼景、丹墀秀,慢词、诸宫调、弹唱、说书艺人赵真真、杨玉娥、顾山山、李童童等。附见各条的又有42人。条文记述了她们的生平、艺术特长和轶事,以及当时的一些戏曲作家、散曲作家、诗人与她们的交往。书中还记载男艺人的事迹,涉及者有30多人。《青楼集》所记艺人涉及今上海地区的就有连枝秀、翠荷秀、李芝仪、闽童等。在记述艺人生活片断时,夏庭芝往往伴以评论。从评论中可以看出他追求传神、风趣的审美旨向。如认为说唱演员时小童“善调话—即世所谓小说者,如走丸坂,如水建瓴”,称善唱慢调的王玉梅“声韵清圆”,称般般丑“落魄不羁工于笑谈,天性聪慧,至于词章,信口成句,而街市俚近之谈,变用新奇,能道人所不能道者”。
《青楼集》是一部较有系统地记载古代戏曲、曲艺艺人活动的专著,对后世研究古上海地区元代戏曲、曲艺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元末杨维桢所作的《四游记弹词》(由《侠游录》《仙游录》《梦游录》《冥游录》组成)是现知最早以“弹词”命名的唱本。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是元代文学家、弹词作家、书画家和戏曲家。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元朝泰定帝(泰定帝为元朝第六位皇帝,1323年至1328年间在位)时期中进士,曾任建德路总管府推官,江西等处儒学提举。张士诚据浙西,屡招不赴。杨维桢擅作乐府,多以史事与神话为题材,纵横奇诡,文字藻饰,明初王彝讥之为“文妖”。他善行、草书,有刚健之气,又喜游山水,与陆居仁、钱惟善合称为“元末云间三高士”。元至正九年(1349),杨维桢开始隐居松江和青浦,常至青龙镇,与青龙镇任氏、章氏名门望族交往密切。他曾为任仁发题诗①,为章元泽撰《归来堂记》;又撰青龙镇《重修隆福寺记》,记录了任氏家族修葺隆福寺的事略。后因兵燹,杨维桢携家居于松江,筑室百花潭上,号小蓬台,后葬于松江天马山。
《四游记弹词》是杨维桢取材唐人传奇并加以敷衍而创作的。明代文人臧懋循汇编《元曲选》,在《负苞堂文集》卷三的“弹词小记”中曾有记述:“若有弹词,多瞽者以小鼓、柏板,说唱于九衢三市。亦有妇女以被弦索,盖变为最下者也。近得无名氏《仙游》《梦游》二录,皆取唐人传奇为之敷演。深不甚文,谐不甚俚,能使呆儿少女无不入于耳而洞于心,自是元人伎俩。或云杨廉夫避乱吴中时为之。闻尚有《侠游》《冥游》录,未可得,今且刻其存者。”后来臧懋循刻成了杨维桢创作的《仙游》《梦游》《侠游》三种,可惜流散,今已无传本。
三、青龙镇是申曲的孕育之地
本滩,是本地滩簧的简称,亦称申滩、沪滩,演唱类曲种,是沪剧之前身,源起于上海地区吴淞江畔青龙镇一带,原始形态是上海农村的田山歌,以及江南农村的民歌。
上海田山歌分东乡山歌与西乡山歌两大类,在黄浦江以东的原川沙、南汇、上海和奉贤部分地区的民歌称东乡山歌,而黄浦江以西的松江、青浦、金山、奉贤部分地区的民歌称西乡山歌,以宫调为多,亦有羽调式与商调式的,结构也是上下句或略微变化的对仗式。本滩的曲调深受此影响。
清乾隆年间,安徽的花鼓戏传入上海。田山歌随之吸收花鼓戏的演唱形式,逐渐演变成了具有上海特色的艺术品种,因安徽花鼓戏的影响,故也有“花鼓戏”之称,其腔调则被称为【花鼓调】。
清嘉庆十八年(1813),青浦人诸联(1765—1840?)所著的《明斋小识》云:“花鼓戏传来三十年,变者屡矣。始于男,继以女,始于日,继以夜,始于乡野,继于镇市,始或村俗农氓,继沿于纨绔子弟”。据此书刊印年份推算,花鼓戏传入上海时,在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前后。清道光年间(1821—1850),花鼓戏出现了“对子戏”的表演形式,由上手(男角)、下手(女角,也由男子装扮)操胡琴,击响板,自奏自唱,以一生一旦居多,也有一丑、一旦乃至两个旦角的,其作品多表现清代江南农村集镇家庭社会生活,其中爱情婚姻题材居多,如《拗木香》《十打谱》《拔兰花》《卖红菱》等。花鼓戏后来又发展成有三个以上演员的“同场戏”。“同场戏”由演员按剧情需要扮演角色,分生、丑、旦三个行当,另设专人操乐器伴奏,有三四个角色的称“小同场”。有七八个角色的称“大同场”。“同场戏”一般在茶馆中临时占一角面对茶客演唱,若逢节日、庙会或农闲期间,则搭台演唱,称之“唱高台”,作品有《打花包》《陆雅臣》《庵堂相会》等。
花鼓戏屡遭官府禁演。清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又明令禁演花鼓戏。至19世纪80年代,上海花鼓戏艺人纷纷从农村进入上海市区的租界;清光绪三年(1877),开始有女演员参加,实行男女合演。据《沪剧先辈图》所列,1890年以后,活跃在上海的著名艺人有金鉴昌、杨惠卿、胡兰卿、杨炳荣及女艺人陆小妹等。他们以卖唱方式自奏乐器,活动于街头巷尾,行话称为“跑筒子”,也叫“卖‘三寸(喉咙)’”;其次是围地设点,空场主唱,谓之“敲白地”。虽然禁令尚未解除,但当时苏滩已在上海盛行,花鼓戏艺人为避免被禁,也仿效苏滩争取观众,故而有意将花鼓戏改叫滩簧,为有别于苏滩,便称之为本地滩簧,即“本滩”。
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许何方为首的戏班首次进入上海英租界的四海昇平楼演唱,以后艺人们组成五、六人规模的演唱班子,仿效苏滩坐唱形式,陆续固定在茶楼演唱,那时是搭台坐唱,并在桌帏、椅披上绣上班社或主要演员名称。常演曲目有《三国开篇》《卖红菱》《卖桃子》等“九计十三卖”,后期亦演唱《珍珠塔》《文武香珠》等长篇。三四年内,仅在法租界说唱本滩的茶楼书场就发展到8个以上,演唱班子也增加到了8个左右。从此,本滩逐渐进入喜庆堂会演出。1913年后,上海市区建立了第一家游艺场所楼外楼,接着新世界、大世界、先施屋顶乐园等一大批大型游乐场纷纷兴建演艺场所。1916年,本滩艺人丁少兰首次献艺于天外天游乐场。此后,本滩就逐渐从茶楼书场进入游乐场。随着听众面的扩大,艺人队伍也逐渐发展,涌现了一批八人以上的班社,如邵文滨班、马金生班、沈桂英班、丁少兰班等。1917年以后,本滩由原来每场一至一个半小时的插场演唱,扩至每场四个小时的正场演唱,并改变了坐唱形式,恢复花鼓戏以前的走唱形式。台上一桌二椅,演员化妆表演,不仅要有手面动作,而且讲究台步、身段等形体动作之美,表演艺术日益求精。这一阶段,各个班社纷纷以“申滩时调”“改良时曲”“改良本滩”“时事本滩”“改良戏曲”等名称标新立异。1920年,本滩改称申曲,逐渐脱离曲艺形式,向成熟的戏曲形式演变,后来发展成了江南重要的戏曲剧种沪剧。
时至今日,原青龙镇一带的白鹤、重固、赵巷等乡镇仍然是国家级的“沪剧之乡”,上海沪剧院的“非遗”传承培训基地,依然有一大批申曲爱好者。这里人人喜爱沪剧,个个善唱能演,涌现了无数的曲艺和沪剧“达人”,创作了众多的现代曲艺与戏曲作品。这也是青龙镇作为上海都市最早演艺中心文脉传承的结果,更彰显了青龙镇作为上海国际化文化码头源头的重要性。
注释:
①任贤才与杨维桢交游相当密切。任贤才常邀他至其家中,校雠商榷,杨维桢极爱重之。任仁发擅长书画,尤善画马、人物,曾奉旨画《渥洼天马》《熙春天马》二图,元仁宗诏藏秘书监,其工力足与赵孟頫相敌,杨维桢以为其画马“法修而神完”。任氏家族为青龙镇大族,任仁发当时最为昌盛和负有盛名,“吾松胜国时最繁富,青龙有任水监家,小贞有曹云西家,下沙有瞿廷发家……”任家在青龙镇东北筑有来青、览晖二楼作为“延宾之所”,杨维桢曾作诗:“大江如龙入海口,青山似凤来云间。任家高阁东西起,左江右海南青山。锦鱼烧尾春前花,读鹤传书天上还。老子胡床一横笛,双成仙佩响珊珊。”
(作者:上海文史研究馆员、上海市文联委员、教授)
(责任编辑/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