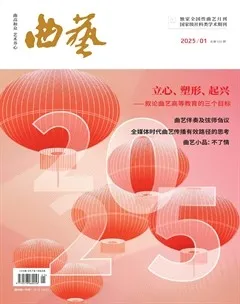曲艺伴奏及弦师刍议
在“歌、舞、乐”融合的中国民间艺术中,民族乐器必不可少地充当着伴唱奏乐的角色,不仅烘托了氛围和情绪,也为表演提供了艺术支持。曲艺的艺术创造也不例外,从击打响器到丝弦管笛,从吹拉弹打到滑抹捻颤,曲艺伴奏无不对口头语言“说唱”叙述的表演起到支撑、垫补、保调、稳场的作用,甚至曲艺伴奏者——弦师还需参与到舞台表演中“跳入角色”和“帮衬唱腔”,与曲艺演员一样有着“一人多角,一专多能”的艺术特点。而如今,曲艺伴奏的研究和建设却显得乏力和无助,曾经的五音联弹、连连叫好的伴奏盛况似乎已成为过去,曾经充当着“曲艺指引者、唱腔伴奏者、作品创作者”的弦师,如“三弦圣手”白凤岩、京韵大鼓韩德福和钟德海等老一辈却后继无人,他们指尖上那独有的伴奏手法和技术技巧也未被较完整地保留和记录。故可言,对曲艺伴奏及弦师的研究滞后制约了曲艺传承和发展,需要得到业内的重视。本文以曲艺伴奏为切入点,对曲艺伴奏的重要性、特殊性和亟须性予以分析和阐述,以期加大对弦师作用的重视,对伴奏艺术的肯定,从而把技术留下来、把新人带出来、把作品写出来、把曲艺托起来。
一、曲艺伴奏的重要性
在曲艺艺术的表演中,伴奏虽说处于听赏的从属地位,但就其艺术构成来说,曲艺伴奏对情绪的渲染、情景的变换、唱腔的领板、摹学的辅助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弦师的纷繁手法中,将音色、板眼、调高、拟声、加花等展现,以配合声腔变化和动作展示,与演员共同完成作品展示。因此,曲艺伴奏有着“三分唱、七分随”和“绿叶之于红花”之喻。
(一)曲艺伴奏是舞台表演的“成员”

不同于戏曲伴奏的幕后作场,曲艺伴奏往往位于台前以亮相舞台之上,并以自我伴奏和乐队协奏两种形态呈现。中国民族乐器的管弦之韵与曲艺艺术中式的典雅之境相得益彰、融为一体,可使观赏者瞬间获得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视听一致性。与此同时,无论是自我伴奏还是乐队协奏,伴奏与声腔相互依附和相互穿插,其中伴奏对声腔的美化、托保,声腔对伴奏的引领、指挥,两者你强我弱、你高我低、你进我出的相互裹挟、相互融合,传入耳廓,沁入心脾。
其中,以乐队协奏为主要伴奏形态的曲种表演,不同乐器的音色象征、拟声描摹也丰富了艺术表达,乐器的特性也得到了展示,尤其在作品开头结尾、大小过门时,器乐伴奏的出现给了演员肉嗓休憩和调整的时机,也获得了大展身手的独立时间,快速高低转换、复杂琴弦交替等“炫技”表演,让曲艺表演增加了趣味和看点。
曲艺伴奏的弦师除了伴奏的“主职”外,还有着“跳进跳出”的脚色扮演和帮腔应和的“表演”职责。当曲本人物较多时,演奏胡琴、扬琴、琵琶、打击乐器的弦师都会跳进曲本中参与,多以节目中角色参与叙事的铺陈,也会跳出进行评议,丰富了情节,也增加了可观性。
(二)曲艺伴奏是演员表演的“助手”
好的弦师是“懂”演员的,也是被演员所依赖的。两者会因长期相伴而成为好伙伴、好搭档,如白凤岩之于白凤鸣、刘文友之于骆玉笙、钟德海之于孙书筠等,前者的在场就像给后者一颗“定心丸”和“镇海针”,让表演者坐怀不乱、从容面对。
之所以如此,便是曲艺伴奏在舞台上“扶持”“补台”的功能显现。当演员自身出现临时变化时,弦师的积极响应和主动调整成为曲艺弦师的必修功课,如演员出现调门、气息、音准等临场变化时,成熟的弦师们有着“眼看到,手给到”的迅捷,成为了演员突发情况处理的第一人,在观众不知觉的情况下化解险情,尽可能保全表演不漏破绽。
除了专业的弦师扶持外,当经验丰富、功力深厚的演员退居台后也会操起乐器为徒弟授课,虽不是专业的弦师,但在多年的耳濡目染中也获得一定的演奏技巧,尤其对声腔和伴奏之间的运行规律的精湛把握。如此有经验、有阅历的“伴奏”便成为了新一代曲艺演员专业成长、艺术养成的“扶手”,曲艺历史上像这样的师徒组合比比皆是,如此培养出来的曲艺演员定会“高点起飞、迎风远航”。
综上,曲艺伴奏是曲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故其“七分”的占比是不无道理的,此外,曲艺伴奏还影响了曲种命名,所用乐器逐渐被借用和固化成曲种名称成为标识,如“琴书”“坠子”“弹词”“鼓曲”“渔鼓”等,但受到名利、市场等因素的影响,曲艺伴奏的概念却逐渐被淡化,曲艺弦师的作用也逐步被弱化,这些对于传统曲艺的继承和传播都有着不小的破坏,需警惕。
二、曲艺伴奏的特殊性
中国的乐器自古就是以伴奏的形态存活于民间艺术,直至刘天华以二胡、琵琶为代表进行了器乐革新,将民族乐器从伴奏地位提升至独奏地位,获得了聚光灯的照射和观众的关注。不可否认,上述变革让民族乐器得到了自由和独立的发展,是中国民族乐器发展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但时至今日,我国高等教育中艺术类器乐专业人才产能过剩,社会需求远无法满足。然而在中国传统艺术如戏曲、曲艺、民歌领域,却苦于没有器乐人才给予配合,如此矛盾的现象正因为器乐伴奏存在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个性与共性、表演与摹学、即兴与默契的差异上。
(一)个性与共性
作为器乐的独奏艺术,其要求个性的张扬和独特的展现,不同的演奏者对于同一部作品都会根据自己不同的解读和认知,结合经验和阅历给予独一无二的版本演绎,从而百花齐放、异彩斑斓,这种个性化的处理在独奏中是被允许和宣扬的,也被称为多元的“二度创作”。但是曲艺是演员以本色身份用“口头语言”表演的综合艺术,其“口头语言”是不能撼动的表现方式,虽伴奏有着“七分”之重,但听得见、听得清的曲艺演员口头表达基本要求不可逾越,个性化的设计和演奏应当受限且要主动克制,因此曲艺的伴奏须向着“合作、共存”的共性方向发展,“弱化、让步”于口头表述。
在曲艺伴奏常用的随腔伴奏、垫补伴奏、对比伴奏中,“托随衬垫”成为主要的伴奏方法。在无音响的书场中,人声肉嗓与乐器声响不仅需要平衡,更需要有主次之分,因此伴奏在与声腔共行时,常以旋律音型、基本板眼、和弦乐音等简易搭配,仅起到“托腔保调”的作用,并且随着情绪强弱和快慢变化,做到不盖声腔、不抢风头、不带节奏的适度伴奏,即绿叶衬托出红花、衣服妆点出美人。因此曲艺的伴奏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既要时刻观察演员的举动,又要监听其他乐器的音响,既要平衡调整音量的大小,又要克制按捺不住的表现,掌握好伴奏的“度”,处理好伴奏的“界”,方能在曲艺伴奏中获得较好的伴奏效果。
(二)表演与摹学
正如开篇所言,曲艺伴奏不仅有着“服务”功用,还要有“表演”可能,甚至还需练就边奏边唱的“曲艺特技”。
置于舞台前的乐队弦师,与表演者形成了舞台表现的整体,这不仅仅要求伴奏的音响要与声腔共融,也要求弦师与演员共同完成作品演绎。与其说曲艺的伴奏是对声腔的支撑,不如说是对声腔的共情,伤心之处低音映衬,欢快之时板点配合,紧张之情紧密烘托,激昂之境众乐齐鸣,弦师的情绪表情、演奏体态也会进入台下观众的视野,共同将作品完整呈现,因此曲艺弦师的表演需要更入心、更入情、更入境。
曲艺中的自奏自唱是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独门绝技”,弦师或演员为了增加音色层次和强化情绪,在帮腔的部分会增加边演奏边说唱的片段,如此绝技断然不会出现在独奏的纯器乐表演中,是曲艺表演需掌握的独有特殊技能。
伴奏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弦师的“脚色摹学”功力上。为了剧情人物的需要,弦师会跳入脚色中摹学人物的神态、动作、语气等,这样的“摹学能力”也是独奏演员所不具备的。在技巧培养的同时,更要有“放得出去,收得回来”的表演能力,即摹学结束后迅速回到伴奏状态,遵循着艺谚“演谁像谁不是谁”的表演特征。
(三)即兴与默契
如果说器乐的专业培养是以乐谱为中心,那么曲艺伴奏则是以演员为标准。成熟的曲艺弦师因和演员长期磨合而使得各种曲牌旋律烂熟于心,因此在表演时多脱谱演奏,将目光始终聚焦演员和观众,展现伴奏弦师应有的业务能力和专业水平。如此,即兴的表演也有着曲艺“一遍拆洗一遍新”的艺术特点,尤其是坐堂弦师,不仅归纳总结了不同曲种的伴奏手法和演奏技巧,还谙熟大量的曲目及不同演唱者的风格特点,再根据观众的人群特点和现场实况选择适合的伴奏形态予以配合,因此弦师也有着曲艺演员“杂货铺”的灵活性。
曲艺伴奏的默契和即兴的生成还需要弦师有着一定的归纳和创新能力,对旋律骨架、和弦和声、手法技巧、演员特点等保持着灵敏的“嗅觉”,同时在与演员的眼神和动作交流中迅速捕捉演员意图,保持着“随机应变”的警觉。与评书表演“墨刻儿”和“道活儿”一般,能够根据框架自由发挥的便是伴奏艺术中的“道活儿”,而对着曲谱严格演奏的则就是“墨刻儿”了。这般即兴能力和默契程度唯有在长期磨合才会获得,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氛围中共同创作、排演、打磨、精化,但在分工精细的现代社会,这样的状态又何其难得呢?
综上所述,正因为弦师的“一人多角、一心多用”和从属地位,曲艺的伴奏不同于独奏。正如子弟书爱好者顾琳在嘉庆二年(1797)著《书词绪论》中第七节“调丝”中所述“好的弦师宛如弦之说书”,即弦师的演奏要强弱得当,与演员的气息声音达到一致,把唱词的头韵、尾韵、腰韵交代清楚,好像用弦子在歌唱,分不清是唱的还是奏;同时还要求弦师要心正,在练功时做到手口相应、心无旁骛,在伴奏时宁缺毋滥、不可胡弹,到了会弹之处也不可有意显露、故意显摆,最终达到“贵正大、贵和平、贵心正、贵敬畏”。
三、曲艺伴奏的亟须性
(一)艺术传承的需要
曲艺伴奏是传统曲艺艺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应作为整体统一看待,它的存在和表演已成为老书客翘首以待和新观众回味无穷的艺术构成,尤其是其“舞台呈现、一人多角、一心多用”的表演技能,共同构成了曲艺艺术特有的辨识标签。
1.艺术的简化盛行。如今为了考虑便携、成本等因素,很多曲艺表演以Midi伴奏为主要伴奏形式,甚至录制声腔后“还音”表演,以一个版本走穴数十个舞台。艺术的简化使得传统曲艺的表演形式也被观众粗暴地理解成与唱歌、唱戏无异,失去了曲艺艺术形态上的辨识度,这对曲艺艺术的传播形成了认知上的错误引导,从“头”便误入了歧途,应予以限制。
2.伴奏的关注较少,除了艺术上的简化让弦师失去了表演机会,曲艺的评奖机制、学术研究等也未把曲艺伴奏和弦师人群重视起来。评选机制中大到国家级、小到地市级,对曲本创作、唱腔设计、主要演员均有奖励,而对伴奏弦师、舞美设计等均未设立奖励措施,忽视了包括弦师在内对作品的劳动付出、对艺术的贡献价值;在笔者所撰《曲艺伴奏艺术研究综述》中,对7部曲艺代表性理论专著进行了梳理,平均二三百页的论著有关于曲艺伴奏和曲艺弦师的篇幅最少的只有1页半,最多的也只有不到10页,学术研究的不足由此可见一斑。
3.弦师的地位不高。正因上述原因,很多身怀绝技的弦师被逐渐边缘化,由此淡出了观众、评审、学者的视野。笔者在数场展演结束后发现舞台上神采奕奕的弦师快速地收拾好乐器从鲜花簇拥的演员身后离开,虽然他们早已习惯,但笔者看着却是五味杂陈。在与京津几位弦师交流中发现,他们对曲种的认识、对旋律的识别、对音律的把握有着惊人的把控力,作为旁观者,他们观察到了曲艺圈儿内的各种现象,见证了曲艺发展的各个阶段;作为参与者,他们熟透了曲种的艺术特点,总结了不同演员的表演习性。因此,笔者认为,失去了弦师,曲艺的发展是不完整的,忽略了弦师,曲艺的艺术是不健全的。
(二)人才培养的需要
比起演员和培养,弦师的培养相对周期较长,教学所需成本也较高,再加之市场分成、名利瓜分等多方面因素,使得弦师的培养呈现成长慢、周期长、人数少、收入薄的困难。
面对器乐学习周期长、成长慢的问题,一是进行曲艺专业院校的订单式培养,招取一定数量的有器乐演奏基础的曲艺表演人才或仅有器乐演奏基础的演奏人才进行人才孵化,根据曲艺伴奏的特点有针对性培养,毕业后可送入各地曲艺团工作;二是在音乐类专业院校里开设曲艺伴奏课程,从原本是器乐专业的学生中选拔一批能够胜任曲艺伴奏的人才加以调整并在毕业后输送给相关表演和教学单位。
面对人数少和收入薄的问题,一是从政策上完善对曲艺全部参演主体的“一视同仁”,鼓励弦师的艺术贡献,设立属于弦师的奖项,还可以打造一批优秀的弦师中的“角儿”,从宏观上提高曲艺伴奏的地位。另一方面,曲艺演员也要认可弦师的艺术创造,尊重其在舞台上的劳动,以发展曲艺的高度和境界团结起来,共同推动曲艺的传承和传播。
总之,曲艺艺术绝不能忽视曲艺伴奏,更不能淡化曲艺弦师,反而要完善研究领域,提升弦师地位,加速人才培养,如此才能扩大弦师队伍,传承伴奏技艺,填补研究空白。
参考文献:
[1]于林青:《曲艺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
[2]栾桂娟:《中国曲艺与曲艺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
[3]吴文科:《中国曲艺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
[4]姜昆、戴宏森:《中国曲艺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5]冯光钰、李明正、周来达:《曲艺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年。
[6]于会泳:《曲艺音乐概论》,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6月。
[7]中国曲艺家协会、辽宁科技大学组织编写:《中国曲艺艺术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3月。
(作者:南昌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陈琪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