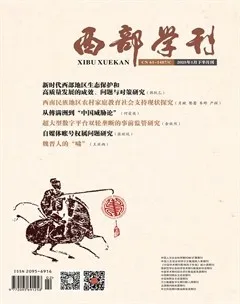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研究
摘要:随着犯罪结构的变化,我国进入轻罪时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决定》提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轻罪治理的司法实践提供方向和要求。被遗忘权是保护犯罪人回归社会的重要权利,以此切入来更清晰地研究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通过界定轻微犯罪的法定刑形式标准,明确犯罪记录封存范围。由于现存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存在“被遗忘权”与其他权利冲突、对象局限于未成年、查询主体泛化和前科报告制度、行业禁止制度阻碍的问题,提出协调“被遗忘权”与其他权利、明确封存适用条件、衔接其他相关制度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轻微犯罪;被遗忘权;封存对象;制度衔接
中图分类号:D925.2;D9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5)02-0111-04
On the System of Sealing Minor Criminal Records
—With the Focus on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Tang Wenjing
(School of Law,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710100)
Abstract: With the change of criminal structure, China has entered the era of minor crimes. The Deci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to Advance Chinese Modernization, adopted a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propo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ystem for sealing minor criminal records, providing direction and requirements for the judicial practice in the governance of minor crimes.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s essential in protecting the reintegration of criminals into society. And this paper, taking it as the focus, conducts a more detailed study on the sealing of minor criminal records, and defines the statutory punishment criteria for minor crimes by clarifying their scope. The existing system for sealing criminal records faces conflicts between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nd other rights, is limited to minors, has issues with the broad scope of inquiry subjects, and is hindered by the criminal record reporting system and industry prohibition systems. In this context,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coordinate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with others, clarify the conditions for sealing, and integrate with other relevant systems.
Keywords: minor crime;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sealed object;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实践逐渐呈现出一种积极化扩张趋势,刑法修正案扩大打击轻微罪的范围,以危险驾驶罪、高空抛物罪和妨害安全驾驶罪为其中代表。为降低犯罪标签的负面影响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问世,但仅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而未成年人犯罪占比较小,80%为成年人犯罪。故此,有必要通过研究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司法现状,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一、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概述
(一)轻微案件的标准界定
1.实质标准说与形式标准说
在轻微案件中以犯罪行为的损害结果或法律规定的责任轻重作为区分实质标准说和形式标准说的依据。形式标准说是指在轻微案件中仅以法律明文规定的量刑处罚轻重为判断依据。实质标准说是指在轻微案件中以犯罪人的主观恶意及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标准界定,其实际弊端在于主要从犯罪人的主观层面出发,司法实务中具有较难的可操作性,并缺乏相应客观标准,使之丧失了界定是否属于轻微罪行的应有之义。
2.法定刑与宣告刑
形式标准说又分为法定刑和宣告刑两种。其中,法定刑是指法律明文规定的具体刑罚种类和期限,而宣告刑是指人民法院根据个案具体情况,以刑事审判的方式最终确定的刑罚种类和期限。法定刑合理之处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在刑事立法时就已经确定轻罪和重罪的标准,不受后期行为人主观恶意和损害结果的影响,具有确定性;第二,轻罪和重罪的标准与刑罚措施相适应,符合罪罚相适应原则,具有合理性;第三,参考美国、意大利等域外规定,都以法定刑为区分轻罪和重罪的依据,具有科学性。
(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被遗忘权”的基本概念
1.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内涵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作为犯罪记录制度中的一种,是指犯罪人所实施的犯罪过程中的全部信息被予以封存,当且仅当符合法律规定,合法的司法机关才能查询。当今社会犯罪结构已经发生变化,重罪案件减少,轻微罪逐年增多,犯罪人因为曾经犯罪的事实被贴上“犯罪标签”,产生不利的犯罪附随后果并且影响再犯可能,最终不能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难以实现治罪与治理相结合[1]。
2.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前科消灭制度之厘清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前科消灭制度极易产生混淆,原因在于两者皆是对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和预防犯罪的应对之策,但是两者并不是同一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从制度概念出发: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针对犯罪人犯罪行为和受到刑事处罚的一种保密封存,允许在合法条件下查询,保护犯罪人的“被遗忘权”;前科消灭制度则是删除、消灭犯罪人的犯罪记录。第二,从制度目的出发: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犯罪人,通过严格的法定程序限制或禁止查询;前科消灭制度的目的在于对犯罪人进行评价,这种评价包括法律评价和非法律评价[2]。
3.刑事司法领域“被遗忘权”的含义
“被遗忘权”产生于法国,以帮助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为目的。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被遗忘权”主要从权利主体、义务主体、权利客体三个方面展开[3]。权利主体是指请求被遗忘信息的主体,在犯罪记录封存中局限于犯罪主体;义务主体是指犯罪信息的控制者,主要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局以及保存相关犯罪信息的国家行政机关,权利客体是指具有公开性的犯罪记录。
二、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必要性
1.相较于犯罪记录制度
目前,我国《刑法》针对犯罪记录的法律规定尚不明确,只在第六十五条、六十六条出现了一般累犯和特殊累犯的规定,对此可从重处罚,体现了我国现有的犯罪记录。犯罪记录制度具有永久性、消极性和人身性,是犯罪人被执行刑罚期间以及结束之后,将会伴随犯罪人一生的一种社会“标签”,并且后期难以通过其他方式予以抹除,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可以避免犯罪记录制度产生不当的犯罪附随后果,促进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
2.相较于前科消灭制度
前科消灭制度是指犯罪人在满足法定条件时,由国家机关予以抹除之前的犯罪记录[4],使罪犯更好地回归社会,恢复合法权利的刑事司法制度。首先,是否消灭犯罪人犯罪信息集中反映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问题。前科消灭制度以抹除犯罪人犯罪信息为目的,将个人利益放置于社会利益之上,不利于公众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信息的知情权。与前科消灭相比,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可以有效降低犯罪风险。既可以减少犯罪信息的传播、保护罪犯的利益,也可以保障公众知情权、维护公共安全、降低对公众造成刑事伤害的风险。再者,不利于对犯罪人造成震慑力,并且与公开透明、正义真实的法律精神相悖。最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产生的衍生问题较少,由于我国已有未成年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存在,可为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提供参照标准。
(二)可行性
1.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经验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有关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正式出台,至今已有12年之久。
2.域外犯罪记录封存的借鉴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英美法系司法实践中已有较为完善的体系,为我国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提供经验。例如,1974年英国颁布的《前科消灭法》和《犯罪自新法令》,规定当犯罪行为人年满18周岁后自动消灭其犯罪记录,不需要其他任何附加条件。美国的马萨诸塞州针对成年人犯罪记录也可以封存,但除性犯罪和严重的暴力犯罪外。俄罗斯对此设置考察期,在刑罚期限届满起8年内可以申请封存,成年人如果在考验期间内表现良好,法院也可依职权在法定期限到期之前撤销前科。德国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采用先封存、后消除的制度模式,最终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必须由法院同意后两年内或免予处罚后销毁。
三、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现实困境
(一)犯罪人“被遗忘权”与知情权冲突
被遗忘权属于一项自然人的私权利,在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中犯罪人就有被遗忘权。但是被遗忘权也与公众知情权和公共安全相冲突,公众知情权要求有关主体履行公开信息的义务,而被遗忘权要求将犯罪人的犯罪信息“隐藏”。被遗忘权和公众知情权两个权利相博弈产生的矛盾是当前尚未建立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重要原因,因此如何权衡和协调两个权利尤为重要。
(二)现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具有局限性
1.适用对象局限于未成年人
如前文所述,我国现有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对象只针对未成年人的轻罪案件,并未包含成年人。但随着轻微案件的增多和轻罪治理的提出,如何实现治罪与治理相结合就变得极为重要[5]。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目的在于对犯罪人的犯罪信息经过合法合理的手段予以保密,不单是未成年人所享有的特权,符合封存条件的成年人也可以依申请或依职权进行封存,达到“去犯罪标签”的目的,促进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降低再犯罪可能性。
2.查询主体泛化
我国关于犯罪记录查询的主体散见于各种部门规章、行政法规和法律之中,高达165份,其中涉及资格禁止的规范合计152个,占比约为92%;而涉及法律责任从严认定的规范仅有14个,占比约为8%[6]。由此可知,关于犯罪记录查询主体过于泛化,直接影响到犯罪人从军、求学、就业,不利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行。
3.缺失责任追究与救济机制
一套成熟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主要从适用范围、适用主体、适用条件、责任追究和权利救济等方面逐一详细规定,但我国现有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针对责任追究和权利救济两方面空白化。其中《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主要明确了信息提供者、管理者和使用者三方主体的违规行为,但未对违规后所承担的法律后果、救济途径进行规定;《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中明确未成年人及法定代理人可在权利受到侵犯时向人民检察院申诉,但也未明确申诉程序。
(三)相关刑事制度的阻碍
1.前科报告制度
我国《刑法》第一百条《刑法》第一百条: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
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明确规定了犯罪人前科报告义务,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可以进行封存保护,但是由于适用主体局限,并不包括成年人,使得成年人在入伍和就业的过程中因犯罪的“标签效力”受到限制。由此可知所有不满足封存条件的犯罪人具有终身永久的前科报告义务,但是各种类型的犯罪由于社会危害性不同,承担刑事责任也不尽相同。
2.行业禁止制度
我国的《律师法》《公务员法》《公司法》和《法官法》等法律中都规定了有关从事上述特定职业的人员不得有犯罪记录,因为对于特定领域、特定职业的人员相应的品质要求更高。在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过程中,上述有关行业禁止的相关内容也应该予以协调。
四、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构建路径
(一)协调“被遗忘权”与知情权
当前网络环境下,具有较高的空间高度开放度,个人生活空间和状态的开放化成为常态,公域与私域在虚实交融中走向了一体化[7]。权衡被遗忘权与公众知情权的本质在于犯罪人所犯罪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程度是否可以优先保护被遗忘权。如果犯罪人只是轻微犯罪,并未造成严重的、不可修复的后果,则可以对犯罪信息予以封存;相反,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严重损害的,公众对犯罪人的犯罪信息具有知情权。被遗忘权属于相对保护主义,根据《宪法》第五十一条可知公民在行使宪法的基本权利不得损害国家、公共、社会利益,此时个人权利受到相对保护。
(二)明确封存适用条件
1.主体扩张至成年人
由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局限于封存主体为未成年人已经逐渐不适应当前变化的刑事犯罪结构,故应将主体扩大至成年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成年人都可以将犯罪记录封存。在刑罚上应该满足法定刑不得高于3年的犯罪人,同时犯罪类型应当排除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黑社会性质、性犯罪等,最后对于累犯、再犯、惯犯不具有悔意的犯罪人的犯罪记录也不应当予以封存。
2.限制犯罪记录的查询主体
针对犯罪记录查询主体,我国法律规定司法机关和其他有关单位可以查询。其中,“司法机关”指公、检、法三家,而“其他有关单位”较为模糊,呈现出查询主体泛化。对此,应该从两方面进行限制:第一,局限于国家安全部门、外交部门、纪检部门和监察部门;第二,单位政审部门、政治部、人事处和人社局,这类部门不影响犯罪人再就业,而影响犯罪人担任特殊职务。此外的其他单位或部门都不可对此进行查询,助力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运行[8]。
3.建立责任追究与救济机制
在责任追究层面,可以从民事、行政、刑事三方面出发。美国和日本将犯罪记录视为犯罪人一项特殊的隐私权,满足隐私权的非公开性、秘密性的特征,可通过民事赔偿的方式追究相关负责人恶意泄露犯罪人已被封存犯罪信息的行为。根据《保密法》的相关规定,若国家行政机关未合理行使职权造成已封存的犯罪记录泄露的,可以申请国家赔偿。而对于通过非法手段恶意纰漏被封存犯罪记录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按照滥用职权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三)衔接其他相关制度
1.免除前科报告义务
前文所提及的我国《刑法》第一百条第二款规定免除犯罪人前科报告义务可以进行条文修改,建议改为“犯罪记录已封存的,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这样不但可以攻克现有前科报告制度的问题,还能与成年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相协调,化解两个制度的冲突问题。
2.明确行业禁止的适用条件
特殊行业需要严格的职业道德,而犯罪记录就是衡量职业道德的一种标准,律师、公务员和法官都要求具备。但是一般行业可不与上述行业一样严格要求,在满足刑罚惩罚与教育目的后,可以使犯罪人重新回归,在各自领域内平等就业。故此,可明确行业禁止的适用条件:第一,禁止进入的行业与犯罪性质相关;第二,行业禁止的期间必须坚持比例原则;第三,由法律、行政法规作出强制性规定。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犯罪人都可以重新回归相关领域,将行业禁止与犯罪记录封存有效结合。
五、结束语
被遗忘权不仅只是保护个人信息安全,还在于加快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轻罪治理的时代贯彻治罪与治理相结合尤为重要。本文以被遗忘权为切入点,为研究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提供新视域,分析司法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参考域外相关制度,提出具有可行性实践对策,但在实践中可能还会存在其他问题,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朱聚红,苏丽萍,吴柳青.轻罪惩治视角下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构建[J].人民检察,2024(增刊1):43-45.
[2]贾红超.我国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构建研究[D].青岛:青岛大学,2023.
[3]聂云霞,殷名.平衡理论视域下数字档案用户被遗忘权的行使与限度[J].档案学研究,2024(3):54-63.
[4]李勇,曹艳晓.中国式微罪记录封存制度之构建[J].中国检察官,2023(7):31-34.
[5]曹化,张建伟,吴宏耀,等.轻罪治理现代化的检察制度构建[J].中国刑事司法,2024(4):98-108.
[6]于志刚.犯罪记录制度的体系化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9(3):62-84,205-206.
[7]苗梅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中被遗忘权的制度性嵌入[J].中外法学,2023(6):1600-1615.
[8]夏朗.论轻罪时代的前科淡化:对犯罪信息获知途径的限缩[J].政法论坛,2023(5):50-62.
作者简介:唐文静(1999—),女,汉族,陕西渭南人,单位为西安财经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为诉讼法学。
(责任编辑:赵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