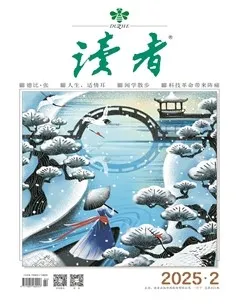人生,适情耳

我与“坡仙”(1037—1101)同为蜀人,自幼便听过无数关于他的逸闻趣事。但我印象最深的却是那两句诗——“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多么古怪的祝福啊,一个父亲竟然希望自己的儿子是个笨蛋。于是我想,这个人一定曾为自己的聪明付出过极为惨痛的代价。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苏轼活着的时候已经是北宋最大的IP(指可供多维度开发的文化产业产品——编者注)。
年少及第,20岁被录为省试第二名,24岁高中制科第三等,很快便取代其恩师欧阳修,成为新一代文坛领袖。起点之高,声名之盛,粉丝之众,堪称“第一国民偶像”。然而,登高必跌重。42岁那年,苏轼陷入党争旋涡,连遭弹劾,过去十年间的诗文也被作为弹劾材料上呈御览,罪名是对神宗皇帝不敬和讥讽新法,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显然,这是一次针对苏轼的文字狱和政治迫害事件。苏轼自八月十八日下狱,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狱,历经整整130天,他甚至写好了绝命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将阖家十余口托付给其弟苏辙,随时准备引颈就戮。
幸而有宋一代不杀文官,苏轼旋即被贬黄州,身份尴尬,生活困顿。有趣的是,物质上的贫瘠反而激发出苏轼精神上的丰沛,正是从黄州生涯开始,他摇身而成“东坡居士”,由是开启了他的“斜杠人生”——不再单单是封建王朝的士大夫、散文家、书法家和诗人,还“斜杠化”为月夜的漫步者、灯下的赏花人、吟啸徐行的半仙、词作者、酿酒者、美食家、农夫、道士、参禅者、旅居者、注疏者、经学家和哲学家……
以黄州为分水岭,苏轼仿佛经历了一次全面的进化,更新了他的“出厂设置”,拥有了两个“频道”——在朝为官时,他自觉成为经世致用、勤政爱民的儒者,一名优秀的公务员;而一旦被贬,他便迅速切换到“聊从造物游”的境界,自在得如同还林之鸟。就连一向与他亲厚的苏辙也不得不承认,从前自己的文学水平尚可与兄长并驾齐驱,黄州之后,就只能眼睁睁望着兄长一骑绝尘而去了。对此,我只想对苏辙说:“你说得对。因为他打破了次元壁,你还没有。”的确,在直面了将死的绝望和贬谪的困窘之后,苏东坡完完全全地,打开了自己的生命。
尽管很少为人所提及,苏轼的的确确是一位哲学家。他是北宋蜀学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与程颢、程颐所创的程学分庭抗礼。世人铭记他的诗文、策论乃至绘画、书法,苏轼却说,每每回首往昔,唯有当抚摸着自己所著的《东坡易传》《东坡书传》和《论语说》这3卷书时,方觉此生不曾虚度。必须指出的是,这3部著作皆动笔于黄州时期。
苏轼哲学的核心概念,乃是“无心”,其中包括3个层次:
首先,无心与有心相对。无心代表的是一种澄澈、天真的状态,有心则指人已受到外物的干扰与遮蔽,故而充满了造作与刻意。对苏轼来说,最理想的无心状态当如“明镜照物”,完全出自无心,才能摒除私心杂念,从而真实敏锐地反映外部世界。
其次,无心意味着精神对感官的统摄。在苏轼看来,君子的修养就在于时时拂去感官的欲望与心智的纷扰,从而进入某种超然于物外的精神境界。
最后,无心意味着个体生命总是能够彻底地与大道合而为一。所谓“君子如水,因物赋形”,苏轼心中的君子不偏执,他们像水一样不拘于固定形态,始终保持圆融与开放,不断与江上清风、山间明月赤诚地相遇,因此也就得以一窥“造物者之无尽藏”的奥义。如果不是有这样的哲学作为其精神内核,苏轼势必无法成为“坡仙”,在其艰险的仕途当中,他当有无数机会死于幽愤、死于内耗、死于忧郁。
南唐后主李煜被囚后,曾作颓丧之词“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将醉酒视为唯一的解脱方式,打定主意沉溺于愤懑与悲感之中,当然也不出意外地死于这种愤懑与悲感。100年后,坡仙化用其诗句,写道“醉乡路稳不妨行,但人生,要适情耳”,一扫衰颓,将醉生梦死翻出一重崭新境界。
何为“适情”?
就是顺势应情,而其前提则是把“道”看得异常开阔:
仁者爱人是道,至情至性也是道;修身养性是道,饥餐倦眠也是道;指点江山是道,月下观花也是道;匡扶正义是道,将一块猪肉炖得很入味也是道。如此适情,方能在世界无情地向你碾压过来的时候,保持平衡,维护自洽的内心,放自己一马,同时也放世界一马。
作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苏轼的哲学难以传世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在他死后一年,蔡京就下令销毁了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及其门人的文集,并禁止传阅、流通和刊印。
但更重要的是,苏轼那“随物感应”“道无常则”“尽个性”的多元人性论调,对于封建王朝的统治者而言,终究还是太超前了。当然,对于我们现代人就刚刚好。
长大后,我特意查过前文《洗儿诗》中被祝福的那个孩子。他叫苏遁,为苏轼幼子,由其最心爱的侍妾朝云所生。他甚至没有机会成为他父亲所期许的那样一个笨蛋,他夭折于旅途,在世上只存活了10个月。
当然,苏轼为之恸哭、垂泪、哀悼和叹息,但他不仅是悲伤的父亲,还是谙熟农事的耕种者,是拄杖听涛的归人,是独自登山的行者,是百姓的朋友,是好客的隐士,他所拥有的生活世界裹住了他。所有那些“斜杠”,撑住了他。
这难道不朋克吗?我甚至感到,坡仙的人生,在“朋克”这个词诞生之前,就定义了朋克呢。
(田安摘自《少年新知》2024年第11期,肖文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