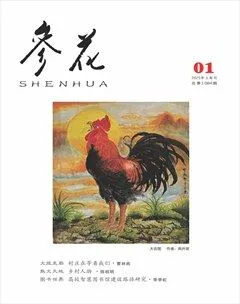喊夜
一
鸡狗入窝人上炕。十七岁那年刚离开学校,我住在一间柴房改造的偏房里。寒屋冷床凉被窝,冬天的风侵扰着朽门漏窗,我蜷缩在被窝里慢慢用体温熥凉窝,似冰洞里的螃蟹久久不敢伸开双腿,依靠美好的幻想默默进入梦乡。那一晚,惊醒我的是一阵阵嘈杂声。
先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引来了家狗的狂吠,紧随的是鸡鸭鹅的合唱,然后父亲和我一前一后警觉地蹿向大门口。拉开门闩,只见门口站着惊慌失措的三伯。我听到他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你爷俩都和我找驴去,驴没了!”
三伯是村子里的干部,退休后放着富足的日子不享,偏又置办犁锄耧耙种大田。一头黑毛溜光的草驴是他刚花了六百元买的。六百元,当时能娶一房媳妇。因为父亲常用一句话刺激我:“念不好书飞不出土窝窝,你就老老实实地给我挣够娶媳妇的钱。”六百元啊!看着三伯着急忙慌地又跑去喊下一个本家去找驴,于是,我和父亲就穿上紧实衣服摸黑往三伯家赶。
三伯家住村子东南角,东、西、南三面没有邻居。东面是长满树木苇草的河沟,南面一片杨树林,西边一片撂荒地。父亲边走边唠叨,三哥的宅子最易招贼。
进得三伯的红砖门楼,院里屋内已聚了不少人,都是本家族人和邻居。有叔辈的,有兄弟辈的,数我年龄小。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猜测驴跑哪去了,是不是被贼牵走了。
三伯嘴唇颤抖着,坐不住,站不稳,驴俨然是他的心肝肺,尽管他家日子过得比在场的任何人都好。还是急性子的父亲开了口:“大家就别闷葫芦了,赶紧分头找吧。俩人一帮,分开找,有去东的,有去西的,有去宰房的……”
“大黑夜伸手不见五指怎么找?和驴走个迎面它不叫也认不出,得有手电筒。”大斗哥开了腔。
手电筒本是贵重家用电器,当时一半以上人家是没有的。青年人手握手电筒就有在女青年面前抬高身价的资本。在这关键时刻三伯不敢小气,他一声不吭麻利地跑进屋,手抓一沓钞票逐一发放,一组十元。
年轻的分了三组,每组两人,年龄偏大的三人一组负责在村子及附近寻找。约莫两个钟头都回家一趟,凑凑情况,防止驴找到了不知道信息的人还在瞎找。我和大斗哥分在一组,负责向北出发。
我俩终于在邻村大街尾临街房看到一户亮灯的,是一户经销店,店房门早已关闭,只有像是卧室的窗亮着灯。大斗哥把我摁到他身后,他悄悄凑到窗帘没扯严实的窗户边观察情况。两分钟,五分钟,大斗哥仔细地探望着。灯光里我看到他饱满的狸猫眼珠子即将蹦出狭窄的眼眶,厚厚的嘴唇像吃鸡又没吃到一样咧开着,嘴角的涎水淌到两腮。以前我见到他跟叫他外号的东良打过架,就因为东良叫了他一声“棉裤腰”。后来我才打听到,“棉裤腰”是指他的嘴巴子又厚又松。我自然好奇他看到了什么奇观,便不动声色地附在他脑袋旁。
敲开店门,胖胖的女店主一头乱发斜披棉袄,眼皮还没眨,话就已经甩到了大斗哥的脸上:“大半夜的不让人睡觉,死人了?”
五元钱买了手电筒,两元钱买了四盒“金鱼”烟,一毛钱买了四个糖块。剩下的钱及烟便装进了大斗哥的裤口袋。糖块是用来堵我嘴的。
寒风吹着锅底一样黑的夜,路,坑坑洼洼。大斗哥一根接一根抽着烟,烟头的红点是我跟随的方向。偶尔一个趔趄便会招来大斗哥的训斥,“你抢啥宝?甭那么上心了,三伯有的是钱,驴找到找不到关咱屁事,有钱也没见他分咱点。谁让他贱,种啥狗屁地?别累着咱就行,你看这又黑又冷的……”
寻到北王庄北麦田里,大斗哥突然随一声怪叫扑倒下去。我愣神间,大斗哥慢慢爬起来,摁亮手电照着身边,一张巨大的网罩住了他。大斗哥不但没生气反而狰狞地哼笑道:“好,好,看我下半夜怎么收拾他们。”原来这是城郊人来围猎野兔下的网,下半夜才能收网。“这是我家麦田,你们践踏了麦田,看怎么赔偿吧。要不就报派出所,最好叫咱福全小叔来,他是协警。他们会乖乖地奉送几只野兔。不行,还得要上五十元钱。”大斗哥絮叨着。虽没了烟头,我也能猜到此时他嘴角上扬,双目放光。
驴蒙眼撞上瞎眼碰,寻寻觅觅了个把钟头连根驴毛也没找到。马上就到镇街上了,大斗哥喊住了我,“小四,咱别急头蒙腚地找驴了,我跟你说个事,你饿不,冷不?大秀家的小吃部就在镇街上,咱咋不去找吃的?”
我肚子接连回应似的“咕噜”了几声,可找驴是正事,哪有闲心讨吃的。大秀是三伯家的大闺女,女婿在油田打油井,一走两三个月。大秀独自在镇街上经营小吃部。我没吭声,大斗哥接着说:“不吃白不吃,不因这个事,人家还能看得见咱?几次赶集在她饭店门口碰面,人家都装没看见。”
二
黑夜里的镇街上只有尾巴扫地的饿狗和为生计而奔忙的鼠辈,连个驴的影子都没有。大斗哥心思早已不在驴上了。我只能紧随他的身影。即将到饭店时,我看到街东头迎面有手电光一闪一闪的。“小四,把手电灭掉,看看前面是哪路贼人?”
我俩蹲在墙根,等那亮光走近时,大斗哥听到来人咳嗽声就立马站到街中心,举起手电筒像对暗号一样上下左右在晃。“二斗,快过来吧,是自己人。”
二斗哥身后是大我两岁的二伯家的长命哥。双方一碰面,几双嘴巴子就开张了。“冻死了!”“饿死了!”“累死了!”二斗哥话更多:“三叔家最富,他日子好也没帮过咱们。叫咱们给他卖命找驴,这不是拿穷人开心吗?”二斗哥的嘴唇要比“棉裤腰”薄一点。大斗哥凑近他们嘀咕了一阵,几个人像是很开心的样子。于是,我们一拨人迎着寒风冲着小吃部赶去。
大秀姐慌慌张张开了门,把娘家人让进店内。灯光下一惊一乍问着事由。迎着灯光,大秀姐垂着一头秀发的脸庞竟化着艳妆红唇。不种田的女人睡觉也上妆?我想。大斗二斗争先恐后翻动着厚唇搅动着舌簧,努力诉说着寒夜里费尽心力地找驴,一通忍饥挨饿受冻的演讲终于引导大秀姐恍然大悟:“抓紧做饭。”一句脆生的话语伴着大秀姐转身去向厨房,两位哥哥转向我们时都露出了得意的笑。我虽然没把笑露在脸上,心里也在笑。其余的人可能也是。
大秀姐直接上了一大盆鸡肉炖土豆,二斗哥抄起勺子就抢。大斗哥捣了他一拳,声音压得很低:“不要瓶酒解解乏?”二斗哥心领神会,直接去柜台里选了瓶二锅头。
大家都在埋头往嘴里“运货”。我和大斗哥坐在朝向店内厨房与卧室走廊的一面,吃得正酣时,我见大秀姐悄悄地去走廊尽头的窗户前摆弄着什么,然后进了卧室。一个紧裹呢子大衣的男人蹑手蹑脚走向那窗前,我确定他不是姐夫。我用手肘碰了碰大斗哥,用眼光示意他向那边看,他瞪大了眼但没有声张。随后一股寒风从西窗口飘然而至,大秀姐镇静地迎风踱去关窗……
二斗哥说:“各位兄弟,吃了妹妹的饭咱更得打起精神使劲找驴,抓紧出发。还有,秀儿,一人给拿一包烟抽吧,黑灯瞎火的,壮壮胆。”
我紧挨着二斗哥后背,刚要说出“我不会抽烟”,话没说完整就被二斗哥倒钩腿踢了一下。他是在提醒我,不会也要领烟,大秀姐一定得按人头发。
镇街东头,一户院子里亮着灯光。我们两拨人还没有分开,二斗哥要走了我那盒烟的同时,长命哥说,亮灯的院子是乡大集上唯一的宰房。我们闷住饱嗝响屁,迂回到宰房周围,寻找合适的地方观望。最后,几颗脑袋聚集在了旧墙上端的豁口处,屏息观望。我们果然看到一头死驴躺在血水溢流的院子里,几个人持刀拿斧忙活,一个妇女在往驴嘴里灌水。黑驴,和三伯家的一个颜色。人人提高了警惕,边观望边思考。杀驴人有说有笑并不避讳。到底是偷的还是从贼人手里买的?我们一时难下定论。
这时,不知谁弄出了声响,紧接着院子角落里蹿出一条大黑狗,冲围墙狂吠而来。在逃窜中,大斗哥告诉我,那是头病死的驴。
三
夜半时分,几帮找驴的人陆续回到三伯灯火通明的院中。院子里没扯电灯干脆挂上了两盏纸灯笼。我俩可能是最后进院子的,三伯、三娘和父辈们用急切盼望的面部表情迎接着我俩,大斗哥用无奈的表情回答了三伯、三娘。
饭棚里大铁锅灶口的柴火烧得噼噼啪啪,炉火正旺。火光映红了三娘焦急的脸庞。我正想多嘴,忽然想起了之前的约定:谁也别在三娘跟前说我们去小吃部吃饭的事。
缭绕的热气裹挟着三娘端来的一大盆煮挂面、两小盆煮鸡蛋,三伯拿出了两瓶白干。饿狼般的小辈们蜂拥而上,一年也吃不上几回的白面和鸡蛋早已诱惑得大家嘴角垂涎、肚子争鸣,除了胃里忙着消化的我们几个。我们虽心里不急但表情要急,再饱也要意思意思。大斗哥干脆抄起半盆鸡蛋悄悄地进了里屋。我端着碗稀面汤跟随大斗哥进了里屋。里屋背人处大斗哥正鬼鬼祟祟地往怀里揣鸡蛋。
三伯展现出当年的精气神,焦灼的眼睛透出警觉与企盼。三娘忙得面红心发乱,使劲地劝大伙儿吃饱吃好。父亲一口没吃,将烟头吸得旺旺的,急等大伙儿吃完饭再上路寻找。还没等人们擦落嘴角及胡须上的蛋渣面沫,他便急不可耐地扔掉烟头立身于屋中央,“这回重新分组出发,换人换思路,仔细寻找。”
出了屋门时,二斗哥又扭转身子开了腔,“是不是得给每人拿上盒烟啊?一是抽烟壮胆,二是托着红烟头浑身暖和。”
三伯家里已没有烟,便慷慨地给每人发了两元钱。其实这个时辰有钱也买不到烟,但装上这两元钱,大伙儿心里比抽烟还踏实,人也更精神。刚出院门,大斗哥就唧唧着要先回家换棉鞋。
北风嗖嗖吹,没走多远风就把人身上的热气吹个精光。这回我和小叔福全分在了一组。小叔四十出头,是我们家族唯一穿警服的人,乡派出所的协警。他指挥我向西洼麦田地搜寻。麦田里大片麦青,说不定脱了绳的驴会去啃青。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行在冬夜里,夜幕下偶尔传来猫头鹰的咕咕声和发情夜猫的嘶鸣声。
踏进软绵绵的冬麦田地,我紧随小叔身后,先横向搜寻,走完一个方块田再纵向寻找。手电筒的照射范围也就几十平方米。我俩来来回回一无所获。小叔停住了脚步,沉思一会儿说:“咱俩这样像湾中取鱼,效果不好。三哥养的是草驴吧,咱不妨换个思路,学公驴叫,也许会有效果。”
“哦——哦,哦哧——哦,哦——”小叔竟然学着驴叫,向着夜空尖厉地吼。吼叫间隙他又动员我也学驴叫,我笨拙地学了几声,居然像挨了刀子的猪在哀号,小叔笑得岔了气,然后让我模仿他,跟他一起喊叫……直叫得嗓子干痒了,小叔才死心塌地地继续搜寻。我俩向西走了三四里,小叔突然停止了脚步:“有情况。”我顺着光望去,朦胧的夜色中,几十米开外一大型动物正扬起头望着手电光。是驴头,不假。我们两个悄悄围拢过去。手电光下细端详,是驴,且它与三伯家的驴一般也是黑色。但是驴头上一条长长的缰绳在黑暗中伸向远方。
喊声把令人恐怖的夜色震碎了,人的胆子也壮了。爷俩顺绳摸贼走出十几米,却摸到了拴绳的铁橛子。贼呢?吓跑了?我俩继续向西搜寻,快到小河坝时,听到坝下有动静。小叔用手电照过去,我们迅速上前看到几个口袋,其中一个口袋露出了一个男人的上半身。黑黑的脸庞,蓬乱的头发遮掩着他的大眼睛。原来他钻口袋是为了御寒。两个没有动静的袋子里露出了麦青。“真不简单,牲口啃青,再偷割麦苗回家贮存。”小叔单脚踩住了贼,手电光照在贼人脸部。“你先把我放出来。”贼说。
钻出口袋的贼一米八的个子。殊不知贼人刚钻出口袋就来了个饿虎扑食,抱起小叔就猛地一起摔倒在地。两人打作一团,连滚带爬。黑夜里我也认不清谁是谁,也无从下手帮忙。缠斗了好一阵,我听到贼“嗷嗷”的哀叫声,好像小叔抓到了他的要害,使他跪地求饶。
小叔喊我取过缰绳,我俩一起把贼捆了个四马攒蹄。小叔让贼看看自己身上的制服,亮明身份后,开始现场审问。在贼人眼中,我应该也是一名警察,起码是一名联防队员。
警察面前,贼吓得全线破防,事情也渐渐清晰了。正在啃青的不是驴,是一头骡子。怪不得我们学驴叫,它不回应。骡子也不是这个叫罗汉的男子的骡子,而是他村中叫红菱的寡妇的。寡妇的骡子出租给没有牲口的种田人家,由罗汉和其他几个村民轮流饲养。小叔随身带着笔记本,做完笔录后,说:“小四,你给他松绑吧。”
四
冷风裹着霜冻,我俩迂回到来时的路继续寻找。我紧盯着小叔门板似的后背,寻思刚才发生的事情。不远处一团团黑影映入眼帘,小叔说这是一片坟地,农人们依附坟头又垛起了一堆堆的玉米秸秆。我下意识地不停挠头。同学们说过,见到坟头就用手挠头。
小叔停下脚步,抱过一堆玉米秸秆点燃,脱下打斗时湿了的棉鞋放在火旁烤干。我贴近夜火,张开双臂拥抱温暖。爷俩边烤火边聊。聊生活,聊人生打算,当然也聊三伯的驴。火燎得我正温暖时,小叔的对讲机响了起来。一阵对讲过后,小叔说:“我还有重要事情,小四,委屈你自己回去汇报吧。”
我突然感到异常恐惧,一时没有回答他。小叔看出我的担忧,略含微笑爽朗地说,“别怕呀,小四,给你手电筒。害怕了,你就边走边喊,喊累了就唱!”
闯吧!我闯进阴森的冬夜,夜幕下,冷汗渐渐打湿了我的脊背,我陡然忆起小叔的话语,别无选择地唱起来,先浅润喉咙哼,再张开嘴巴浅唱,最后大声喊大声唱……
“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一声声高亢的亦喊亦唱的声音与夜幕搏斗着,恐惧被喊叫声震得粉碎。不知不觉间我又一次望见了三伯家院落的亮光……
堂屋内众人围着饭桌。饭桌上有猪蹄子、鸡爪子、烧鸡等。凑不到饭桌前的人参差不齐地挤站着,动作挺规律的,一只手或双手抓牢食物与嘴巴不住地“亲密着”。这是何等奢侈的食物,夜半三更从何而来?莫非草驴找到了?
三娘眨着通宵没睡的双眼,走上前心痛地拉住了我的手,一边往炉火旁走,一边絮叨,“看把孩子冻成冰坨坨了,找不到驴也不能把孩子冻坏了!”三伯双目露出红血丝,平常精打细算的性情此时也被抛到了屋顶上,只顾劝吃劝喝劝拿出找驴之战术。
待我吐出最后一块鸡骨感觉再也吃不下时,大斗哥将我喊出了屋门。在厢房前的苦楝树下,他说:“小四,你去把你大秀姐叫过来,有点事。”我有点蒙:“我咋没看到大秀姐呀?”我说。“你只顾吃,她在炕沿里边呢。”
陪同大秀姐来到楝树下的时候,我才明白饭桌上美食的来源。大斗哥笑着谦恭地对大秀姐说:“妹子,真不好意思,有点事求你帮忙。我吧后天给儿子交学杂费,我吧,本打算明天上工地跟工头借五十元钱,你看我一整夜找驴,明天是出不了工了,我想先跟你借五十元救救急!”
大秀姐一准儿也了解大斗哥的为人,思忖着他俩是堂兄妹也就一拃近的族情。大秀姐说:“哎呀,我身上生钱啊?五十元大钱儿多久才能挣出来啊!”眼看一头秀发的背影即将扭进堂屋,大斗哥厉声道:“秀儿,跟你说个重要的事!”
在大秀姐转身的同时,大斗哥快步抄上前去拽住了她的胳膊,一边往树下走,一边又拉住了我一同来到树下,声音压得很低但粗重有力地窃语道:“秀儿,上半夜在你店里吃饭时,我和小四看到一个人从你店里西窗跳了出去!”
大秀姐始终一言不发。过了好长时间,说了一句“你在这等着”,然后像一截木桩一样移向屋内。我顾不得此时阴影中大斗哥的表情,只想我家为什么这么穷,上学时为三十元学费父亲就愁了几天几夜。
大秀姐像憋尿的小媳妇寻茅房一样,焦急但不露窘态地迈着小脚碎步回到树下,把攥着钱的手伸进了大斗哥的口袋,不容置疑且大方地低语:“装好了,日子过得紧就别还了,谁叫咱是一个墩头发芽的呢!”
一夜三顿饭,顿顿比过年吃得都好。我也出现了上打嗝下放屁的生理反应。眼看着长命哥从茅房里露了头,我立马钻进了茅房。正在我用力地排泄时,茅房又闯进了一人——二斗哥。他一看茅坑被占,骂了一句转身离去。
我将又一个等茅坑等得直跺脚的人让进了茅房后,就围着院子逛圈。就在等待屋内的人做出继续找驴还是停下歇息的决定时,我猛然被鬼祟的大斗哥挟持着不由分说地拽到了院外。几米外的墙根下,夜幕更加黑暗与神秘。大斗哥拉着我与早已躲在暗处的二斗哥围成了一个圈。二斗哥声音压得更低沉:“出事了,三叔家的驴找到了。我被你挤出茅房,就憋尿到驴棚撒尿。驴棚里有个黑影,我定睛一看,你猜是啥?驴,三叔家的驴。驴根本没丢,可能是三叔临睡前来探察时,驴卧倒在驴槽后的暗影里打盹儿呢!”
“那可是大喜了,我赶快告诉三伯去。”我说完没等挪步就被大斗哥一把按住了:“你傻啊,这兴师动众折腾了一宿,三叔家花费了半头驴钱,发现驴根本没丢,那可收不了场。赶快想办法,屋里人正打算放弃寻找呢。”
二斗哥上学时成绩就优秀,一袋烟工夫他就计上心来……
五
大斗哥恰似当兵打仗时的指挥官:“大家都去屋里,商量下找驴的对策,一定要找到三叔家这驴。”虽然这话听着有点别扭,但主家三伯一定不会怪罪他,反而会赞赏他这种认真负责坚持到底的精神。大家都萎靡不振地耷拉着眼皮子进了屋。大斗哥堵在门口宣讲,同时也是为防止有人来院子里看到我和二斗哥的小动作。
我尾随二斗哥贴着墙根悄悄地进了驴棚。二斗哥先用预备好的裹脚布捆住了驴的上下嘴唇,怕它叫出声,捡起掉落在地上的缰绳,轻抬脚慢落步悄悄地出了驴棚出了院门。二斗哥在驴前,我在驴后,钻入夜幕下的田野,冲着指定目的地越走越快。驴的脚步也随我俩变得轻盈起来,它迈着碎步,有节奏地颠扭着。也许驴在想:是不是要给它换个吃的住的更好的东家。
过了几条封冻的小河,八条腿驻足在南洼大片麦田里。二斗哥边解驴嘴套边嘟囔:“伙计,你折腾了我们一夜,不怪罪你,这回你敞开大嘴尽情地吃吧。”我本打算蹲下歇息,二斗哥却不允许,“小四,咱们去地头抱些玉米秸来,一会要点火,要喊夜,把大斗哥带领的人马引到这边来。”
夜霜之下,人被寒冷侵袭。守着一堆柴火我忍不住说:“二哥,咱先把火点燃吧。”二斗哥也是人,普通人。他毫不犹豫地掏出打火机把火点燃了。面对腾舞的火焰,我俩高兴得手舞足蹈。
二斗哥黑黑的脸庞被火烤得通红如烙铁。他竟不知羞耻地褪下棉裤冲火焰撒起了尿。边尿边报复性地说道:“驴找到了,不能这么便宜了三叔,折腾一宿明天谁也打不了工,一天就是五元钱啊,得想办法让主家赔偿。”
约莫过了一个小时,到了与大斗哥约定的时间,二斗哥命令我起身喊夜。他想让驴发出比我俩喊声更凄厉的叫声,可怎么打它都不叫,只顾低头啃青。二斗哥就是聪明,他扔掉棍子扯着驴站在火堆旁,驴往回撤步他就戳驴腚,被火烤得滚烫的驴终于扬起前蹄纵声嘶鸣起来,“呃,呃——呃哧——”
嘶鸣声划破长空,这时我看到来时的路上闪着几个亮点,一准儿是大斗哥带人寻来了。我俩牵上驴往来人的方向走去。驴不叫了我俩叫:“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往前走,莫回头……”二斗哥声音更欢畅:“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吔,叭叭地响哎……”
双方相距能辨出人影的距离时,按照约定灭掉手电筒,对暗号。二斗哥双手喇叭状罩在嘴上:“鸡鸡翎,跑麻城。”对面传来大斗哥厚嘴唇发出的悦耳的喊声:
“麻城开,芝麻秸。
干草垛,麻火烧;
你那人马任我挑。
……”
双方人马会师后,又喧响起欢乐的喊叫,一众人包括驴在内皆大欢喜。驴才不管人间事,吃了青苗美食才是它最要紧的事。闹腾一阵后,一众人马踏上了回家的路。一路欢笑中众人竟喊叫着把我托举起来放到驴背上,我摇摇晃晃神魂颠倒地骑在驴背上,恍如仙人……回家的路越来越近,一堆篝火燃起在三伯家大门外,一众亲人立于火焰旁向我们招手;驼背老者手提铜盆敲得盆底“咣咣”响,双方人马离更大的喜悦越来越近了……
(责任编辑 杨蕊嫣)
———作者必读(四号仿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