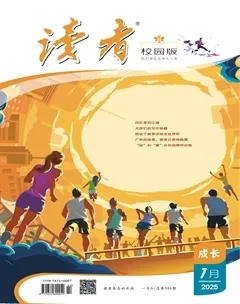关于欺凌,你应该知道的10个真相

1.什么是欺凌
美国作家特鲁迪·路德维格曾说过:如果一个人故意说了伤害别人的话,或者故意做了伤害别人的事情,但只做了一次,这叫“刻薄”;如果一个人故意反复说伤害别人的话,或者故意反复做伤害别人的事情,而被伤害的人却无力反抗,这叫“欺凌”。欺凌与正常的社交冲突之间的差异在于,欺凌包含3个关键要素:伤害意图、权力不对等、反复的攻击性行为。
2.欺凌是如何升级的
欺凌常常是从小摩擦、小矛盾开始的。比如,某个同学说话有口音,就有人模仿他说话的口音……很多欺凌行为,一开始都是偶发的。但欺凌者从中尝到了行使权力的快感,加上被欺凌者的惧怕、顺从和旁观者的沉默,欺凌行为会变得肆无忌惮。这种时候,欺凌已经与矛盾、冲突没有关系了,它更多的是一种轻视和控制——我比你强,我有权这样对待你。如果没有及时干预,欺凌就会逐渐升级,变得越来越残酷和卑劣。
3.欺凌的实质是权力的不对等
通过攻击他人获取权力和控制感是一种古老的人类本能。在校园欺凌事件中,欺凌者正是通过这种原始本能聚集权力,建立自身的支配地位。钟馨乐曾在演讲《校园欺凌从“小摩擦”逐步升级到恶性暴力,有太多可以被制止的机会,但都被错过了》中指出,欺凌很多时候并非“坏孩子”的反社会行为,而是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渴求认同与权力的表现。“青少年们努力地让自己符合某一类受到认可的文化标准,驱逐并排斥那些不合格、不一样的同伴,从而赢得更多的权力和更高的社交地位。”
4.欺凌的核心是羞耻感
欺凌者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对谁是社交等级秩序中最容易被欺凌的“猎物”非常敏感。他们会挑选那些看上去不会反抗的人。欺凌者知道,这些人会将羞耻感内化,而不是反击。欺凌者为什么欺凌他人?被欺凌者为什么不反抗?这一切都与羞耻感有关。
羞耻感是一种强烈的负面情绪,让人感到自己不值得被爱、被接纳。当一个人感到羞耻时,他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应对和缓解羞耻感。但是,当羞耻感无法缓解的时候,欺凌就诞生了。欺凌者会将羞耻感投射到他人身上,通过欺凌他人来减轻自己的羞耻感。
5.欺凌者比我们想象的更受欢迎
鉴于欺凌行为中内置的恶意和伤害性,我们一般认为欺凌者是不受欢迎的。但最新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欺凌与受欢迎程度之间呈正相关。很多欺凌者在运动、学业等方面都表现出色,而且他们的欺凌行为,的确会提高他们在同龄人中的地位和受欢迎程度,尽管这种人气部分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心理学家认为,社交环境的不确定性(比如同伴关系大换血的初一)会加强欺凌与受欢迎程度之间的关联。但在过渡期结束后,欺凌者受欢迎的程度就会逐渐减弱。
6.欺凌者是怎样养成的
有时候你会遇到那种“全员恶人”的家庭:父母欺负子女,哥哥姐姐欺负弟弟妹妹,弟弟妹妹在学校里欺负同学。更常见的情况是——家庭教育中过度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才是催生欺凌者的源头。欺凌者可能来自一个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的家庭。所以他们很容易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并将自己的行为归咎于受害者,认为是受害者“自找的”。
7.旁观者为什么袖手旁观
欺凌行为中必然包含旁观者,因为权力的实行需要得到人群的认可。旁观者的存在会让欺凌者感到自己的行为得到了认可,从而增强他们的权力感。
旁观者虽然是沉默的大多数,但实际上掌握着大部分的权力。有研究显示,当旁观者中有人站出来去制止欺凌行为时,50%的欺凌行为都会在10秒之内结束。但是有勇气站出来制止欺凌行为的只有5%到7%的人,大部分旁观者不愿意将头伸出护栏。因此,在一个欺凌的情境中,如果其他人都被残忍的笑话逗乐了的话,那么旁观者就会认为这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他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道德推脱,从而让自己从某种道德困境中解脱出来。
作为欺凌事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每个旁观者都对自身行为的后果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即便没有煽风点火,旁观者冷漠的态度也会对被欺凌者造成持久的伤害。
8.在校园欺凌中,受害者不止被欺凌者一人
对校园欺凌的受害者而言,在个人成长的关键阶段被同龄人羞辱和践踏的痛苦,会给他们带来长期的心理创伤。但在校园欺凌事件中,受欺凌者并非唯一的受害者。对欺凌者而言,欺凌行为虽然能带来一时的支配感和优越感,但长此以往,他们可能会发展出反社会人格,变得更加暴戾、残忍,甚至触犯法律。至于旁观者——目睹欺凌会让一个人丧失安全感。旁观者会陷入基于恐惧的两难:他们知道发生的一切都是错的,但因为太害怕变成下一个受害者而保持沉默。这种心理冲突可能会让他们变得麻木、冷漠,在未来的社交生活中难以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
9.社交媒体让欺凌变得更加隐蔽和不可控
社交媒体的匿名性会释放人们内心的野兽,而它的便捷性又令作恶的成本变得极低、效果极强、规模极大且隐蔽性极高。只需一个点赞、一次转发,你就成了欺凌的一部分,而你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被欺凌者则变得更加无处可逃——如果你在社交媒体上受到骚扰,你的整个社交圈都会知道这件事;只要你能访问网络,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通知提醒你。
10.我们与恶的距离有多远
在一组实验里,心理学家让实验对象回想别人对他们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情,描述发生了什么、作为受害者有何感受等。然后,他再让他们回想他们自己曾经对别人做过的最可怕的事情。
心理学家发现,实验对象对这两类事情的描述是完全不同的。当他们是受害者时,他们认为恶劣行为对他们的影响是长久的;但当他们描述自己对别人做过的坏事时,总是有各种不得已的理由。
所以,理解邪恶的第一步,是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作恶。从进化的角度来说,暴力和攻击性都是人类社会化生活的产物,深植于人性深处。比起消除人性中的暴力冲动,更现实的做法是强化我们内在约束这些冲动的力量。只要我们提高自制力,就能极大程度地减少恶。相反,如果你想制造恶,你只需要把克制自己的理由拿走。自制力的一点儿弱化,就足以导致暴力冲动的升级。恶静静地潜伏在那里,等待着被引爆。
(小鱼几条摘自《少年》2024年第10期,视觉中国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