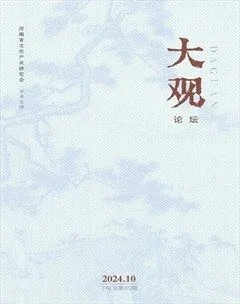“熟悉的陌生”:民族舞剧《红楼梦》中东方美学的现代表达
摘 要:中国文学名著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哲学思想及独特的价值观。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这些经典文学作品以多种艺术形式得以传承与展现。由黎星、李超导演的大型民族舞剧《红楼梦》改编自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该剧作为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的获奖作品,在文学经典、现代表达与舞蹈创作之间找到了平衡,以崭新的创作视角重新诠释了这部经典文学作品。
关键词:舞剧《红楼梦》;舞剧改编;东方美学;现代舞蹈创作
注:本文系2024年度信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立项课题“中国文学作品在舞剧创作中的文化价值研究”(2024WX058)研究成果。
“熟悉的陌生”这一概念是冯双白教授在深入研究俄国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别林斯基的理论后所提出的舞蹈评论观点。别林斯基曾指出,人们对艺术形象所感受到的新鲜感和陌生感,实则是艺术形象共性与个性的完美融合[1]。基于这一理论,冯双白教授对舞蹈艺术创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在舞蹈创作的过程中,创作者应致力于提升对文化的深刻领悟能力,锤炼出独具匠心的舞蹈表达技巧,并不断探索和创造那些既让人倍感亲切又充满新意的“熟悉的陌生”元素[2]。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文学典范,中国人对其中的角色形象和场景画面,拥有与生俱来的亲切感与熟悉感。黎星、李超版的舞剧《红楼梦》,在大众熟悉的原著场景与情节中融入了舞蹈的创新编排与现代审美,观众在欣赏过程中,不仅能够看到熟悉的文学元素,更能感受到舞蹈艺术赋予文学作品的全新审美体验。这种表现形式充分展现了舞剧的民族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是“熟悉的陌生”这一艺术理念的成功实践。
一、对传统文化的敬畏
尊重原著,是对文学作品进行舞蹈改编的前提和基础。对于《红楼梦》这样一部鸿篇巨著,由“剧”转为“舞”的这样一种平面到立体的“可视化”转换,需要面对的是庞大的故事剧情、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和丰富的文学素材等。舞剧《红楼梦》依据当代创作审美追求,以原著的经典桥段为核心,严格遵循文学作品与舞蹈艺术的互文性和辩证统一原则,达到了原著精神的准确传达与舞蹈艺术的创新融合。
(一)文学经典的中国特色
民族舞剧《红楼梦》采取了原著经典的章回体小说特色,通过提取原著中较为经典的章节,高度凝练叙事情节,在舞蹈改编中进行取舍和再创造。舞剧共分为“入府”“幻境”“含酸”“省亲”“游园”“葬花”“元宵”“丢玉”“冲喜”“团圆”“花葬”“归彼大荒”十二个篇章,各自独立又串联成篇,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且丰富的舞剧结构。
以舞剧改编中国文学经典作品,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它能产生一种很强烈的、属于中国舞蹈的戏剧性语言,同时也更易于观众理解和接受。这也向整个舞剧创作团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现代的艺术创新下还原原著的精髓。舞剧致力于全面而精准地还原原著中的情节,在舞蹈道具设计、光影媒体设计、服装设计、造型设计以及多媒体设计等多个层面,借鉴了明清古画的美学特质,奠定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审美基调。在角色的选择、舞蹈语言的凝练、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舞蹈情感的表达上,考虑了时代背景、人物命运等多种因素,力求最大程度地还原原著中人物的形态与性格,以呈现一个更为真实、立体的艺术形象。
(二)经典人物的叙事视角
舞剧《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从十二金钗的角色形象出发,演绎文学经典中的情感纠葛、家族兴衰以及人性挣扎等,放大故事细节的同时,也较为完整地将整个原著的故事脉络呈现在舞台上。
在舞剧中,贾宝玉、林黛玉及薛宝钗三位核心人物之间的事件发展与戏剧冲突,均紧密围绕他们各自的人物关系而展开。在舞蹈表现中,三位演员的肢体语言完成度及情感表达深度与原著人物高度契合,这得益于前期编导与演员对原著的精细研读和对人物形象的代表性舞蹈语汇的反复推敲与琢磨,从而精准捕捉每个人物典型的性格特征,进而沿着原著中观众所熟知的“前情景”推进情节的展开。
林黛玉、薛宝钗、贾元春、贾探春、史湘云、妙玉、贾迎春、贾惜春、王熙凤、贾巧姐、李纨、秦可卿,原著中十二金钗分别代表十二种不同属性、不同色彩的花朵。在舞剧改编中,编导通过服装、道具、舞美、多媒体设计、舞蹈语汇等文学形象的符号化和象征化的设计,对十二位演员分别进行了鲜明的形象特征和性格特质的刻画,以塑造一个唯美的、属于年轻人梦中的、有古典气质亦有现代审美的红楼十二钗群像。舞剧中十二位金钗共有五次合体亮相,分别在“幻境”“游园”“团圆”“花葬”“归彼大荒”,每次的齐聚都代表着不同的含义,推进情节发展的同时贯穿舞剧演绎的故事主线。
二、对东方美学的诠释
东方美学是一种诗性的理论,其内在的诗性思维方式赋予了艺术表现语言以诗歌般的特质,即高度的形象性、浓缩性、主观性、抒情性、生动性与含蓄性[3]。在舞剧《红楼梦》的创作历程中,编导基于对原著的深入感悟与精准把握,运用舞蹈肢体语言赋予文学作品新的艺术表达,借助舞美灯光道具还原原著恰如其分的氛围,同时借助编创手法全新诠释舞剧,阐释了编导对于东方审美的艺术洞见。
(一)虚实相生的舞蹈意境
虚实相生、情景交融是中国舞蹈的审美追求之一,也是舞蹈创作在舞蹈意象营造过程中的一个具体准则,还是舞蹈鉴赏中的一个审美标准[4]284。而意与象、情与境是中国舞蹈美学的两对重要范畴。舞蹈意境的创造主要通过形象化的情景交融的艺术特写来完成,其结构层次表现为:景—情—形—象—境[5]。虚实相生的舞蹈意境具有情感性、多义性、虚拟性和模糊性,这种意境在舞剧中有多处代表性的体现。
“入府”改编自原著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分幅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6]16。该幕采用了心理式结构描述了宝黛的初次见面,二人出神的幻想在当下的现实情景中闪现,舞台上华丽的府邸道具在灯光下快速隐去,只留演员在舞台中央演绎经典桥段“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6]23,以主角的人物内心变化推进了情节发展,现实世界的喧闹实境和精神世界的空灵虚境相交融,二人“一见钟情”的意境在细腻的舞蹈情感处理中全然脱出,给人以审美享受和情感冲击。
“幻境”改编自原著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6]32。由宝玉的梦境引入,珠帘绣幕后隐现十二金钗身着白衣缓步登场,舞动于宝玉的梦境之间,演绎“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6]41,舞台上垂下的大幅素白纱幔,昭示了太虚幻境的缥缈质感。在演员各自的独舞片段中,纱幔上十二金钗的判词依次映现,随后如云烟消逝,亦真亦幻,以意象舞美还原盛景,以宿命视角陈述了每一位人物的命运,将原著中的文字具象化呈现。
“冲喜”改编自原著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6]781和第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6]792。该幕将舞剧的悲剧氛围推向高潮,用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的红与白两色渲染悲喜交织的复杂情绪。其中,红色象征着宝钗金玉良缘的喜庆,而白色寓意着黛玉潇湘馆内焚稿断情的悲凉与哀愁。红白两色的对冲设计,让大喜大悲同时演绎,运用色彩美学隐现更深刻的含义,在视觉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增强了舞剧的戏剧张力与冲击力。通过这种方式,舞剧以有限之形,传达无尽之意境,从而展现出一种极具特色的东方审美符号。这不仅体现了中国艺术虚实相生的美学范畴,更彰显了舞剧创作的审美价值。
(二)含蓄蕴藉的东方审美
“含蓄”是含而不露但意蕴深远[4]299,与内敛、和谐、自然美等构成了东方独有的审美认知。含蓄蕴藉的东方审美,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它追求的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是情感、形式、内容三者的高度统一,也是中国舞蹈艺术特有的表达方式。在舞剧《红楼梦》中,这种审美理念得到了充分体现。
“葬花”改编自原著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6]155,该部分演绎的是宝黛二人在落花下共读《西厢记》的情景。黛玉出场,舞台上铺满了竹子的倒影,象征着黛玉清雅淡泊的气节。舞台中央的帷幔深处,花瓣从天撒落,这种细腻且富有诗意的舞蹈画面,将宝黛二人情真意切之美好隐喻地表达出来,呈现了雾里看花般唯美的氛围。该幕的展现是舞剧中式美学的极致表达,同时也是原著中宝黛产生情感波澜的重要情节,花瓣的洒落不仅营造了浪漫的氛围,而且隐喻着宝黛二人情感的诞生如同花的败落这一更深层次的话语蕴藉。
“含酸”依据原著第八回“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6]57之情节改编而成,呈现为宝黛钗三人共舞的精彩片段。编导巧妙运用舞台布局,以帷幔掀起的一角为内心戏的“小窗口”,将舞台空间一分为二,以此展现舞蹈创作中时空交错的独特叙事结构。林黛玉的敏感,薛宝钗的端庄稳重和贾宝玉的纯真懵懂,与紧锣密鼓的音乐相得益彰,共同营造出三人间微妙而复杂的情感氛围。在舞蹈的演绎中,编导精心地在舞台空间的构造与舞蹈情感的演绎中融入了内敛、细腻的东方审美符号,从而赋予文学作品在舞蹈表演领域以全新的诠释与展现。
三、现代创作的自由
崭新的现代创作风格和编导自我独特的视角是黎星、李超版《红楼梦》的一大特色,该剧并未拘泥于小说本身的框架,而是以舞剧为媒介,借由想象、抽象等编创形式表达对《红楼梦》的一种特殊情感,同时,这也是编导对原著的延伸理解与创新想象,体现了对传统文学作品的当代解读与艺术再创造。
(一)个人命运与家国同构的人文情怀
从审美范畴的视角来看,曹雪芹所著的《红楼梦》无疑是一部典型的悲剧作品,它揭示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与人性的复杂多面。但在舞剧中,“游园”“团圆”两幕是两位导演为中国观众们圆了一场美好的“红楼梦”,在遵循原著的基础上合情合理地为情造景,让十二金钗在惜春的画中得以齐聚、让红楼梦的故事在宝玉的梦境中圆满。因此舞剧中并未过多地直接展现其悲剧色彩,而是将十二金钗团聚的幻象作为一个重要的舞台画面,与小说中金钗们各自悲惨的命运形成对比,使观众在欣赏舞蹈的同时,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她们的命运多舛与无奈,以及对《红楼梦》悲剧色彩的共鸣和感慨。
(二)传统与创新的碰撞与交融
第十一幕“花葬”作为舞剧中极具现代审美特质的原创呈现,是舞剧精神内核的具象化体现。十二位女演员摒弃了华丽繁复的舞蹈服饰,身着素色服装,散下了发髻,用道具“高背椅”“白花”蕴含的双重含义,为该舞段赋予了更深刻的含义,通过极具张力和抽象性的现代舞的舞蹈语汇描绘出了十二金钗在家族兴衰、命运浮沉中的顽强挣扎与不屈抗争。尽管此幕的改编成为舞剧中备受争议的一处,但无疑在传统文化题材舞剧的改编历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为艺术创作的独特魅力就在于其富有自由性和创新性,能够为观众营造留白想象空间,让人们看到舞剧艺术的无限可能性和创新力量,引发人们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关系的深入思考。
《红楼梦》的舞剧改编不仅深刻映射出中国改编类舞剧在发展进程中的鲜明取向,更展现了舞蹈创作理念的变革。在舞蹈创作层面,逐渐摒弃了先前过度侧重于模仿的陈旧模式,转而更加聚焦于文化内核的挖掘与呈现,致力于深入探寻传统文化与现代话语的交融点。作为编导表达自我精神世界的重要载体,舞剧在最后对原著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还原本真”的概念赋予,特别着墨于金陵十二钗与所有女性个人命运的深沉关联,打破了传统情节、时空关系的束缚和观众对原有认知的固有期待,从而达到了艺术创作的先锋性。
综上所述,舞剧《红楼梦》是以年轻一代视角对民族文学经典的再演绎,把爱情故事转化为女性思考的表达,以舞蹈肢体连接传统与当下,在按部就班中打破常规,在熟悉的艺术形象中寻找创新的表达,演绎女性的力量,呈现编导对时代变迁和生命本真的体悟,让红楼记忆、民族记忆和生命感触得以共情共舞。
参考文献:
[1]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M]//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379-382.
[2]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应邀来校讲学[EB/OL].(2024-05-17)[2024-07-22].https://news.xynu.edu.cn/info/1004/22550.htm.
[3]邱紫华.东方美学史: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9.
[4]袁禾.中国舞蹈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5]隆荫培,徐尔充.舞蹈艺术概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175.
[6]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长沙:岳麓书社,1987.
作者单位:
信阳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