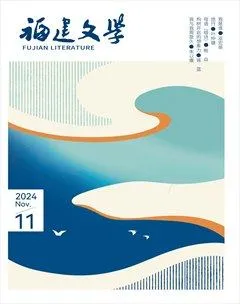我与我周旋久

1
到一个小朋友家,看到他书桌上一摞字帖,其中一本是《兰亭集序》。心想这个小家伙至少在五岁时就看到《兰亭集序》了,而我是二十五岁,整整迟了二十年。那时在山区,冬日,有幸搭一辆货车到县城,在新华书店买下,书价是五角。有人说好东西都要及早品味,境界才会高远。如我这般命途不畅的人,许多好东西都是在考上大学才品味到的,便生出许多遗憾,觉得看迟了,眼界低了。其实《兰亭集序》买来后我也没有认真临写——我不太喜欢这种轻逸的笔调,喜欢比较质朴的、拙重的。后来我下功夫的也是王羲之这个时代的,只不过不是名家,而是一些民间的无名氏的墨迹,譬如敦煌残经。我当书法教师之后,也没有推荐《兰亭集序》让学生学,因为它太有名了,应该把它供起来,敬而远之。有人让我推荐字帖,我会更侧重于北朝那个时段的碑刻,同样也是一些无名氏的笔调。有人猜度我是不是怀疑《兰亭集序》非王羲之所书,我说和这个没关系,主要是学的人太多了,咱们何必再挤进去,况天下独异的碑帖太多了,不必止步于此。这也使我的学生,好像没有一位能把《兰亭集序》写得传神的。
今年春节我是在湄洲岛度过的。一位喜爱书法的学生在自己开的宾馆里填充了大量的书法情调。他让我到楼上看看,自己选一间喜欢的。我转了一下,每个房间的窗帘都让他印上《兰亭集序》了。拉开就是一幅巨制,合拢起来,各种笔画探头探脑。人在房间,就得看着,除非熄灯睡觉。其实他全然可以每张窗帘所印不同,书法风格多了,各个房间就韵致不同,适宜不同欣赏趣味的人们。但他太喜欢《兰亭集序》,希望每位住宿者也如此。我想在此住几天的人从此都会记住《兰亭集序》,由于他的传播,即使全无书法常识的人,也能和人说道几句。关于《兰亭集序》有许多故事,故事让俗常人好奇,说道中越发添加它的神秘和幽深——既然是旷世之作,也就有无限的可解读性,非奇不传。我想,没有哪一幅古人作品会比《兰亭集序》更有讲头。讲吧,讲吧!
我认识的人中,苏先生在百岁那年出了大名。他经历那么多时段,晚清、民国、北伐、抗战、解放战争,进入新社会,又骎骎进入改革开放。风云变幻无休,他一以贯之地学《兰亭集序》,最多也不逸出魏晋这个范畴。百岁那年他参加一个比赛——就是以《兰亭集序》参加的,得了一等奖,算是给自己的百岁诞辰来了一份大礼。如果传王羲之写《兰亭集序》为五十出头,那么苏先生则年岁大他一倍。相比之下我非常喜欢苏先生笔调的,质朴深沉,有沧桑浑穆之气,是另一种境界的《兰亭集序》。后来苏先生送了我两幅书法,字无多,却胜千军万马。苏先生百岁后进入名家行列,而且与《兰亭集序》紧密相连。他常年写字是为了调息养神的,却想不到有这么美好的结果,百岁之前,无人知之,百岁之后,无人不知。我以为是上天对他持恒不辍的嘉奖。
现在碰到的难题是《兰亭集序》的真伪——有好事者会问真耶伪耶这个问题。清人张问陶认为“古人已死不须争”,我是很赞同的。但活着的人对死去的人留下的谜团,还是喜欢有一些自己的见解,于是争无休。这个《兰亭集序》放在西、东晋这个时段的书法作品堆里,无论如何都如生客阑入举座寡欢。有人说他是书圣,是超人。我当然也同意,他超出我们这些凡俗之人太多了。
但是,他超不出那个时代。
2
王献之算得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典型,后人称大小王,说的就是他父子俩。许多的传承到父辈这一代就终结了,因为下一辈毫无兴致,或者创造力不济,便接不下来。家学承传,还真不是可以轻易言说的。现在,王献之的大名还能与其父一起为我们所知,这么长的时光,可见不是浪得虚名,肯定有一些实在之质可以细读细审,尽管那个时候众人并不认为他是瑚琏之器,说的都是他父亲如何了得。
有一个盛会让王献之赶上了,那就是353年的兰亭雅集,他八九岁。此次曲水流觞中他没有作诗,清代一位文士说起这事还讥讽他,“却笑乌衣王大令,兰亭会上竟无诗”,其实他那么小,愿意跟着父兄来看风景就很好了。那些参与雅集的成年名士,也有十多人作不出诗来——有的快才,有的慢才,每个名士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必如此计较。我后来也参加了兰亭雅集——当然,离王献之参加的那次已经过去一千多年,人已非,江南的暮春还是旖旎如故。参加的人穿上了晋时装,坐在曲水边,开始一场仿古的游戏。看着载酒的觞晃晃悠悠转着漂下来,人就有些激动和紧张。想着若停在我跟前,是否能来一首最简洁的十六字令?我盘手坐着,看着旁边的参与者,都有些急促,看手机的、翻笔记本的,上边的诗是早作好的,或者请人作的。其实,雅集就是玩玩,不会作诗实在不算什么。现在的书法家都与古人不同,此时要仿古人写兰亭诗、兰亭序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王献之是有野心的,我一直认为他夸奖王珉时说的那句话是他自己的写照:“弟书如骑骡,骎骎欲度骅骝前。”
父亲的影子太大,把他都笼罩住了。到了初唐,声名又受重创,更是无可奈何。李世民只喜欢王羲之的书法,捧到尽善尽美的高度。他看不上王献之,说他字势疏瘦,宛如隆冬之枯树,了无伸张气度;又认为他笔踪拘束,好似饿隶久病,无纵横之象。一个皇帝这么说了,朝野都要受影响。王献之书法绝不是李世民所说的,而是相反。他的过人处就是与父亲的笔调相异,下笔胆大,纵横开阖,无所羁囿。像那个《鸭头丸帖》,那么小,字无多,却咫尺有千里之势,小中见大了。不知别人如何理论他的“破体”,从字面上解也很简单,就是破前人、破时人,也破破自己的父亲,开拓自己的审美空间。
每个人都有对风格的喜好和嫌恶,依自己的性情而为就是。李世民的倾向性这么鲜明那是很自然的,只是智者不要止于皇帝之说。
被人亲切地称为“小王”,是他风格形成之后,开始为人承认。和开宗立派的父亲在一起很幸福,也很悲哀——如果不比别人更下气力,展示出与父亲笔下不同的风采,那永远都没办法让阳光洒落在自己的肩头。小王的几个弟兄也不甘示弱,那个时代就是一个诗酒风流的时代,美风仪,美才情,美独立之个性,不是燕雀之网可以罗。一个人可以没有成佛作祖的雄心,不为人囿的野心还是有的,那就是让人从笔迹中察觉出独异,与王羲之不同,也与同时的名士谢安、王珣、孙绰等都不同。做到这点,真是一个很艰难的指向。
现在我们说王玄之、王凝之、王徽之、王操之、王焕之,都不如说小王真切,可以看清他与人不同的容颜了。
3
说虞世南,似乎没什么好说,他能让人当故事说道的太少了。艺文从事者,有的总要弄出不少动静,支持了传播的宽广度。虞世南没有,让人不知从何处说起。俗世生存中的人不喜藏而喜露,越来越爱分享,把应该藏的那部分也像口袋那般翻出来给众人看,似乎不如此难以为人。虞世南的故事我以为有很多,只是当时他把口袋扎住了,现在更是尘泥三尺,打不开了。他从隋朝入唐,当了李世民的书法老师——一个人与皇帝这么亲近,他还是自觉地持守,寻常交流寻常写。李世民称他身怀“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五绝,都是正经之说,形成不了传奇。虞世南身居庙堂之高,条件优越,纸墨充足,他又活得那么久,本以为会写出许多佳作并得到良好保存,没想到少得可怜——这是我一直疑惑的。后来的颜真卿,处乱世中,留下来的作品却比他多得多。作品多了,创作链就清晰了,使人把握住一位书法家的笔墨历程。而我们面对虞世南则无此可能,可以说他离我很远。如果不是今日行笔,又几人说虞世南——他算是一个很静穆的人。
如果有人问我天下谁学虞世南书法最传神,我还真说不上来。给虞世南很大的声名,成为一座里程碑,这些都可以做到,而实际上人离他很远。他的笔下太过平整岑寂,像在汹汹的场面上一个人站着不动。越来越快的生存节奏,也使人们更积极倾向那些飞扬跌宕的形态和表现手法——毕竟,我们做一件事,还是为了让人看到,否则就白瞎了。虞世南的楷书《夫子庙堂碑》一直享有盛名,却也一直处清冷中。可以想见虞世南当年动笔时,内心是何等恭敬、谨慎。文章是他做的,字是他写的,此时古稀了,投入多少心力,多少功力!我没有临写过《夫子庙堂碑》。这方碑是让人来感受与敬畏的,真去临写就徒劳了——古人的作品对后人来说都有贡献,有的实用,有的感悟。那些有象征、隐喻功能的,就是用来悟。既是悟,那就玄妙了。他内心那么多微妙复杂的情思,连同作为一个生存中人处庙堂之高的深想善感,都以一种静态的方式寄于一碑之内,绝不可轻言看懂。我以为《夫子庙堂碑》是“无用”的,绝无可能铸剑去竞赛场上显露身手,这也注定它的寂寞是一个长久的时日。
我对“无用”抱持多年。我对史上的遗留都是抱着适意来接受的,这会使自己在笔墨行程上更多地自由与开怀。《夫子庙堂碑》有一缕清洁的诗性之美——我嫌纸上狼藉不堪和汁水四溢,尽管有所谓的墨趣。洁癖还是文士需要具备的,尽管我上升不到名士这个程度,但濡墨行笔时,素净是我顽固的遵守。像傅青主那样的用墨,得到那么多的夸奖,我从来缄默无声——有人喜欢晕润一团,有人喜欢洁净如玉,只能各行其道。在微凉的深秋书斋,我不断地把玩《夫子庙堂碑》的洁净之美,那澄澈秋空般的天幕,没有一只飞鸟过往。
它对我来说既无用,又实有大用,只是难说。
清人吴淇说:“我与古人不相及者,积时使然;然有相及者,古人之诗书在焉。”就算是和虞世南同时代,要与他谈书艺,真没有可能。他的位置那么高,与平民之间是一道鸿沟。但我千百年后居然能与之相及,的确是来自他的诗与书法。可以说,他笔下是给我不少暗示的,暗示写得慢些,写得纯粹一点,那些枝蔓的牵扯都得芟除了当。比起同时的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要更孤独一些。像他这般真能具备“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五绝的人,众人还是敬而远之的,和他没什么好说。
他那个著名的写蝉诗句“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我想就是写他自己,他身在高处,却很自信。
虞世南就是一只不死之蝉。
4
看了几篇文章,都是追捧颜真卿的,说他的《祭侄文稿》应该超越《兰亭集序》,成为“天下第一行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座次观,如果闲得无聊,可以从第一一直排到千万。
颜真卿是忠烈之士。如果没有安史之乱,他理应可以多活很久,笔下多出很多好作品。颜真卿的存在使我们在教化上多了一个典型人物,可以借此解决教化上的一些问题。我想,道德是道德,书法是书法,分开来说会爽朗一些。我自幼承庭训习书,后来就没有断过。我感受着不必与人合作的独自快乐,日子一天天过去,很贫瘠,很艰辛。这方面也就是要自觉地把自己培养成一名独行者,写无休。这样做的人不只我一个,而是很多。道德品质保持在中等水平,艺术指标却定得很高。整日自个儿忙碌,交游也就无多。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在阿默斯特镇的居民看来,她简直就是一个隐者,很少能看到她出门的身影。有时她想让镇上的孩童品尝到美味的糕点、糖果,也是装在一个篮子里,打开窗户,用绳子吊下去。至于这些糕点、糖果,也不是她出门去买的。她都在房间里,不停地写,越写越多,也不急于发表,先放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像颜真卿这样能成为忠烈,又善写,书法史上无多。二者不能兼顾时,就选择写字——我是这样想的。
颜真卿楷书对我的书写心态起了作用,就是缓慢,慢心态,慢手态,让自己热爱慢。很多人的目的都是以颜真卿的楷书为基座,把握好了,如重器不可移易。他中年以后的字不能称雅致,有金刚力士气象,学不好就是一堆死墨,混沌不开。这也使人学了几年之后就向他告别,与他周旋久的人都有德艺双修的想法,平生托付颜体不悔。
活人与古代碑帖的关系有如鸟与树。树是兀立不动的,鸟却是飞动游移,不会长久地立于一棵树的枝条上。人的选择和放弃有许多缘由,随大流,徇时势,依性情。如果是依性情就好了,很真诚地学习,也很真诚地放弃。
《祭侄文稿》是颜真卿最著名的作品。说直白一点就是一篇祭文。没有谁会把《祭侄文稿》作为背景图案展示在庆典上。文辞让人心有惊恐,逆贼、凶威、荼毒、巢倾卵覆、呜呼哀哉,都不是俗常人乐意见到的。由于思绪悲怆散乱,笔迹也草草复草草,涂抹复涂抹——草稿就是如此,任性情驱遣纵横无碍,行于可行处,也行于不可行处,出轨越位并无不妥,只是向前。有些字是写给执掌权柄者看的,像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就得精工极致,尽遵矩镌。颜真卿写《祭侄文稿》则是吊哀纪丧——家族死了那么多人,自己却还苟活着,奈何奈何。这个文稿最有美感的就是那些涂抹的痕迹,它们不是字,是乱麻般的心绪,是他写《颜勤礼碑》《颜家庙碑》所不曾有的。
这些涂抹之痕也给好事者信心——一个人恣意而作,忘天地,忘众生,忘自我,何曾不是第一。
读《随园诗话》。有人问袁枚,当朝诗人谁为第一,袁枚反问他,《诗经》三百首,哪一首为第一。那个人没法回答。
问这个问题的人本身就有问题。
5
从一些记载来看,张旭和怀素皆以狂草闻名,人们还是更偏爱怀素。论怀素草书的诗、文还真不少,使他离我们近了许多。李白年长怀素二十多岁,还是写了一首《草书歌行》赞美——我想后来许多文士作诗文盛赞怀素,和李白率先写这首诗有关。
李白在这首诗里描绘了某一年的八月九月秋高气爽的日子里,酒徒辞客坐满了一个空间,免费欣赏一场墨戏——这是怀素给大家带来的福利。
李白是描写现场的高手,不知道当时他是否到场。如果真到场了,主持人一定要给他安排一个最好的位置,让他能把怀素挥毫的形神尽收眼底。而此时,怀素正在醉后的蒙眬里,准备出场。要是我,是不会坐下来看的。我不喜欢这样的表演。尤其像他这样的身份,到抄经堂静静抄写会更适宜。后世以书写为节目表演的越来越多了,有酒前的,有醉后的。既然李白都赞赏不已,后人步其旧辙,开表演新径,也无不当。没有人界定书写应该是哪样的一种姿势,只是各自去写,大叫狂走的,攘袖瞠目的,各尽其兴。昆德拉不会书法,但他会说:“没有一点疯狂,生活就不值得过,听凭内心的呼声的引导吧。”如此,则不必批评怀素的疯狂,他把自己置于如此适宜的场所,就是在众人目击下想开心一把。我与怀素异也,真参与一些笔会,也是信手写三两字应酬。只有在书斋里,才会心机松弛,写上百字千字。说起来,怀素是一位善于与人交流调动情绪的大师,他的狂草的功夫、激情,都是让人欣赏的亮点。李白说:“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辞客满高堂。”观众早早到了,耐心等待明星——这和现在是多么相似,就差没有高呼“怀素、怀素。”
李白诗中,有不少笔墨是惊叹速度的,“须臾扫尽纸千张”“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真是狂人之速。我买了十刀宣纸,一年都没有写完。看怀素表演也是需要储备的,一场下来,先备一百刀纸吧。李白做了一些调查后说:“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怀素的书写量太大了,亏了他有闪电般的速度,满足众生求书的愿望。不知当年李白看怀素表演是写了什么,他写了那么多,而留到现在没多少了,估计每一场表演之后都被人顺走,不知所终。现在我们谈怀素还是喜欢从《自叙帖》来展开——他把张芝、张旭以来的草书速度推到了极端。他的狂草应和我们同样高速。高速已经填充在我们日常的每个动作里,不让自己快起来,就是给自己找不自在。
狂草《自叙帖》有“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以这十个字喻怀素,再没有更合适的了。
6
有人问我宋代哪位书法家给我的影响比较长久,我说是欧阳修,他便有些意外——他本以为我会说黄庭坚或者米芾。
欧阳修是我的书法生活的导师,这是我很多年前读他的书论时认定的。欧阳修的书论浅显——大家笔下都是如此,不必故作高深让人看不懂。语言的运用太神奇了,但都是用来让人读的。他的书论零零星星,并没有专注于此,但三句两句,便可照亮前路。
欧阳修说的是:“至于学字,为于不倦时,往往可以消日。”这是他中年以后的一点体会。人虽生不同时,但有许多相通处,可以越过时空。欧阳修那个时代是笔墨无歇的时代,文士可以靠一支笔来打天下,建立功业。后来欧阳修功名有了,同时也觉得绷太紧了,如一把长期撑开的伞,一张拉满的弦,总是有些吃力。欧阳修自陈,他此前广泛的艺文爱好都渐渐舍弃了,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毕竟难以安放,只有书法被他继续下来——这种书写形式对于人生,太适宜“消日”了。通俗地说,就是写字是很好打发时日的。一个人终日忙碌何为,过于闲散又何为,都不及写字快意。人生虽短,算算还是有大把时间可以打发的,那就写吧。欧阳修说的就是一种日常化书写的意思,如饥食困眠,是很私有的事。
一个人成名后,坐在家中都会有人邀请,参加这个展览,或者那个展览。古人没有展览,雅集倒是不少,作品就从书斋进入一个广大的空间。作品展示说起来是大好大坏的博弈,有时被人说得一文不值,以至扫兴不已。但文士还是勇猛精进,像古诗人,游走于公卿大夫、豪门通显之间,呈上一组诗,是以端楷写的,中锋行进,笔笔精到。为了功名前程,此时就不能信笔,自觉地克制一下自己。我觉得自己也有与他们相近的心态,参加有档次的展览,必尽全身之力以奔赴。废纸一大堆,才可能挑出一幅。太认真用意了,也就甚合法度,可是自然度削弱了许多。我是一个比较敬惜字纸的人,有的老宣纸写坏了,边角还有一些空白,我会取出一枚刀片,将其细细裁下。瘦长形的、小方块的,我信手写两三个字,或者一句诗,成一小品,轻松之至。这些年,这样的边角纸条写得多了,说不上有多好,只是自然之至,不须用意,也不须用力——过日子也理当如此,不必经常思考其中的意义,否则人生就辛苦了。
我想这类作品会越来越多,它更合于欧阳修的“消日”观,它的维度是向下的,再向下的。
女作家亚历克西斯·赖特谦卑地说:“我连尘埃都不是,我只是一场梦。”写手都是为做梦而来的,因为有了写,梦的尽头是这些纸本,可视可抚。
写写复写写。欧阳修的“消日”说是落实在他的楷书上的,他循颜真卿轨辙,说起来没什么新意。他在政治上、文学上堪称大家,书法上就不必再跻入大家行列了。据我能看得到的欧阳修楷书,的确贯彻了他的“消日”观,就是很自然。
7
和赵孟頫同处一个时代,只能说不幸。有一次我得到一个机会,看了不少元代的书法作品,作者有的是通显的官僚,有的是寻常士人,他们的笔迹都与赵孟頫无异。如果把名字遮起来,还以为是赵氏亲笔。一个人的才华如此远迈不群,文也好,艺也好,官也当得好,什么都过人,只能让人膺服认命。和赵氏同时代的鲜于枢说“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代第一。”如此直截了当,鲜见,鲜见!
杨维桢的出现给了后人另一个思考的角度。
杨维桢如同生活在别处,不知有赵,无视风气。他走一条与赵孟頫不同的道路,不易其守,不累其真。赵书妩媚甜美,杨书冷峭夭矫,赵书圆熟精致,杨书生涩奇崛。赵书太让人喜欢了,说雅俗共赏绝不为过,几十年来培养起一个书写群,一个欣赏群。赵孟頫在前,大家跟着走,人在群中,自然其乐融融,蔚成风气。杨维桢此生注定要踽踽独行,没有多少人喜爱他这样的笔法,既杂汉简,又掺章草,纵横奇诡,跌宕无常。估计要到中年这个份上才会理解这种写法。亨利·梭罗在《行走》中曾将流浪者称为自由和独立的个体。人情已尽,俗世无恋,也就没有顾忌,行止皆得于己。我认为梭罗所说的流浪者是从精神上认定的,如此才有价值。
赵孟頫在我看来是一个善忍之人,内心苦痛,睡不着觉,笔下却都是春风锦绣,内外相差很远。常人只见到春色,不知冬夜。杨维桢则书如性情,性情如书,狂狷出之。他这么多的号,都是坚硬冰冷——铁崖、老铁、铁心道人、铁笛道人、铁龙道人、铁冠道人,怎一个铁字无休,如此高冷,又何人与之相近?
后来我发现这么理解杨维桢偏颇了——他不是那么免俗的,他最快乐的是在昆山遇到了巨富顾仲瑛,这个比他小十五岁的崇拜者大方地买了好几个歌伎舞女送给他,说是让他组建家庭乐班。接下来顾仲瑛还为杨维桢出版诗集,使他声名广播。为了回报,杨维桢为顾仲瑛收藏的大量古字画作了题跋,为他的玉山草堂写了不少美文,其鼓吹也罢,虚誉也罢,看得出杨维桢温柔了。尤其是那一首《顾仲瑛为铁心子买妾歌》,亲昵地点到绿花、杨柳、芙蓉的艺名,可见陶醉。每次到玉山草堂,杨维桢都得到了隆重的款待和敬重,附近的同道知之,也赶来相见,诗酒流连,吟唱遣兴,那真是让人难忘的好时光。杨维桢总是会及时地用他的“铁崖体”记录下来:“余抵昆,仲瑛必迎余桃源所,所清绝如在壶天,四时花木晏遇,常如三月时,殆不似人间世也。”
谢榛曾说:“善人在坐,君子俱来。”杨维桢似乎就是善人,他每次来昆山,文士名流都会接踵而至,玉山草堂热闹了起来。据闻雅集七十余次,赋诗三千首。后人将其与兰亭雅集相比,也颇有见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艺文之道,有的喜欢追时兴而走,写一手足以乱真的赵体字,也是能自慰平生的。有的人却与之相悖,于时兴不闻不视,如同虚无。个人的脾性疯长起来了,笔下何羁,只任意一往。合群有合群的乐趣,单干有单干的自在。书法还是适宜单干,单干久了,一下笔,个人气味就飞扬起来。
对杨维桢的书法,我是一直都喜欢着的。
对杨维桢这个人,我则喜欢五十岁之前的他,也就是认识顾仲瑛之前。
我已习惯了把人与书法分开来说,如此会更清楚。
责任编辑 陈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