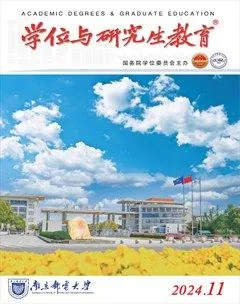研究生学分制的失灵

DOI: 10.16750/j.adge.2024.11.008
摘要:研究生学分制作为研究生教学管理制度,旨在促进研究生自主学习和自由探究。实践中却运转失灵:先教学后科研,催化“赶课”与“趋易”;重教学轻学习,课外学时缺位;标准模糊,教学与科研学分分配参差;旨趣消弭,协调教学、学习、科研的自主性与灵活性式微。究其根源,研究生教育的“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发生断裂,学分制未能匹配教育制度环境变迁与协调连结体的统一。在研究生教育系统层面,应通过完善分类、以研带教和以教促研整合连结体;在学分管理技术层面,应合理规划学分量,完善学分的认定、转换与衔接;在学习文化层面,应增进多主体的认知,焕发学分制的价值与理想。
关键词:学分制;研究生教育;“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研究生管理
作者简介:刘业青,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比较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林杰,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875。
当前,研究生教育中的学生匆匆赶课、避重就轻选修“水课”、对课程学习不满意等现象司空见惯。大学将成因归咎于研究生的功利主义或教师的授课质量,却忽略了学分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学分制作为研究生教学的一种管理制度,不仅承担学时计量的管理职责,也指涉研究生培养的结构与内容。学分制策源自欧美国家,镶嵌于特定的教育体制及文化土壤。生硬的移植会招致淮橘而枳的症候,日本便是前车之鉴。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引入美国的学分制,迥异的文化、环境和结构性因素造成学分制的收效不佳[1]。我国的学分制同样引自欧美,所“嫁接”的研究生教育体制与学分制“原生”的教育体制存在出入,它能否实现赋予学生学习自由、促进自主学习的初衷[2],是否能改善研究生培养质量,皆有待研判。
高等教育中学分制的研究成果浩繁,却心照不宣地聚焦于本科阶段,研究生阶段几乎隐身。但是,本科学分制的症结在于课程量过多[3]以及选修课程纷繁破碎而威胁知识结构的体系性与统一性[4],学分制应对的难题是平衡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5]78-79,而研究生阶段以专业教育为主导,学分的课程量要求显著下降,不构成课程过载以及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冲突。学段性质殊异,本科学分制的研究成果并不能充分揭示和回应研究生学分制。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研究生学分制失灵的表征与原因是什么?以教育学科为案例的原因在于,教育学专门研究和管理教育活动,若教育学科的学分制尚存在失灵,遑论其他学科,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研究生学分制的病灶。研究方法上,依托多重证据,通过文献研究、整理全国十余所教育学作为优势学科高校的政策文本,并辅以这些高校教育学科师生的访谈资料及网络资料,阐释研究生学分制的失灵表征。同时,借助伯顿·克拉克的“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researchteachingstudy nexus)的理论视角,分析研究生学分制失灵的成因。
一、研究生学分制的引入与发展
1.哈佛大学改革与卡内基学分:美国的学分制雏形
学分制发轫于德国,完善于美国,是选课制发展的产物。学分制的理念可溯至18世纪末的德国,洪堡办学崇尚科学研究,以学术自由为原则。受此思想推动,柏林大学创设选课制,保障学生的自主学习权利,尊重个性。这一观念与制度深刻影响到美国的高等教育,弗吉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院校在19世纪初开启试验,此后选修制得以在美国推广[6]116。
选课制在美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拓上实用主义烙印。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人才需求多样化的时代洪流中,选课制过于刻板的短板暴露出来。19世纪下半叶,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 Eliot)推行学分制,以学分衡量学生的学习成果,作为授予学位的依据。这彻底改变了旧时修满必修课才能获得学位的办法,学生可根据兴趣选修课程,完成一定数量学分即可获得学位,学分制的雏形由此定型。
在学分制的制度化进程中,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的角色也不容小觑。20世纪初,该机构捐赠1000万美元在全国范围制定资助计划,并提出符合标准的条件,要求学校基于课堂时间(师生接触)授予学分,1学分对应120小时,即“卡内基学分”(Carnegie Unit)。因操作性强、易于理解,学分日益传播为一项通用的教育管理工具[7]127。
学分制的后续改进主要指涉两个维度:一是学时数量与构成。卡内基学分标准是针对高中阶段提出的,目的是保障学生升入大学的质量,便于学段衔接。但美国大学的教育规划难以匹配1学分120小时的要求,故逐渐改变为1学分对应约12小时课堂教学以及3倍课外学习时间,将匹配课堂的课外学习任务量纳入学分要求[8]。二是学分分配与选择。学分制在大学推行时遭到强烈质疑,抨击其自由选修割裂了课程体系与知识结构。哈佛大学又一次率先以改革回应。艾略特的继任校长劳伦斯·洛厄尔(Lawrence Lowell)创设集中分配制,规定学生将选修课程中的一部分“集中”在专业主修范围,一部分“分配”于人文、社会、自然科学,剩余部分自由选择。并引进英国的导师制,帮助学生规划学业[9]36-37。
总体上,学分制是以学分为单位衡量学业成果和水平的教学管理制度,经历多次调整后建制,更具弹性和适应力,扩散至世界各地,发展出多元形态。但学分制的产生服务于本科阶段,初衷在解决课程学习的评估、认定问题,“先天”聚焦教与学,不具备协调“科研—教学—学习”的连结体意识,在导入以科研为主要教育方式的研究生教育时,遭遇协调科研与教学、学习的挑战,亟待调适。
2.从传统学年制到学年学分制:我国学分制的主流形态
中国的现代学分制最早出现于民国时期。五四运动以后,一些视野开阔或具有留学背景的教育家从美国、日本引进前沿教育制度,例如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实施的选科制和积点学分制[10]。1919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下,试行选课与学分制,各高校随之效仿,直至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制度承袭苏联,放弃学分制而用学年制,所有学生在同一套刚性教学计划和培养规格下接受教育。其后又历停滞,直至1978年又重新采用学分制。
1978年是我国学分制发展的新生阶段,恢复研究生招生后,学分制再次登上历史舞台。除北京大学外,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也随之实践。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将学分与学位制度确立下来,国家教委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先行先试,学分制开始向全国扩散。这一时期的重心在本科阶段学分制,只有少数重点大学将学分制应用于研究生教育,例如中国人民大学规定“提前修满学分并完成其他学习项目者,允许提前毕业;缩短两个主学期,增加的副学期组织选修课、社会调查、科学研究和撰写论文;增设体育课和计算机基础知识”[11],将学分与弹性学期、学位颁发、选修课程结合起来,形成一系列学分管理制度。当时,受限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实景,广大高校起步缓慢,仍是在统一教学规划下适当增强灵活性,学分制的应用程度有限[12]。
直至2000年前后,研究生学分制才真正普及并成型。2000年之前,我国研究生教育还未大规模扩招,许多高校和专业还未取得硕士学位授权,研究生和导师数量寥寥,不具备施行学分制的物质条件,研究生教育仍沿袭传统的“学徒式”培养形式,即小规模的导师带教,研究生跟随导师自主学习,培养体制还未成熟。伴随研究生扩招,研究生学分制才正规化、体系化。经多年实践与探索,我国研究生学分制衍生出多元类型,完全学分制、学年学分制、混合学分制等。主流形态是学年学分制。它将传统学年制与完全学分制折衷,既遵循学年制的计划性,保有修业年限和必修课程,又迎合学分制要义设立多元选修课程,兼具一定程度的学习自由和弹性。
总体上,学分制改造了我国的研究生教育面貌,实现多重进步:一在教育观念,学分制蕴含学习自由的大学精神与理想,承认个体差异,学生能依据禀赋和兴趣自由学习、各展所长[13]138。学分制的弹性教学计划交还学生学习自主权,提升学生学习主动性[14]。二在培养制度,学分制赋予课程灵活性、延展度,依托选修制这一实现形式,不仅突破刚性教学计划和统一课程体系对思维的固化,还提供跨学科、创新思维的孕育空间,避免人才培养的趋同,并且推动课程质量的革新,学生选修“用脚投票”,若教师开课陈旧、质量低下可能导致无人问津。三在管理与评价,学分制实质是一套教育管理制度,不仅是计量学习时间与成果的一般等价物。学分改革可引起系统的管理变革,包括研究生教育治理结构与方式、管理实践与技术、与内外部教育环境的关系,以及教育和学习文化[15]。因此,虽然学分制的主要功能在课程教学管理,但当前研究生培养的制度环境已然变化,以科研为重心,学分制有必要与科研等其他活动环节充分匹配。
3.我国研究生学分制的实景:教育学科的案例
由于学科各异,学科之间可比性弱,因此从特定学科切入分析。相比其他学科,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指向学校(教育制度)、学生和教师,更善于发现、反思和修正教育症候,其教育制度实施更符合人才培养规律,实现教育功能。若教育学科的研究生教育学分制尚有问题,一定程度上寓示其他学科也难以幸免。同时,本研究聚焦学术学位硕士类型。
综合多轮教育部学科评估结果,本研究确定教育学为一级学科且长期居于A类的十所高校,并增加一所西部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覆盖全国各地的教育学科为代表性院校。基于官方网站、问询、访谈补充等多途径,收集这些学校研究生教育学分制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培养方案、研究生手册、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学位培养要求),以官方网站的更新版文件为准。教育学科下设有多个研究方向,经比较发现,虽学分要求略有差异,课程选择有所偏向,但在学分方面的规制基本一致,具体见表1。
教育学科的研究生学分制反映出如下特征:①学分制牵涉广泛,不只是课程,而关联科研、社会实践、其他培养规定、学位论文等一系列培养要求,能够调控个体的学习规划与进程。②学分量主要分配于课程,其他教学形态的计量薄弱。课程学分占总学分的平均比例约85%,科研/社会实践等学分的比例不到15%,许多培养环节和附加培养规定甚至不计入学分。③课程模块与分类精细,专业知识的系统与连贯难以保障。公共选修、公共必修、专业选修、学位基础、学位必修、跨学科选修或自由选修等类目众多,因此在每门课程学分量少(2学分为主)的结构下,分布到每个模块不多,专业必修课程也存在碎片化,不易实现奠定学生专业知识体系的预期,尤其是选修课程(专业选修和跨学科或自由选修)学分量偏低,不到1/3。④偏重课堂教学形态,忽略课外学时。学分内涵不止在课内学时,在美国、日本均演进为1教学学时配套2至3倍课外学时,但国内高校的规定中缺乏阐释和强调学分指涉的课外学时。只关注教学学时可能错估学习一门课程所需的真实时间,不利于课程安排的张弛与课程学习质量。⑤免修、免听制度应用有限。免修几乎均适用于公共课(外语),专业方面的免修免听制度暂不健全,不易于不同专业水平的学生差异化施教。
通而观之,研究生教育学分制的突出问题是教育过程重教学(课程),但实质和结果是科研导向(学位论文、小论文成果),暴露教学与科研任务、自主学习的不相协调,为实践中的失灵埋下伏笔。
二、研究生学分制失灵的表征
基于访谈、高校政策文本与研究文献、网络论坛等资料分析发现,教育学研究生的学分制存在制度失灵,失灵意味着学分制未发挥预期功能,实施低效而有碍教育质量,集中于四个向度。
1.学分规定的区隔:先教学后科研,催化“赶课”与“趋易”
研究生教育中广泛存在一类异象:研究生将课程学习堆挤在前期,尤其前两个学期课业繁重,奔忙于不同教室间。学校从未直接规定课程修读的时间,强制第一年完成,甚至少数高校要求第二学年修读适量学分以避免课程过度集中,却为何产生“赶课”这一无形秩序?一些受访者坦言,初入新环境,受制于有限理性,追随往届学生经验或同侪行为无疑是稳妥选择。但这难以解释往届学生和同侪行为又源于何处、有何依据。考察培养方案发现,集体性行动背后隐藏制度性约束。中期考核是高校研究生教育中的常设环节,通常在第三学期完成,考核条件是完成课程学分、开题、学术伦理规范测试,这间接告诫研究生务必第三学期前修完所有课程。制度原意是加强管理、保障研究生的学业进程,前期以课程奠定专业基础,后期专注于学位论文(保证投入时间不少于1年),但却造成课程与科研的分隔,与自主选修、修业灵活的学分制初衷背离,抑制学分修读的灵活性。最终形成先教学后科研的研究生培养节律,导致研究生忙于将学分集中修完。
忙于“赶课”的实然后果是研究生追捧“水课”,在此指代研究生口中高频出现的“难度不高、作业不多、教师nice、给分友好”类课程,对应研究生趋易避难的选课标准,并非科学、统一的课程质量标准。趋向“水课”是出于研究生的理性选择,而非简单归因于盲目、懒惰、功利等消极学习态度。一方面,源自精力分配下的取舍。由表1可知,各高校教育学科学分制规定的课程比例高、课程总量多,课程平均约12门,第一学年每学期约5至6门课。更重要的是,课程以外的培养环节增多,不仅有实践活动、国际化活动、论文发表要求等规定,还有导师制及其科研任务并进。研究生难以保证多门课程同时高投入、高质量完成,于是主动打听、选择“水课”成为时间紧任务重下的无奈策略,以保障个别科目的高质量投入,同时兼顾学分要求。另一方面,实用主义的考量。“水课”的顺利通过与完成是可预期的,规避学业贻误等不确定性风险,有助于保障后续关于科研、升学、实习的时间规划以及奖学金获得。
总之,学分管理规定(中期时修完课程学分)有意将教学与科研区隔,设定先教学后科研的学习节奏,不利于教学与科研的内在统一,保障学分修读效率却折损学习质量,导致研究生选修的课程、修读的质量很难达到“科研预备”的预期效果。
2.学分构成的缺位:重教学轻学习,低估课外学习时间
学分制原型是卡内基学分,引入大学教育后历经适应性调整,从课内时间向课外拓展,1学分通常对应十余小时的课堂教学以及两至三倍的课外学时。例如一门3学分课程15周完成,则每周课堂教学约2.5小时和至少5小时课外自主学习或等量作业[16],并且课内和课外学时可转换,只需保障总学习量。但在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学分构成中,重课堂教学轻课外学习。制度层面,十余所案例高校的多项文本中均未提及学分内含的课外学时或学习量,只声明1学分对应的课内学时。访谈发现,许多师生不清楚1学分内含的课内外时间与质量要义,只掌握每周的课程安排。尽管研究生课程也设有预习、汇报等课外作业,但课内学时和课外学时并未作为整体课程设计。对学分制的认知阙如也为研究所证实[17]。这与学分制生长的教育制度环境有关。学分制诞生地美国,师生均重学习,研究生课程多是参与式研讨,学生是课堂的主体而非讲台下的听众,若不充分课外自学将难以胜任课堂学习。但日本大学重科研轻教学,课堂以教师讲授为主,课外学习流于形式。我国与之类似,早在学分制的试验阶段一项深圳大学的实证研究揭示这一点[5]69,实现学分制的教育使命(推动主动学习)需要系统的文化、环境和结构因素变革。
实践层面,研究生课外学习时间难以保证。为满足“研究生课程的学分原则上不超过2个”的规范,许多高校将专业课程压缩至2学分,以B大学为例,压缩大量3、4学分的课程,初衷是增加课程数量,扩大研究生知识面并且满足教师的开课需求,但导致研究生课程负担加重,课外学习时间不再充裕。吊诡的是,学分缩减导致课程课时减少,无法深度展开,实现教育效果反而更依赖课外自学。两个案例可佐证:①教师A备课认真,课程内容充实,但“从教多年一是很少有学生课后反馈和交流,二是很少有学生能跟上,系统地研读所有材料”。②教师B采用新型教学方式,效果突出,但是前期准备量较大,有小组合作、个人书面思考撰写和课堂互动展示。同学们表示“课程形式很好,收获很多,但不要再来第二次,拜托”。当研究生可支配的自主学习时间被课程和事务填满,不难预料他们学习积极性的降低,乐于接纳教师主导和主讲的授课形态[13]153。
然而,缺乏对课外学时的考量,不利于合理地教学规划。若纳入课外学时,基于既定学分标准,一门2学分课程对应32或36课时和至少两倍课外学时,则每门课每周至少6学时,而研究生第一学年集中选课每学期课程约5门以上,负担可想而知。问题是今日的研究生学习活动远不止课程,当研究生缺乏经典阅读与自主思考的时间,如何发现选题、琢磨研究?背离以基础学科尤其是人文社会学科为特色的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18]。
3.学分标准的迷思:教学与科研的分配参差
诞生之初,学分意指具体的教学时间,1学分对应数十小时的授课。但以时间为准绳过于绝对、客观,在实践中易于僵化,阻碍其他教育形态的运用,学分的内涵范畴由此扩展。这亦是学分发展的重大转向,从追求量的绝对时间转向追求质的学习内容时间[19]。新的学分兼容各式课程形态,授课、实习、实验、独立研究、线上教学等。引发的新问题是,关于非教学(课程)形态的学分数量如何分配?不同教学形态的学分质量(学时标准)是否一致?在美国,1学分对应15小时授课,2至3倍学时的实验、实践课程。类似地,日本的1学分内容基于授课、讨论、实习实践类型而区别,学时数量1∶2∶3[20]。但国内的研究生学分制中,科研学分占比约1/10,并且未阐明学时换算依据。这一困惑萦绕于研究生群体:“科研项目要完成一系列工作,花费时间比课程还多,为什么是1学分?”“科研工作和一些学术活动几乎没什么学分,但有的水课不怎么用课外投入也能得到3学分。”
学分的一项基本作用是充当学习计量单位,一定程度上使学习质量标准化,可流通、兑换。但在研究生教育的学分中,学分数量与学时投入不相匹配,不同教学形态间更缺乏相对等值及其解释,导致学分计量功能模糊,存在既不指向实际教学量也不指向实际学习量的情况。而学分量也是影响研究生学业规划和学习投入的衡量因素,当他们意识到学分收获与学时付出不对等时,倾向学分数量多但任务宽松的内容,回避学分数量少但任务重的选择,不利于发挥学分量对学生学习的调控和管理作用。
4.学分归旨的消弭:协调科研、教学、学习的自主性与灵活性式微
高校大多已实现以学分衡量学业进度和学位资格,但未必实现学分制的本质精神[21]。学分作为计量工具的表征下,以自由选课、自主学习与弹性学制为精髓,赋予学生选择学什么、什么时间学、怎么学并形成自己思想的自由,人尽其才。这正是高等教育理想所在,培养人自我决定、改造社会的能力,不只是适应传统、依附实用[22]。然而学分制的计划与实施不尽一致,仅一定程度上松动传统学年制的刚性管理,但远未抵达定位。
概观学分制的应用实景,赋予学生自主、自由的学习逻辑失灵:其一,学习进程无法自主。无论是中期考核前要求修满课程学分,还是学分需求和开课时间冲突“课程开设在特定学年和学期,我秋季的时候没空,春季没有这个课选不了的”,皆显示出学分制所谓的学习自由被框定在重重制度界限内。其二,学习内容与方式的程式化。在研究生学分中,课程模块占绝大部分,而涉及跨学科内容的自由选修学分、以科研或实践为学习方式的活动学分屈指可数,可见个体的学习自由建立在传统课程上。同时,课程模块的分类及其学分分配,割裂学习内容,未能促进在某一专业方向的纵深探索。其三,学习与学分的目标—手段置换。学分本是服务自主学习的工具,实践中却不乏“为上课而上课”的凑学分现象,以学生为本、实现学习自由的价值目标,异化为向上负责的管理目标[23]。不仅无益于学习效果,挤压从事感兴趣的科研活动时间,还可能阻碍对知识、对学术的内部动机,这是最令人警惕的。
综上,研究生学分制镌刻传统学年制的底色,研究生在学业规划、课程选择等诸多方面自主权受限[24],学分制的价值出发点与教育旨归已经悄悄陷落,沦为工具性管理、评价手段,抑制了学生的课外学习的积极性与自由度,削弱研究生对科研、教学、学习的自主安排与灵活整合,导致学生所获学分与其学习质量、个人发展的关系甚微,这是学分制长期以来遭受质疑的痛点[7]128。
三、研究生学分制失灵的成因
尽管学分制的各项规定有据可依,但落至学生学习中屡屡事与愿违。综观失灵表征,研究生学分制重教学、轻科研、轻学习,而研究生教育的科研、学习面向愈发显要。“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难以为继,研究生教育系统内的多股力量不再协调甚至冲突,学分制的失灵正根源于此。
1.研究生教育的理想形态:“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
伯顿·克拉克通过比较多国研究生教育体制,阐明“科研—教学—学习”的分析范畴,揭示研究生教育穿梭于科研与教学之间。现代高等教育发源于德国时,科研与教学统一的原则业已确立。按照洪堡的理想,高等教育以真理为追求,科研活动占据高等教育中心,师生是共同从事高深学问的伙伴,教学与学习皆服务于科研,有别于低层次教育——教师为传授学生封闭而有限的知识存在。而伴随知识生产的专业化,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催生出以教学为中心的大学或学院。教学内容的通识化、班级规模的扩张,使教学与科研拉开距离。英国分化出研究型与教学型高等教育机构,而法国则将科研置于专门的研究机构与作为教学场所的大学分开[25-26]。但是,科研与学习的统一理想并未丧失。教学本位只在第一级学位(本科阶段)普遍存在,而设立第二、第三级学位的研究型大学,科研①的合法性毋庸置疑,探索研究生教育的“科研—教学—学习”的连结体仍是众多高校的共同命题。
连结体寓含的价值理念是科研和教学不止相互渗透而且实质上兼容,这基于伯顿·克拉克对大学本质的体察,大学被定位为探究的场所,主要指向今日的研究型大学。教学与学习统一、服务于学术研究与创新,研究生们在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中学习或在以教学为基础的科研中学习。然而,大学与科研愈发卷入社会,伯顿·克拉克的考证表明,受市场与知识生产转型的驱动,“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受到多股力量分化,趋于瓦解。但作为探究场所的大学,最终需要、也有可能整合科研与教学,向连结体回归[25]221。然而,作为教学管理制度的学分制,却在连结体的瓦解中推波助澜。
2.连结体的结构张力:各行其是的三驾马车
学分制始用于本科教育,应用至研究生教育时留有惯性,倒向“教学”。但研究生教育与本科教育实质有别,本科阶段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并奠定知识基础,偏重课程学习情有可原[27]。而研究生处于专业教育阶段,不再追求通识教育,尤其学术学位硕士生以科研为实质主线、课程起辅助作用,研究生学分制处理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充分回应专业知识(教学)与专业实践(科研)。但当前研究生学分制的大部分学分仍在课程,延续本科学分制的内在逻辑。忽视“教学”仅是研究生培养的一维,导师负责制、自主学习也贯穿教育全程。研究生的角色显著转变,不只是课程学习者,而是导师的科研合作者以及独立的研究者。课程教学之外,他们面对大量的学术社会化锻炼——师门会、导师或院系级课题、联合培养、学术会议与交流、实践活动等。这些学习投入与产出却不为学分评定所认可,只作为学分含量极低甚至不计学分的必修环节或额外毕业要求而存在。学分制将研究生培养的各式目标(专业能力、跨学科能力、道德素养、数字技术/英语等国际化能力等)逐一投射在课程模块和课程学分上,课程量多而散,而忽视导师指导、科研活动、学校文化等隐性课程在涵养和锻炼这些素养上的实质作用。
由此,研究生的时间与精力被牵拉至多重面向:“课程讲的、导师要求做的,自己想做的,三驾马车各管各的,没在一条道上”“上课学的是一套,老师让我干的活是另一套,我自己想做的又是另一套”。伯顿·克拉克对“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的内在紧张早有意识,指出现代研究型大学内存在三股涌动源流:作为专门知识和职业基础的专业教育、以求知本身为目的的自由教育、科研的运作与训练领域[25]286。理论上,若研究生教育定位明确,区分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硕士生,则能平衡三者的优先次序。然而,教育学学术学位硕士的案例表明这一问题悬而未决,多线并行——教学、科研与自主学习同步异构,既隐含美国研究生教育的重课程形态,又混合英国的导师制色彩,略显“臃肿”。英国研究型大学蕴有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古典学术传统,专业基础在本科阶段业已完成,故研究生培养用小而精的导师制,重科研轻课程;美国则重课程轻科研,因本科教育重通识教育,专业教育有失扎实,以高质量的研究生课程为博士生研究筑基、预备,作为过渡学位[25,28]。相比而言,中国的研究生培养试图博采众长,教学与科研并重,近似英、美两种模式的结合却忽略它们各自起效的系统条件——适用于特定的师生规模、培养目标与学段衔接背景。
因此,“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内置三重结构:教学需求(课程)、科研需求(导师、奖学金规定、学校鼓励学术的氛围)、学习需求(学生兴趣)。“三驾马车”常常各行其是而非同行和接力。甚至学分制所倚重、赋予领跑职责的教学马车,变成学生实践中“不重要的事(指课程)先做完”“课程在我学习重心里占比最低,课程小于老师派给的任务、小于我自己的任务、大论文、小论文”。总之,研究生教育学分制所处的制度环境改变,学术学位研究生的整体教育环境以科研为取向,但学分数量设定、内容构成、分配及管理停留于重教学轻科研,未能适应研究生培养方式的变迁,疏导三驾马车间的紧张节奏。
3.连结体的内容张力:教学与科研的脱耦
学术学位研究生以科研为取向,但据此弱化“教学”一维有失牵强。“教学”不受研究生重视的关键在于,难以担起科研的地基,与科研相辅相成。“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实现的前提是科研与教学的实质兼容,但现实情境下,教学与科研的裂隙却日渐扩大。借助伯顿·克拉克的分析框架,现代大学教育中分化连结体力量的趋势有二:教学漂移和科研漂移。
教学漂移,指教学制度与知识背景脱离科研,重心移出科研指向教学。直接表现是赶课式学习,课程集训填满学习时间,将科研挤出。课多的情况下,选课难以结合科研需求,无暇大量阅读,也无暇付出科研选题与高质量写作所需要的充分投入,并且学生忙于课程阻碍导师较早介入指导,指导程度受限,最终呈现为研究生学习生涯前半段目标漂移,科研进展缓慢。另一深层原因是教学知识与科研需求的分裂,课程的使命与逻辑不再直接导向科研。首先,自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生源条件改变,硕士阶段课程承载着大众化教学的使命,愈发难将学生带往专业深处。教师的授课倾向也不再是高水平的创新和攻坚,而是照顾多数研究生的知识水平,或自降难度与标准以吸引研究生,满足开课人数,众多教授合开一门基础性拼盘课程的情况数见不鲜。其次,课程知识与科研所需知识的落差。现代社会知识更新急遽、知识总量规模扩张,在有限时间内积累专业知识体系愈发困难,教学知识试图把握必要、共同的内容,相对经典、全面和基础,与之冲突的是,知识生产与学术研究日趋精细化,能够组织学界共同研究的方案和问题意识消退,研究者只愿解其中片言只语或跻身前沿而开拓创新。因此,即使是专业细分领域的课程,也难以对接具体的科研问题、小众的创新发现,尤其在理工学科,前沿的学习材料往往是学术期刊而非课程教材。
科研漂移,指教育环境变化,科研活动逐渐撤出教学,重心移出教学指向科研。不止教学脱耦科研,科研一侧也疏远教学。一方面与现代大学变革有关,大学向服务多重目标的“多元巨型”机体进化[29],嵌入社会、接轨市场。在知识经济的影响下,外部力量的涉入加深,大学承接大量来自政府、企业等机构的科研项目,突破知识生产模式I的纯粹学科逻辑,应用性擢升[30]。而课程教学围绕学科主题,总体依照学科逻辑,二者的分歧难以弥合。科研项目与基础研究、与专业不直接相关,学术市场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蔓延为诸多国家的共象[31]。另一方面与科研知识的特性有关,科研的核心过程是探究,裹挟默会、实践、个性化知识,而教学以理论知识授受为主,不能替代科研。受访者反馈“课堂学习的知识都忘记了,用不上”“课程学习极少有收获”,教学所得知识若难以应用,往往被搁置、掩埋。与此区别,科研收获的是“活知识”,导师指导、合作实践等科研实训中,传递着缄默的学术知识、思维、方法与伦理,并且具有针对性、私人性,这是作为公共和显性知识渠道的课程难以实现的[25]268。
总之,学分制失灵的原因在于未能有效调控教学、科研以及学生自主学习的关系。诚然,课程质量问题、知识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导致科研与教学分离的关键成因,但学分制作为教育管理制度,未能适应研究生学习生态变迁以及学术学位硕士生的科研培养取向,不但无益于“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的通力协作,反而放任并催化了教学与科研的矛盾。
四、研究生学分制的改进
研究生学分制的失灵指涉双层面向:表层矛盾在于学分规定(规定、构成、标准)有失灵活与完备,最终学习自由的归旨式微;深层冲突则超越学分本身,与研究生教育的系统结构关联,即“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脱耦,学分管理未匹配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的连结体需求。因此,破解学分制失灵的根本策略在于,实现有意义的科研、教学、学习协同,减少人才培养的分力与耗散。
1.学分制所嵌入的研究生教育系统层面,有机整合“科研—教学—学习”
整合前,建议明晰各培养类型特色。国内研究生分为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但学术学位内部也高度异质,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生仍在少数,造成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因顾及多数学生,专业课程偏基础、学分分配重课程,未充分接轨研究性人才培养,与本科教育的区分度不高,这是大型研究生院的常见失误[32]13。英美国家通过细化研究生培养类别化解这一问题[32]321。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生培养分三类八个水平,根据所需证书、文凭、学位水平不同,学分要求及其内容规划匹配其定位。对于就业或提升学历的类型和水平,课程学分占绝对比例,而对于通往博士学位的研究型硕士学位和哲学研究硕士学位,科研类学分大幅提升[33],针对性的学分配置调和了科研与教学的冲突,满足不同群体需求且保障质量。类似地,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也因授课型硕士与研究型硕士的性质差异,调整课程与科研学分配比[34-35]。哈佛大学采取另一种灵活方式,专业课程占约一半学分,其余自由,任选科研实践类学分或课程,因人而异[36]。部分国内高校已通过另设硕博连读、直博生的学分规定回应这一点。
整合实施中,一是深化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与学习,以研带教。研究生的学习不囿限在课堂,学术研究过程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混合环境。学校、学院举办的诸多学术活动、课题、项目合作中,涉及校级跨学科的教师、院系级不同专业方向的教师指导,而基层环境中导师为核心的师门/研究组,更是导师指导、教学相长的常见场域。若有意识地规范上述科研过程中的教学,将其投入时间与成果合理地纳入教师和学生的考核评价,有利于保障教学与科研的融合,实现科研群体与教学、学习群体的联结。伯顿·克拉克也强调将大学内部的系、科研小组等实践基层纳入教学环境[25]243。二是改进以教学为基础的研究与学习,以教促研。课程是科研的基础,引领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进入研究,即使是专业基础课程,也应区别于本科课程,具有研究性,发展学术思维、锻炼研究写作。但当前的专业教育课程许多较为基础或泛泛,知识的生硬输入不能服务于科研。少数以教学为基础实现科研需求的课程是:①提升学术能力的课程,例如特定研究方法、学术写作类,这些课程备受赞誉、受访者枚举颇多,针对性解决研究生学术技能欠缺、学术经验不足的困扰,实现课程与导师互补。②激发学术兴趣、拓展思维的课程,通常是选修的理论或跨学科课程。这类课程虽不直接导向科研,但助长了学生的科研认同与兴趣,唤起学生的科研热情与投入。以知识为目的的课程与现代科研工作方式的脱节不可避免,但点燃科研热情与志趣的课程始终内蕴生命力。
2.学分管理规定与技术层面,合理规划学分数量,完善学分的认定、转换与衔接
首先,调整课程学分量并放宽完成时间,使学习更灵活而不是拥挤和紧张。课程学分过多会抑制学习质量与科研投入,浙江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三所高校的学分量均约25个(比其余案例高校少近三分之一),受访者表示:“修读课程时间不多,能保证对主要课程的投入,后续时间会旁听感兴趣的课程并且导师能很早介入,带领做科研。”相比其余课程学分多的学校,课程少而精是保障他们科研投入、师生合作数量与质量出色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时,课程修读的时间弹性也不可忽视,中期考核等规定使课程节奏过于集中,不利于教学与科研的结合,“选修的时候以为课程是课程,科研是科研,二者没有关系”,也难以完成教学所需的阅读或自主学习。因此,学分修读的进度应综合考虑课程的整体学时及其他学业活动,只需保证学生在学位允许的最长年限内完成。
其次,推进科研创新的学分认定。这有助于不减少总学分、维持培养规定的情况下释放一些研究空间。研究生教育以科研为主线时,主修科目相应减少并增加选修科目或研究训练[26]115。已有少数高校走在实践前沿,鼓励多元类型的创新成果冲抵学分并设立一定数量上限[6,37],案例表明,这一举措使研究生的综合实力明显提升[38]。但创新学分认定有其难点,学分的优势在于可衡量,课程学时易测,科研活动不然,这也是诞生伊始便萦绕学分制的非议“重在教育时间而非教育质量”[39]。为改变单一的学时学分窘境,美国联邦政府2011年重新定义学分,将能力注入学分[40],这是美国模式向欧洲模式(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的借鉴,以学习成果为导向而非授课时间为准绳,以发展一个囊括能力因素有望广泛用于职业教育或培训的学分体系。由此,创新学分的认定可以借鉴基于能力的欧洲学分制。但考虑公平与多元发展,创新学分应作为可选而非必选项,一些现行改革以必修学分强制学生参与特定科研活动(如数十次讲座),恐陷入制度僵化而流于形式的泥淖。
再次,优化学分的衔接与转换。学分制内含免修免听制度,适用于学业基础好、学习能力强、通过自学或先修已达到课程要求的学生。但这一条例主要应用于公共外语课,专业课参与极少。这忽略了具备前置学历或相应专业背景的学生,因为研究生课程的学分设置中,许多旨在弥补专业基础。已有高校针对缺乏学科背景的学生增加必修课程,实质也是回应这一诉求。目前国内升入硕士的大学生比例已占据相当规模,有必要根据不同培养类型的衔接,完善本科与研究生学段、不同高校间的学分互通、转换,既维护学生的学习自由、保障自主学习,又降低教育资源浪费。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牛津大学等名校,课程转换学分占比可多达1/2[41]。
3.学分及其学习文化层面,增进多方教育主体的学分认知,焕发学分制的价值与理想
在众多教育决策与教育行政人员、教师、学生眼中,学分被看作管理和评价工具,对其内涵、旨趣及现实作用一知半解,因此并未充分觉察学分相关的各项规定通过调配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注意力,也干预到教与学的质量。更重要的是,忽视学分制相比学年制的核心奥妙:以灵活、弹性的方式保障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激发自主学习,实现多元、个性化的人才培养。当教育主体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时,也就丧失了学分赋予的主动权。因此,学分制改革既需要制度调整也需要文化回归。在依据学段、学位类型调适学分规定的同时,亟待教育管理者、师生共同树立全面、系统的学分认识,真正实现学分对个体学习自由的维护与解缚,主动达成课内外学习要求与质量目标。
参考文献
[1]""""""" 有本章. 大学の社会的機能—―総論: 学問生産性の中の教育機能[J]. 兵庫高等教育研究, 2019(3): 105-117.
[2]""""""" 苑津山, 张傲冲, 吴亚雯. 中国高校学分制高阶探赜: 学分制调控功能的立意、变迁与时代因应[J]. 江苏高教, 2022(5): 74.
[3]""""""" 丁洁琼. 减负与加压之间: 本科课程数量的变迁——学分制是如何失灵的?[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0, 41(3): 129.
[4]""""""" 博耶. 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演讲[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107.
[5]""""""" AGELASTO M. Educational transfer of sorts: the American credi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Comparative education, 1996, 32(1).
[6]""""""" 周清明. 中国高校学分制研究: 弹性学分制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7]""""""" 芦苇. 美国学分制述评[J]. 现代教育科学, 2010(6): 127.
[8]""""""" 杨劲松, 江波, 钟之阳. 高等教育国际化视野下的学分探析[J]. 中国高校科技, 2018(5): 9.
[9]""""""" 蔡先金, 宋尚桂. 大学学分制的理论与实践[M].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6.
[10]""""" 陈学飞.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50年(1949—1999)[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9: 1781-1783.
[11]""""" 周建明. 中国人民大学决定今年入学的研究生试行学分制[N]. 光明日报, 1985-10-03(2).
[12]""""" 刘元芳, 林莉. 研究生教育中引入学分制的实践与思考[J]. 现代教育科学, 2003(7): 56.
[13]""""" 薛成龙, 邬大光. 论学分制的本质与功能——兼论学分制与教学资源配置的相关性[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7(3).
[14]""""" 冯向东. 推行学分制: 教学制度与观念的深刻变革[J]. 高等教育研究, 2003(6): 60-61.
[15]""""" RESTREPO ABONDANO J M. Managerial consequences of credit system introduction: a Colombian case[J]. Cuadernos de administración, 2008, 21(37): 2.
[16]""""" American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 academic rules and regulations[EB/OL]. (2023-12-01) [2023-12-01]. https://www. american.edu/provost/undergrad/undergrad-rules-and-regulations.cfm.
[17]""""" 禹常胜. 基于卓越绩效的研究生学分制管理研究[D]. 昆明:云南大学, 2020: 68.
[18]""""" 唐检云, 刘聪科. 研究生成才的内在要素及其培育[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6(9): 41.
[19]""""" 舘昭. 改めて「大学制度とは何か」を問う[M]. 東京: 東信堂, 2007: 65-66.
[20]""""" 覃丽君, 陈时见. 欧美大学学分制的比较与借鉴[J]. 教育发展研究, 2013, 33(11): 71-72.
[21]""""" 韩磊磊, 源国伟. 中国高校学分制30年——大学教学制度改革讨论述评[J]. 高教探索, 2008(4): 64.
[22]""""" 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 等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49,105.
[23]""""" 郝龙飞, 操太圣. 高校“水课”问题产生的制度归因——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视角[J].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2, 10(2): 107.
[24]""""" 张群. 教育学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研究——基于学生体验视角[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22: 43.
[25]""""" 克拉克. 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M]. 王承绪,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26]""""" 克拉克. 高等教育新论: 多学科的研究[M]. 徐辉, 等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27]""""" 叶飞, 尹珺瑶, 田鹏. 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实践向度循证研究[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2(11): 18.
[28]""""" 克拉克. 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M]. 王承绪,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134.
[29]""""" 克尔. 大学的功用[M]." 陈学飞, 译.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13-17.
[30]""""" 博克. 走出象牙塔: 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 徐小洲, 陈军,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156-159.
[31]""""" 范德格拉夫, 等. 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
较[M]. 王承绪,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176.
[32]""""" CLIFTON F, HAWORTH J G, MILLAR S B. A silent success: master’s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33]""""" UCL Academic Manual. Section 4: types of qualification [EB/OL]. [2023-12-01]. https://www.ucl.ac.uk/academic- manual/chapters/chapter-7-programme-and-module-approval-and-amendment-framework/section-4-types#4.4.
[34]""""" University of Oxford. Introducing our courses[EB/OL]. [2023-12-03]. https://www.ox.ac.uk/admissions/graduate/cour ses/introducing-our-courses.
[35]"""""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Master of Liberal Arts[EB/OL]. [2023-12-03]. https://mla.stanford.edu/program/program-stru cture-requirements.
[36]"""""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Master’s program of education leadership, organizations, and entrepreneurship [EB/OL]. [2023-12-03]. https://www.gse.harvard.edu/degrees/ masters/program/eloe.
[37]""""" 吴平. 完善高校学分制的思索[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159.
[38]""""" 王健, 卜小芳, 孙琳, 等. 基础医学研究生学分制条件下的双导师制培养——以安徽理工大学为例[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6(4): 319.
[39]""""" 靳贵珍. 试析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学分制及其借鉴意义[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3): 23.
[40]""""" 钟金梅. 美国大学学分制的演变研究(1869—2011)[D]. 金华: 浙江师范大学, 2022: 43.
[41]""""" Department for Counting Education. Credit accumulation and transfer scheme, and qualification frameworks[EB/OL]. (2023-12-04) [2023-12-04]. https://www.conted.ox.ac.uk/ about/cats-points.
(责任编辑" 黄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