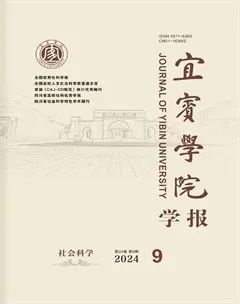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现状检视与内涵界定-
摘要:把握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界限的核心在于准确理解和界定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在防卫过当司法认定中,存在着重损害结果轻防卫行为的“唯结果论”,以及防卫限度条件中的“明显超过”常常被虚置等认定偏差,基于1997年《刑法》修改正当防卫制度的立法目的及更好地保护防卫人的合法权益的政策立场,在认定“必要限度”时,立足必需说的立场,防卫行为应是最必要的有效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限度;且这只是防卫行为认定的最低限度,超过“必要限度”并不能认定防卫人属于防卫过当,还要防卫行为达到“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程度,才能认定为防卫过当。结合防卫行为对侵害人人身安全可能造成的损害程度进行等级划分,“明显超过”应是至少高出防卫必需限度的一个危险等级以上的行为。
关键词:防卫过当;必要限度;明显超过
中图分类号:D924.1
DOI:10.19504/j.cnki.issn1671-5365.2024.09.08
近年来,随着“余欢案”“于海明案”等案件的出现,正当防卫制度在实践中的价值和问题日益受到刑法学者和社会大众的关注。作为法律赋予公民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权利,如何确保在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认定上实现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是正当防卫认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把握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界限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和界分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基于对此问题理解上的偏差正是导致司法实践产生认定误差的根源,因此需要对“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内涵作出合理界定。
一、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司法认定的现状检视
关于正当防卫的限度问题,1979年《刑法》规定为“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1997年《刑法》将其修改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1997年《刑法》一方面是在“超过必要限度”前增加了“明显”二字;另一方面是将“不应有的危害”限定为“重大损害”。可以看出,1997年《刑法》明显放宽了公民行使防卫权利的限度条件,即只要是为了制服不法侵害所必需的防卫行为,在性质、手段、强度和损害后果上没有明显超过相对的不法侵害,或者虽然造成的损害明显超过了不法侵害,但是造成的实际损害尚没有达到重大程度的,都属于正当防卫[1]197。修改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适当放宽正当防卫实施的限度条件,进一步保障公民在遇到或面临不法侵害的时候,敢于积极对抗不法侵害,制止不法行为,保护合法权益。然而,在正当防卫认定的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一些偏差,司法人员在对防卫的司法认定上态度较保守,在某种程度上不敢认定为正当防卫以保护公民的防卫权,特别是在当防卫行为导致了实际的损害后果时,即使符合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也容易被判定为构成防卫过当,甚至在有的案例中直接被认定为犯罪行为,这使得正当防卫部分法律规定被长期搁置,处于“休眠”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僵尸”条款,[2]导致了正当防卫制度的虚化[3],影响了正当防卫制度积极保护公民对抗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利的作用的发挥。
我国司法实践对正当防卫的限度掌握过严,“唯结果论”的认定态度依然有广泛影响,一旦防卫导致重伤或死亡的结果,即便行为人行为的防卫性质被肯定,一般也要被认定属于防卫过当,而且对过当的判断往往正是根据实际损害结果的严重程度做出的[4]。具体而言,司法部门在把握防卫的限度条件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注重造成“重大损害”条件而忽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条件,即通常考虑到防卫过程中发生了损害后果,特别是发生伤亡结果时,便将其认定为防卫过当。有学者通过对722份判决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司法判决中有83.24%的案件在记述了行为人进行防卫导致不法侵害人伤亡的后果后,接着就指出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构成防卫过当[5]。
二是通过某些因素的简单比对或利益的衡量就认定为防卫过当。主要表现为:(1)将防卫行为的强度与不法侵害的强度进行比较,如果防卫行为的强度明显超过不法侵害的强度,或者在不法侵害程度减弱或丧失以后,防卫人不停止而继续追击的,就认为防卫行为过当;(2)在防卫人进行防卫要保护的法益或不法侵害人实施侵害可能导致的后果与防卫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损害结果之间进行衡量,如果二者之间悬殊,就认为构成了过当的防卫;(3)对防卫所采取手段和不法侵害手段进行衡量,如果不法侵害人“未持械”,而防卫人持械防卫①,或者认为防卫人能采取更为轻缓的方式却未采取的,即构成过当防卫[6]。
三是防卫行为限度条件中的“明显”常常被虚置或认定模糊。1997年《刑法》对防卫行为限度条件“超过必要限度”增加规定了“明显”的程度要件,意在放宽防卫限度条件。但在很多情况下,司法机关往往仍是经过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的比较后,认为防卫行为超过了不法侵害,再结合造成了重大损害后果,便认定构成防卫过当,而忽略了防卫行为限度条件中的程度条件“明显超过”,或者不敢判决构成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正当防卫。即使在判决书中认定“明显超过”的条件时,也只能完全根据法官的自由裁量,标准把握模糊不清。如在赵宇正当防卫案②中,赵宇在看到他人人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出手制止,并未使用任何器械或刀具,徒手防卫,只是朝对方腹部踩了一脚,造成的伤害结果是被害人重伤的后果,在处理时,公安机关最初以赵宇涉嫌故意伤害罪进行立案,在侦查后又以涉嫌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可见在侦查阶段,对赵宇属于制止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未予任何肯定。而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检察院虽然肯定了赵宇的行为属于防卫,但认定其属于防卫过当,因此作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本案最终由福州市检察院审查后认定赵宇的行为属于防卫,尽管超过了必要限度但程度并不明显,不属于防卫过当,并指令晋安区人民检察院作出绝对不起诉决定。最终,本案中赵宇的行为被肯定为正当防卫,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在本案中得到了实现,对其他案件的认定也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但通过本案的处理过程对实践中防卫限度条件把握过严的问题可窥一斑。在本案中,防卫人在防卫手段上未使用器械,在损害后果上仅造成一人重伤后果,认定过程都可谓一波三折,更不用想象实践中对很多防卫过程中使用了器械,造成侵害人死亡或多人死亡结果的案件,在认定时更难以被认定为正当防卫了。
二、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概念厘清
如何判断防卫行为有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不仅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不一,在刑法理论上也是观点纷呈。学者们在进行讨论时,用语和指向亦存在差异,主要有“必要限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及“防卫限度”等,虽然这些不同表述所指的中心问题是同一的[7],但其所涵涉的范围不尽相同,在进行理论梳理时首先应予区分。
(一)防卫限度与防卫行为限度
防卫限度是正当防卫权利合法实施的界限,是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界分的重要条件。无论是1979年《刑法》规定的“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还是1997年《刑法》规定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在防卫限度的认定上都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防卫行为的限度,二是防卫结果的限度。在认定正当防卫是否过限时,防卫行为限度和防卫结果限度二者缺一不可,只有防卫行为过限同时造成了防卫结果过限时,才能认定构成防卫过当。因此,防卫行为限度是界定防卫限度的重要条件之一,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进而在界定防卫限度时,应当将防卫行为的限度和防卫结果的限度两者区分开来,如果不加区分的做与单一条件说类似的一体化理解,那么将会再次陷入利益衡量的窠臼,导致把防卫结果当作界分防卫是否过当的唯一依据,进而模糊正当防卫权利行使的界限。
(二)防卫行为限度与必要限度
结合1979年《刑法》 规定,防卫限度规定中的防卫行为限度即“必要限度”,所以在不区分防卫限度与防卫行为限度的情况下,防卫限度就被理解为了“必要限度”。而1997年《刑法》将防卫行为限度改为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从字面上看,仅是新增了“明显”两个字,但究其实质,这样的立法修改背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并将对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根据1979年《刑法》正当防卫的法条,防卫行为的限度边界是一条线——也就是“必要限度”划定的那条线。它既是达到制止不法侵害实现防卫效果的防卫行为强度的最低线,也是界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防卫行为强度的最高线。而根据1997年《刑法》的规定,防卫行为的限度条件就不再是单纯的一条线,而是由上限和下限两个界线形成的一个权利幅度,具体而言,其底线仍是“必要限度”所确立的那条线,而处于其顶端的上限则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所确立的一条线。[8]因此,在界定防卫行为的限度时,既要合理把握防卫行为的最低限“必要限度”,还要强调防卫限度的程度条件“明显超过”。
三、“必要限度”的理论聚讼与合理界定
(一)“必要限度”的理论聚讼
针对如何把握防卫行为的“必要限度”问题,刑法理论上存在“基本相适应说”“必需说”和“相当说”的观点争论。按照基本相适应说,限度以内的防卫要求防卫行为在性质、手段、强度、结果以及保护法益等方面都要与不法侵害大致保持相当。因为该学说过于严格地限制了正当防卫权利的行使,不利于保障防卫人的合法权益,使得该学说备受质疑。要求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大体相当,使得紧急状态下的防卫行为变成了精细的衡量过程,对防卫人的要求无疑是过于严苛的,等于要求防卫一方承担了较多的注意义务和法律风险,而且不法侵害行为的实施是一个逐步发展、动态变化的过程,侵害的手段、方法和强度大小随时都在不断变动中,要求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大致相当也就是需要防卫人精准判断并预测侵害行为后续发展的整体情况,这显然脱离了防卫的具体情况和实际要求,背离了正当防卫权利设立的初衷[9]。
必需说主张判断时主要看所采取的防卫行为是不是为制服不法侵害、保卫合法权益所必需。只要是必需的防卫行为,就认为是防卫必要限度以内的正当行为。同时,为了避免必需说可能导致的过于放大正当防卫权利的风险,持该学说的学者对此做了一定的限制,在保护法益和损害利益之间也要进行一定的权衡,二者不能过于悬殊,也就是要求不能为了保卫微小的权益而导致不法侵害方重伤或者死亡等非常严重的后果。[10]对于必需说,学者们也存在一定的疑问。即如何界定“必需”,如何判断“必需”,必需说因为过于抽象,无法给出具体的标准,会导致其内容具有不确定性。
结合基本相适应说和必需说存在的不足,相当说对以上两种学说进行了折中,这也是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即在确定必要限度时,一方面须以是否为制服不法侵害所必需作为防卫行为限度的首要考察标准,与此同时,对防卫利益的性质及其可能遭受的损害程度进行考察,衡量防卫行为和不法侵害在法益的性质、损害的程度等方面是否大体相当[11]。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作为通说的相当说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主要在于相当说在本质上仍是基本相适应说,根据相当说的观点,在判定防卫行为是否为超限的防卫过当时,基本相适应说仍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就造成相当说在某种程度上同样避免不了基本相适应说的固有缺陷[12]。而且,根据相当说的观点,在判断行为限度和结果限度的过程中对同一个客观结果性要素进行了重复评价,从而放大了客观损害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造成司法实践中界定防卫行为限度困难的规范诱因[13]。
基于基本相适应说的固有缺陷及其与必需说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长期坚持相当说导致的正当防卫司法认定的实践困境,相当说作为通说的地位越来越受到质疑,必需说受到更多学者的支持。还有学者试图另辟蹊径,提出了“最低强度的有效防卫说”[14],认为“必要限度”就是最低强度的有效防卫行为的强度,但就其本质仍是必需说的立场,且“最低强度”的限制有进行事后判断的嫌疑,不利于放开防卫人的手脚,解除防卫人的顾虑。
在“必要限度”的认定上,必需说更为合理。首先,必需说符合强化公民正当防卫权的立法目的。受当时立法指导思想的影响,以及为了防止滥用正当防卫权等方面的考虑,立足于“宜粗不宜细”立场的1979年《刑法》在关于防卫限度的法律规定上较为原则和笼统,造成实践中在把握正当防卫适用条件时过于严格[15]197,严重约束了公民的防卫权,使得公民在面对不法侵害时不敢防卫。基于此,1997年《刑法》对正当防卫制度特别是防卫的限度作了较大的修改,并同时规定了特殊防卫权,其立法的旨意就是要放宽防卫的限度条件。而基本相适应说和相当说显然不能实现此立法目的,只有坚持必需说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公民的正当防卫权,保障防卫人的合法权益。且相当说本身就是立足于我国1979年《刑法》规定而形成的认定防卫行为的通说,在司法实践的检验中其弊端已越来越明显,在我国刑法已经作出较大修改的情况下,仍固守相当说的立场必然会束缚公民正当防卫权利的行使,与我国刑法的立法修改的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不相符。
其次,必需说符合鼓励正当防卫“以正压邪”的实践需要。基本相适应说和相当说在进行比较时,容易脱离防卫实施的动态环境,对防卫人进行冷静地事后评判,进而导致司法人员在认定防卫过当时的“唯结果论”,不当缩小了正当防卫的空间,其后果是公民在面临不法侵害时要么是不敢防卫,要么是奋起反击构成防卫过当受到惩罚。而实际上,公民在面临不法侵害进行反击时,如果想要制止不法侵害,往往需要通过采取更为严重的暴力才能实现,如果采取基本相适应说和相当说会让防卫人受到惩罚,导致“正不压邪”的怪象出现。因此,在面临不法侵害时,应结合不法侵害的具体情势,以防卫人达到制服对方侵害效果所必需采取的行为为界限,给予防卫人更多的宽容,才能纠正当前司法实践在认定防卫行为时存在的误区和偏差,真正体现正当防卫制度“以正压邪”的价值。
再次,就必需说所受的不易操作的质疑而言,必需说在对防卫是否过限进行衡量时,并不是只讲抽象的原则,而不考虑具体的操作。实际上,其更强调立足不法侵害的具体情境,在弄清案件所有事实之后再进行综合衡量,而不能仅关注行为强度、行为方式或造成后果等一个或几个侧面。同时,就必需说中何谓“必需”,如何判断“必需”不甚明确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必需说的研究尚不够深入,这正是需要进一步深化必需说研究的理由,而非否定必需说,对其避而不谈的理由。
(二)“必要限度”的合理界定
立足必需论的立场,“必要限度”应是指有效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防卫行为限度。
1.“必要限度”是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限度
正当防卫是国家赋予公民在面对合法权利遭到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所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保卫合法权益的权利。根据刑法的规定,正当防卫是国家鼓励公民“以正对不正”,保护合法权益的一项积极的防卫权利,而非一种“不得已”的应急措施[16]129。因此,即使在能通过逃跑或躲避等方式避免不法侵害的,也不应以行为人采取了直接对抗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而认定为防卫过当。如田某故意伤害案③中,田某系一酒楼厨师,2007年12月15日,田某与另一厨工陈某因琐事发生争执。当晚10时30分许,陈某找来郑某、魏某及蔡某,授意三人殴打田某,同时要求三人不要打得太重。郑某等三人即到村口,拦住田某拳打脚踢。田某即掏出平时做菜用的雕刻刀,刺向郑某和魏某,然后转身跑回酒楼。经鉴定,郑某和魏某构成重伤。法院在认定时认为“被告人田某在受到一般性殴打且有机会躲避的情况下,持锐器刺伤两人,致两人重伤,其行为虽具有防卫性质,但其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属于过限防卫,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在本案中,田某夜晚遭到三人拳打脚踢的情况下进行防卫,不能以田某有机会躲避没有躲避,而采取直接对抗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而降低对其防卫行为的认定标准,进而追究其刑事责任。
2.“必要限度”是有效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限度
为了鼓励公民敢于对抗不法侵害,保卫相应的合法权益,基于必需说的立场,“必要限度”应达到有效制服不法侵害的程度,也就是说,防卫人采取的防卫行为应足以能制服对方侵害。具体而言,防卫行为首先应足以制服已经展现出的、正在进行中的不法侵害。如果是多个不法侵害人实施的共同侵害,防卫人的防卫行为应是足以制止所有共同侵害人的防卫行为。同时,基于不法侵害的实施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防卫行为应足以制止不法侵害人可能实施的进一步的不法侵害。因此,在实际认定防卫行为过限与否时,应立足防卫人的角度设身处地,结合不法侵害人的人数、不法侵害实施的具体环境、手段等因素具体进行判断。
3.“必要限度”是最必要的有效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限度
基于必需说有可能会造成过于放宽防卫权的限度,造成防卫权滥用的担忧,从限制防卫行为造成过度损害的立场出发,在确定防卫的“必要限度”时,应作出一定的限制。在存在几个可供选择的制止不法侵害的防卫措施时,防卫人应当选择其中强度最低、造成损害最小的方式进行防卫[17]461。即如果能够不使用武器进行防卫的,就不应使用武器;如果能通过不使用致命武器进行防卫的,就不应使用致命武器。当然要求防卫人以最低限度的有效行为制止不法侵害,应是以防卫人在行为当时能够有时间、有机会进行选择为前提的。因此,需要注意的是,在判断是否防卫必需时,应立足不法侵害和防卫的具体情境,结合防卫人的具体状况,考虑一般大众的行为标准进行具体判断。如果时间紧迫,防卫人在当时来不及选择,或者防卫人在当时基于极端恐惧等影响不能选择的情况下,不能苛求行为人只能以最低限度的防卫行为进行精确防卫。如在张那木拉正当防卫一案④中,首先,从事件的最初起因看,在毫无征兆和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周某强等一行四人突然闯进张那木拉的个人住所,且都提前准备了侵害工具,其中有两人分别持长约50 厘米的砍刀,另外两人中一人持铁锹,一人持铁锤,而在当时,张那木拉并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和防卫准备;其次,从事件的具体过程看,周某强等人在闯入屋内后,直接对张那木拉进行拖拽,在后者转身向后挣脱时,随即又使用所携带的凶器砸砍后者的后脑部,在这中间,其中一侵害人丛某又持铁锹击打后者的后脑处。可见,不法侵害已严重威胁张那木拉的生命安全,此时,张那木拉随手在茶几上抓起一把尖刀进行还击是必要的;再次,从事件的进一步发展看,张那木拉到屋外后,看到张某2手持铁锤还与其兄张某1打在一起,总体来看,这时不法侵害仍未停止,其行为仍处在防卫的过程中,为了防止其兄被殴打,张那木拉用随手从门口处拿到的铁锹将尚在挥舞砍刀的周某强两次打入鱼塘里,致周某强轻伤,其行为对制止不法侵害是有效的也是必要的;最后,从克制防卫行为方面看,在持尖刀捅刺了陈某2新,后者退到外屋并倒地,周某强、丛某也跑出屋外后,张那木拉将尖刀放回原处;在其兄张某1将张某2也打落水中后,张那木拉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并且在原地等待,都表明其在实施防卫行为时克制的态度。因此,在本案中,虽然造成了一名不法侵害人死亡的后果,但在面临不法侵害人四人持械并击打重要部位危及生命的情况下,张那木拉随手抓起尖刀捅刺进行防卫是最必要的有效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并未超越防卫的行为限度,不能认定为过当防卫。
尽管“必要限度”要求防卫行为应是最低限度的有效防卫不法侵害的行为,但是根据刑法的规定,这只是防卫行为认定的最低限度,超过“必要限度”的行为并不能直接就被认定为防卫过当,还要防卫行为达到“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程度,才能认定为防卫过当。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界定“明显超过”?
四、“明显超过”的内涵界定
虽然我国1997年《刑法》将防卫行为限度修改为了“明显超过”,但刑法学者过去对此要么采取回避的态度,要么简要述之,如同隔靴搔痒,其直接影响是无形中消解了1997年《刑法》对防卫行为限度补充增加“明显”的程度规定的重要意义,结果导致司法实践在具体操作中往往忽略“明显”的要求,依旧按照旧刑法规定来界定防卫过当条件,最终使得防卫过当的认定发生偏差,变成了防卫与不法侵害之间两个行为强度的大小比较、防卫保护利益与不法侵害损害利益的法益衡量、防卫所致的损害与不法侵害可能导致的损害之间的简单比对,影响了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的合理认定。弘扬社会正气,倡导见义勇为,鼓励公民积极行使防卫权,纠正司法中对防卫行为限度掌握过严的偏差,应充分发挥刑法规定的防卫限度中“明显超过”之条件的作用。
(一)“明显超过”的比较对象
以往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在认定防卫行为过当行为总是简单地把防卫行为和不法侵害放在一起比较,并造成了实践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明确“明显超过”的涵义,首先应明确其与之比较的对象。根据现行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法条规定,通过对该句的结构分析,防卫行为是该句的主语,“超过”是该句的谓语,“明显”作为状语修饰谓语动词,而该句中谓语其所指向的宾语是“必要限度”。结合上述对“必要限度”的阐述,也就是说,防卫行为明显超过了有效停止不法侵害的最低限。换句话说,在确定防卫行为过限程度是不是达到“明显”程度时,“拿来比较的双方应该是案件中的防卫行为与必不可少的防卫行为,而不是案件中的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18]。因此,在把握防卫行为限度,界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行为时,不但是防卫超过了所必要采取的防卫行为的最低限度,而且超出程度达到了“明显”的程度。反过来说,既不能将一超出“必要限度”的行为认定为防卫过当,更不能简单地将在强度上高出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就认定为防卫过当。
(二)“明显超过”的规范内涵
根据汉语词典的解释,“明显”是指“清楚地显露出来,让人容易看出。”因此,“明显超过”即指超过最低限度的幅度比较大,让人容易看出。其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明显”的表现;二是“明显”的判断。
1.“明显”的表现
何谓“超过”的幅度大?即多大程度上超过必要限度才构成“明显超过”?解决此问题的关键是需要找到一个对行为的衡量单位。尽管行为的实施主体、实施对象、实施方式等各不相同,但是都呈现为对其它法益造成损害的危险程度,并与一定的实际损害结果表现出一定的对应关系。结合防卫行为来看,其通常表现为对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权益的损害,防卫行为的强度正好与其对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权益所造成的危险程度相对应。进一步而言,根据人身安全可能受到的损害程度进行划分,可以将防卫行为的强度根据严重程度由轻到重分为三种情况,即足以致人轻伤的危险、足以致人重伤的危险及足以致人死亡的危险。基于此前提,“明显超过”应至少高出防卫必需限度的一个危险等级以上。即根据不法侵害的具体情形,防卫行为最低限度为足以致人轻伤风险的行为,则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是达到致人重伤危险的行为,并造成他人重伤及以上的损害后果;如果防卫行为最低限度为足以致人重伤风险的行为,则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是达到致人死亡的危险的行为,并造成他人死亡的损害结果。如在朱凤山故意伤害案⑤中,齐某因不满妻子提出离婚并带着女儿回娘家居住,进而酒后到朱家进行骚扰滋事,其主要的意图是不愿意离婚,想和朱凤山女儿和好并继续维持婚姻。虽然其在闹事过程中实施了投掷瓦片以及后来与朱凤山进行撕扯等行为,但其对后者人身权益的伤害从程度上讲只是轻微的,且后者已经报警,尚有进一步周旋和等待的余地,朱凤山不需要采用伤害强度大的行为就可以实现防卫的目的,但朱凤山却在先使用铁叉阻拦的情况下,又使用宰羊刀进行防卫,并在双方撕扯的过程中直接向齐某胸部等要害部位进行捅刺,进而造成齐某死亡结果的发生,其行为已超出了防卫必需限度的一个风险等级以上,属于明显超出了有效防卫的必要限度,构成防卫过当。
需要注意的是,在不法侵害伤害程度不明或有进一步伤害风险的案件中,在确定防卫必需限度和“明显超过”标准时应立足有利于防卫人的立场进行认定。如在前述赵宇正当防卫一案中,赵宇在看到李某将邹某摁倒墙上并殴打邹某头部时上前制止,并从背后拉拽李某,致使李某倒在地上。但此时危害行为并未被完全被制止,李某站起来后还想殴打赵宇,并扬言要找人“弄死你们”,可以看出,此时李某有进一步实施不法侵害的可能,且不法侵害程度并不明确,即使是徒手的情况下,也不排除有造成重伤及以上侵害后果的风险。因此,赵宇为了制止不法侵害,徒手将李某推到在地,并朝李某腹部踩一脚的行为,结合当时防卫的具体情境,是连续的防卫行为,也是必需的防卫行为,即使客观发生了不法侵害人重伤的后果,也不构成“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过当。再如前述的田某故意伤害案中,尽管雇人伤害田某的陈某在事先授意郑某、魏某、及蔡某在伤害时不要打得太重,但田某对此并不清楚,三人在夜晚轮番对其身上、头上进行拳打脚踢,立足田某所处的情境来看,不能就此认定其属于伤害程度低的“一般性殴打”,结合具体侵害情形,当时蔡某抓住田某的头发“压倒在地,用膝盖在身上顶,用拳头在脸上、头上打。”在郑某去踹田某肚子时,田某持随身携带的雕刻刀进行还击,之后魏某也朝田某扑过来,田某有用刀捅刺了魏某,在蔡某又准备上前殴打时,田某向酒楼跑去。可见,在面临三人不明侵害程度的伤害时,田某持随身的刀具进行防卫是必要的,且采取的还击行为均是对上前殴打的人捅刺一刀,在第三人又上前殴打时跑走了,表现出田某在还击不法侵害时保持了克制,尽管造成两人重伤的后果也不应认定为防卫过当。
2.“明显”的判断
明显超过的幅度不仅是一个客观事实的问题,还是一个要求“人容易看出”的判断问题。对此,应以社会一般人的认识和判断为标准,并在具体解释时采取有利于防卫人的立场。因此,对同一个案件的防卫行为,在确定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构成防卫过当时,基于有利于防卫人的立场,必须要求不同的司法者观点一致地认为被评价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才属于过当防卫。反之,只要有其中的审判人员持否定看法和意见,就属于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19]同时,为了规范防卫行为限度的评价,统一对防卫行为认定的标准,应加强正当防卫指导案例的作用。通过指导案例的引导,使司法人员在认定时大胆放宽防卫行为的限度的认定标准,敢于认定属于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正当防卫行为,合理把握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界限。
结论
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界限的核心问题就在于认定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可见,我国关于防卫行为限度的规定是质的界限与量的程度的有机统一。在具体认定时,首先应认定防卫行为的必要限度。对此问题,我国理论界历来存在基本相适应说、必需说和相当说的争论。基于基本相适应说和以其为基础的相当说的内在缺陷及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必需说更符合正当防卫的立法目的,认为防卫行为的必要限度应是防卫行为应是最必要的有效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限度。在具体判断时,应立足防卫人的角度设身处地,结合不法侵害人的人数、不法侵害实施的具体环境、手段等因素具体进行判断。其次,超过“必要限度”并不能认定防卫人属于防卫过当,还要防卫行为达到“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程度,才能认定为防卫过当。结合防卫行为对侵害人人身安全可能造成的损害程度进行等级划分,“明显超过”应是至少高出防卫必需限度的一个危险等级以上的行为。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不法侵害伤害程度不明或有进一步伤害风险的案件中,在确定防卫必需限度和“明显超过”标准时应立足有利于防卫人的立场进行认定。在认定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达到“明显”程度时,应以社会一般人的认知为标准,同时,应通过加强正当防卫指导案例的发布,引导司法人员在具体认定时适当放宽对“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过当标准的把握。
注释:
① 如在孟蔚故意伤害案((2016)青01刑初45号)中,被告人孟蔚与朋友在一菜馆饮酒吃饭至凌晨0时30分,当行至某酒吧门外时,因吴某提出进入该酒吧并用手指向该酒吧,坐在酒吧内的被害人朱某误认为二人对其进行辱骂,从酒吧出来后,孟蔚及其朋友吴某与被害人朱某发生争执。后被害人朱某和其朋友朱某等四人即对孟蔚及其朋友吴某进行殴打,被害人彭某在场劝阻,在厮打过程中,因对方人员众多,孟蔚被逼到角落里遭到围殴,且朋友吴某已经被对方打倒在地,孟蔚随即从自己的上衣兜内掏出携带的折叠刀对被害人一方人员进行捅刺,导致朱某等五人被捅伤,其中一人经抢救无效后死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孟蔚在自己人身权利遭到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有权进行正当防卫。但孟蔚持刀正当防卫的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一人死亡、二人重伤、一人轻伤、一人轻微伤的重大损害后果,属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② 2018年12月26日晚11时许,李某与之前相识的女青年邹某一起饮酒后,一同到达邹某的暂住住,二人在室内发生争吵,随后李某被邹某关在门外。李某强行踹门而入,谩骂殴打邹某,引来邻居围观。暂住在楼上的赵宇闻声下楼查看,见李某把邹某摁在墙上并殴打其头部,即上前制止并从背后拉拽李某,致李某倒地。李某起身后欲殴打赵宇,并威胁要叫人“弄死你们”,赵宇随即将李某推到在地,朝李某腹部踩一脚,后又拿起凳子欲砸李某时被劝阻住,后赵宇离开现场。经鉴定,李某腹部横结肠破裂,属重伤二级;邹某面部挫伤,属轻微伤。
③ 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2008)灞刑初字第085号。
④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44号:张那木拉正当防卫案。2016年3月12日早上8时许,张那木拉与其兄张某1及赵某在天津市某鱼塘旁的小屋内闲聊,周某强纠集丛某、张某2、陈某2新四人开车至张那木拉暂住处,在确认张那木拉在屋后,随即返回车内取出事先准备好的两把砍刀,其中,周某强、陈某2新二人各持砍刀一把,丛某、张某2分别从鱼塘边操起铁锹、铁锤再次进入张那木拉暂住处。张某1见状上前将走在最后边的张某2拦截在外屋,二人发生厮打。周某强、陈某2新、丛某进入里屋内,三人共同向屋外拉拽张那木拉,张那木拉向后挣脱。此刻,周某强、陈某2新见张那木拉不肯出屋,持刀砍向张那木拉后脑部,张那木拉随手在茶几上抓起一把尖刀捅刺了陈某2新的胸部,陈某2被捅后退到外屋,随后倒地。其间,丛某持铁锹击打张那木拉后脑处。周某强、丛某见陈某2新倒地后也跑出屋外。张那木拉将尖刀放回原处。此时,其发现张某2仍在屋外与其兄张某1相互厮打,为防止张某1被殴打,其到屋外,随手拿起门口处的铁锹将正挥舞砍刀的周某强打入鱼塘中,周某强爬上岸后张那木拉再次将其打落水中,最终致周某强左尺骨近段粉碎性骨折。此时,张某1已经将张某2手中的铁锤夺下,并将张某2打落鱼塘中。张那木拉随即拨打电话报警并现场等待。最终,陈某2新因单刃锐器刺破心脏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张那木拉属轻微伤;周某强构成轻伤。
⑤ 如在朱凤山故意伤害案中,朱凤山之女于2016年1月向齐某提出离婚并分居后带女儿与朱凤山夫妇同住。齐某因不同意离婚经常到朱凤山家吵闹。5月8日22时许,齐某酒后驾车到朱凤山家,欲从院子一侧小门进入院子未得逞后在大门外叫骂。朱凤山告知齐某其女儿不在家后,齐某仍不肯作罢。朱凤山通过电话请邻居帮忙劝说后,齐某驾车离开。23时许,齐某驾车返回,站在汽车引擎盖上摇晃、攀爬院子大门,欲强行进入,朱凤山持铁叉阻拦后报警。齐某爬上院墙,在墙上用瓦片掷砸朱凤山。朱凤山躲到一边,并从屋内拿出宰羊刀防备。随后齐某跳入院内徒手与朱凤山撕扯,朱凤山刺中齐某胸部一刀,致齐某死亡。
参考文献:
[1] 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 陈兴良.正当防卫如何才能避免沦为僵尸条款:以于欢故意伤害案一审判决为例的刑法教义学分析[J].法学家,2017(5):89-104.
[3] 高铭暄.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157-168,192.
[4] 劳东燕.正当防卫异化的根源与司法裁判的功能[J].中国检察官,2018,40(18):45-48.
[5] 尹子文.防卫过当的实务认定与反思:基于722份刑事判决的分析[J].现代法学,2018,40(1):178-193.
[6] 汪畅.防卫过当判定标准及处罚问题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20.
[7] 汪雪城“. 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判断标准的实证检视、应然转向与本土展开[J].刑法论丛,2019,59(3):163-196.
[8] 邹兵建.正当防卫中“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法教义学研究[J].法学,2018(11):139-153.
[9] 李金明.防卫限度论[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3):9-18.
[10] 张明楷.刑法学[M].第5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11] 高铭暄.刑法肄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2] 劳东燕.防卫过当的认定与结果无价值论的不足[J].中外法学,2015,27(5):1324-1348.
[13] 张宝.防卫限度司法认定的困境与出路[J].法学杂志,2016,37(10):95-101.
[14] 邹兵建.正当防卫中“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法教义学研究[J].法学,2018(11):139-153.
[15] 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6]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第八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17] 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上)[M].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
[18] 陈璇.防卫过当中的罪量要素:兼论“防卫过当民刑二元论”立法模式的法理依据[J].政法论坛,2020(5):13-32.
[19] 张明楷.故意伤害罪司法现状的刑法学分析[J].清华法学,2013(1):6-30.
【责任编辑:许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