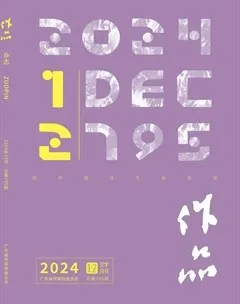越界狂欢的写作探索
广奈的出现是今年的一个惊喜。我想将他命为越界狂欢的写作探索者。
广奈发表在《作品》2024年第4期的六个短篇作品,出现了不同学科领域的混杂对话,却又显得如此圆融合理;他在不断试探小说写作的边界,也将小说中发生“故事”的可能性极大地推广、扩充到不同范畴,他在写实中想象,在科幻语境中沉淀文学史,在游戏中拼凑学理,如此种种都十分之有趣。
《时间的形态》从标题来看,可以是讨论时间物理性状的科普文,但它的确讲述了一个故事。小说开头是“我”父亲在普莱塞河畔的消失,而“我”由此便展开了寻找父亲踪影的一生。“我”创造的“想象·回归”理论,说是建基于“能量守恒定律和唯心主义理论”,其实这二者一个出于科学范畴,一个来自哲学领域,前者作为热力学第一定律是得到了广泛实验论证的,而后者认为意识是世界的本源,先于物质而存在,这就是一个有争议而无法证实的理论了。可以说,这二者在本质上是相悖的。但主人公“我”终其一生实践着自创的这个理论,希望通过想象(唯心)而迎来失踪父亲的回归(能量守恒)。
在科学的认知之下,时间的线性流动是不二的形态,过去发生的无法改变,未来是不可知的,时间也无法逆流。小说中的“我”渐渐明白,“只有超越时间,才能真正与他(父亲)相遇”。
因此,“我”以泛滥的想象极力搜捕父亲留下的点点痕迹,但却不可避免地在时间里变得衰老和萎缩;而随之而来的故事转折,同时也是小说结尾便显得十分精彩了。在一个类似于自我认同的镜像观察中,“我”在河水中看到自己的倒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在这一瞥之后,“我的身体变得无比轻盈”。作者大概在暗示着“我”的回归——在经历了一生的想象和等待之后,在与父亲失踪那天同样的炎夏、同样的普莱赛河边,“我”终于回到了本来的面目,回到了父亲身边,小说也从结尾回到了开头。
为了模糊时间的界限,作者在故事中段安排了一个失眠的女人,她向已经失去父亲多年的“我”提到了自己死去的男人莱昂纳德,她向河中抛下了手中摘下的蓝宝石戒指;而故事的结尾,“褪去陈旧的枷锁”、回到父亲身边的“我”又从河里找到了一枚蓝宝石戒指,父亲口里的“我”恰恰是莱昂纳德。父亲说:“多年以后,你可以把它(蓝宝石戒指)送给你的恋人。”
由上可见,在《时间的形态》中,广奈不仅在科学与哲学之间越界,更在时间的线性形态中越界。现在的蓝宝石戒指可能出现在过去,或者未来;死去/失踪的人会重新归来;衰老的“我”会重返童年,“我”也可以是“他”。这样的结尾固然可以视为一场带有神迹启示的梦境,但我觉得,这篇小说的意义就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能的温情想象。在时间的旷野中,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事物都是卑微如沙尘的,消逝、衰老甚至死亡,是人类对于时间的永恒乡愁(nostalgia),而这个以顺时针行进的时间故事最后用逆流的方式完成,科学做不到的,文学想象做到了,这个结尾多少有点令人感动。
《时间的形态》里已经明显透露出广奈不同于一般小说作者的理科学养(例如能量守恒与傅科摆),《“石头剪刀布”虚构史》中更是以游戏为名,概括了一系列数学理论,例如概率、排列组合等。而《弹射》这篇小说甚至可以说就是一道数学函数题。
“我”是抛物线上的一个点S,爱上了一条名叫莫须有线的曲线(函数)。这是一场不可能发生的爱情故事。首先,S和莫须有线不在同一个象限。根据文章中出现的S坐标点(9,-18)来看,“我”在抛物线x/y轴的第四象限;而莫须有线的数学公式是y=2x+62,这就意味着无论x如何变化,y都只会出现在正值轴的一、二象限。S与莫须有线没有交集。其次,S是一个点,而莫须有线是一个曲线,正如S的好友月如所说:“只有线才可以爱上线,我们都是函数上的点,它不会爱上你的。”
然而,爱情之盲目,即使在函数界也是如此。S是如此固执地爱着莫须有线,乃至于它愿意冒着消失的风险,也要通过弹射去靠近莫须有线,去看见它“完美的弧形”。为了完成“我”的夙愿,另一个爱着“我”的点洛必达提议与S一起弹射,并让S在越过莫须有线的时候借助洛必达的推力原路返回。
在洛必达的自我牺牲之下,S得以穿越它本无法触及的莫须有线,《弹射》由此也变成为一则以数学函数描述不可能的爱、讨论爱与被爱之关系的小说。在这个故事里,广奈的文字首先穿越在自然与科学(数学)之间。梧桐树、森林、河流、鱼群等自然景观出现在函数空间;作者描写这里“一场雨将要到来”“二次函数的天空依旧晴朗”;生活与生命的痕迹在这里俯拾即是,例如“我喜欢捡拾路人丢失的宝物:葡萄、铅笔、向日葵、卡片、松针……我会把它们珍藏起来,有些送给我的朋友,有些埋进土里,等待它们开花”。在这样的描写之下,原本只有简单点和线的数学函数成了鸟语花香的世界。
在这基础上再来细究“弹射”的含义。正常的弹射在数学中大约等于函数曲线上的点随着变量(x,y)的移动,但S与洛必达这不同寻常的弹射,则无异于数学抛物线的计算错误吧?只不过,在小说最后,S越过了莫须有线“盲目的眼睛”,终于回看到爱自己的洛必达,由此,在爱情角逐中非理性的偏执、爱而不得的哀伤以及自我牺牲的悲壮都使得这个算错的“函数题”显得如此深情款款。以文学书写数学的越界写作,让本应该是冷冰冰的数学函数题带上了温暖而伤感的情感基调。
《我们如此热爱飞跃》也是饶有趣味的一篇作品,广奈用文学评论论文/发言稿的形式写小说,有意打破了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与文学研究的界限,他用科幻写作的壳,前瞻式地“回顾”了后瘟疫时代的文学写作,未尝不也是在科幻与历史、文学与评论之间的越界。
凡此种种,我们都能感受到广奈对于文学写作可能性的探索欲,这也是对小说虚构本质的最大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