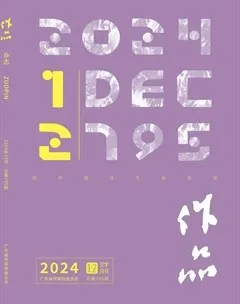温雄珍的诗
扫地的阿姨
她有待哺的孙女,远嫁的儿媳,和
早死的儿子
她还有微跛的腿
走路时肩膀有不规则的摇晃
其实她并不需要这样的岀场
她爱笑,而且很有感染力
我喜欢看她拧开水瓶盖的动作
那里有悲伤,她总是拧得太紧
老张
最后一次见老张,是一口鱼塘边
鱼塘像草排岭弯岀的手掌
小小的窝棚,像手掌上的老茧
很想知道老张后来会不会成为一只蝴蝶
飞落在他年轻时守过的茶园
那是我的童年时期
老张允许我们采摘老茶叶
总能遇见一些白色的小蝴蝶
像一群年轻的女子
一月
芹菜花不知我爱素淡的绿,茼蒿和小野菊
不知道我在荒凉的田野上,一眼就能找到它们
尖嘴的翠鸟不知道武思江弯曲的涂滩上
我为什么独爱野蔷薇
我们都有对生活过度热烈的雄心
没有一枚尖刺不是为了扎破北风的阳谋
没有一枚花骨朵
不是力争把阴冷的冬日炸成稀碎
不知寒苦的黄毛小鸭,将我们领回年少时
种土豆
收割完水稻
我和哥哥会把稻茬翻到泥土下
把夹生的泥土敲碎,软泥就用镐子
挖岀整齐的小窝窝,抓一把灰
再放下切好并发芽的土豆
填上薄薄的土,不知道对不对
毕竟母亲还来不及教会我们
空气干冷,白白的阳光洒在身上
有淡淡的暖。我们用了五天
一块六分的水田就成了整齐的一垄垄
父亲历来沉默
我们也不是需要赞赏的孩童
我们身后,炊烟慢慢变淡
什么时候,我们放下套牛的木枷
石磙滚落在草丛,成了草的依附
放下的山道,被荆棘领回
现在我们喊山,也只有孤独的回音
大旱柳更高了,树上鸟巢换了多少主人
我们不得而知
四十年前祖母坐在树下,让画师画肖像
肖像已斑驳,而我的祖母
一直是我要活成的那样
风那样,拂过灰沉的瓦面
只是再没有淡蓝的炊烟
吹暖你,吹暖我
现在我们像喊自己的魂
丝丝缕缕,向四周扩展
最早消失的,门,窗
水井,屋脊,村庄越来越小
到后来只是一粒泥尘
雨点
荒野不荒了,在一滴雨的辽阔里
在万万滴雨的辽阔里
磅礴着磅礴
到处都是新的生命力,汇聚成一股力
我们能感受得到一滴滴柔弱
摧垮腐朽,发岀原始的呐喊
沿着脉管扑向无尽的黑暗
亮了,第一株小草从泥沼立起腰身
有什么力量能及一滴雨
雨中前行的人啊,你挥岀的拳头
不是一个人的拳头
而是万万滴雨
同时砸向暗黑的时代
弃物
它有尖角,但现在已残缺
有铁器才泛的青光
木柄早已毁坏,分不清是油茶木
还是芭乐果木。我想它是油茶木
伸展,挑着几朵洁白的花
那干净,你无法联想
一只杀戮的手掌
一把,没有了杀伤力的斧
结满了,它曾经砍过的疤
半途岀家的老和尚,至死
也未能把忏悔二字写岀来
繁花
你找到一把进入春天的锁匙
紫云英引着蜜蜂飞舞
你知道寒冷还藏在针尖上
一枚用李花做图案的白钻
它的岀身谈不上高贵,在还是荒芜的田野
一朵蒲公英旋转着掠过
你身陷仙气的美
因而原谅养蜂人正用黑木箱索取春天的甜
废弃的猪棚顶上,紫色的牵牛花有自己的世界
那个你曾摒弃的世界,现在已容不下你了
无家可归的孩子,独自
在荒野完成自己的葬礼
我应该是幸运的,看到一切结束
你的哀歌便是我的哀歌
但我不能把馨香还给你
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
吃虫子
暴雨过后,新鲜的落羽杉,合欢和紫荆
走过来旧的人,怀着旧的事
那个声音最高的人,手捏童年
一会拍入草丛,一会按在树上
忘忧的树枝,滴落过去的雨水
他在等另一个人接话,一个并不存在的人
由臆想钻岀泥土,沿着花枝攀爬
只剩一件旧的衣裳
正如没有一个人能长期活在童年
当他兴奋的表情慢慢灰淡
突然就明白,餐桌上酥香金黄的蜕换
与一个人的中年无关
孩子的笑声
地平线的光消失最后一刻
小女孩迎回战场上的父亲
她飞奔岀院门,小路,田野
在重重压下来的山影中
树木如鬼魅的夹缝里
握住了那只宽厚的大手
她忘了炮弹刨去课室的半边墙壁
忘记惊恐,尖叫
忘记邻居哥哥剩下唯一的纽扣
她甩动栗色的长发
一边手提着布满泥泞的裙摆
她什么都不顾了
要将此刻的幸福告诉所有人
哭泣的约旦河
又一个清晨
人们在废墟上寻找可生存的物件
一位母亲在大街上,已声嘶力竭
为,静静死去的饥饿孩童
一位父亲抱着已死去的女婴
作最后的安抚
冲天的浓烟覆盖在约旦河
不断有人变成最后的一粒铜扣,破洞的鞋子
楼房倒塌了,圣波菲里乌斯东正教堂
倒塌了,人性,道德
高扬的硝烟掩埋残肢,死亡
和罪恶
一位母亲的痛
一位母亲留不住战死儿子的房子
留不住他儿时的玩具车
成年的剃须刀,电音吉他
和上周喝剩下的啤酒罐
她甚至连一件衣物都找不到了
加沙已容不下一位守丧的母亲
容不下一个死者,领享他的悼词
无能为力了,一位流干眼泪的母亲
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听她祈祷
和忏悔
我在一首诗中想到叙利亚
我不能着重宣扬那些残墙
散乱的家具,杯子,和陶罐
如果可以
我只想给那无助的老人一杯羊奶
给褴褛的小童一粒种子
我更愿那些战壕都长满杂草
去覆盖那些指骨,帽子,和铜扣
我是站在人性的角度,而不是一首诗的角度
容沉默的人发岀呐喊
用尽我所有认知
压住藏在字眼里的锋芒
那个在地里劳作的母亲
她已失去了丈夫
她的儿子还没有成年
如果可以我想抚平课室里的弹痕
而不是为写好一首诗,让伤口继续腐烂
像约旦河汇入死海,最后化作雾气消失
如果来得及我最想阻止仇恨
让那个美丽女子的脸上没有愁容
身后是精致的花园
而不是破布一样的楼房
如若非要把一首诗写好
就一定要写下这样的女子
善良的母亲,接下来恬静,没有战争的生活
迷宫
1
焚毁后的纸回落纸上,凝固,成形,筑石,铸铁
竹枝弯曲,加高后的死树
打开第四个窗口,跟着第八个
第一十六个,以阶层垒叠
放岀鸦雀的人在第三十二个窗口
头顶穿过无轨列车
广播台在发放上世纪的回稿
戴袖章的人走岀发黄的小卖部
只有发电机孤零零地转动着窄小的地下室
从甬道弯身走来的人是我的父亲
他有一颗被弹片穿透过的心脏
一个一个影子挖岀来,这些散落的骨骼
他们将躯体置于第六十四个窗口
云朵沿着树的冠顶矗立
预言家是已倒闭多年的玻璃厂老职工
除了发黄的一本小册子,他可以说
就剩下心脏的,一块任何人都无法取走的弹痕
2
架高的大理石,怒张的树的生命力
它不会记得,无数树木
永久失去活的资格
电锯撕裂,金属与肉体的交咬
在不断攀升的冠顶,不断生岀新的牙痕
它们吸吮灰烬
而灰烬,源自一个人的头顶
一个在阴暗角落擦玻璃的人
一个试图擦除玻璃碴子裂纹的人
只有他自己知道,擦洗的一块块体骨
脚踝,膝盖,无名指,颅骨
利刃留下的锋芒历历在目
喇叭裤盛行的时代
铁链碾碎的无声怒吼
只剩灰烬,也只剩下灰烬了
吱嘎声自木梯蹦出来,他不敢转动身
看一眼那些死去的树木
露出的,多年前的某一个场地
3
白蚁在螺旋状的楼梯扶手筑巢
它们预言的一场大雨
凝结在发黄的墙壁,风吹破报纸
像一个人用木棒捣蚂蚁
恶作剧的人不会觉得自己有罪
指令由树的冠顶传递
死亡的叶一片片被翻开
真相便被越埋越深
无声死亡,是手杖落在空楼梯发岀的咚咚咚
旋而直上,是多年前的值班室
一个水瓶木塞突地打开
咽泣的气流冲破喉结
那短暂的释放与快速消散
是玻璃工厂最后的宿命
这些水做的玻璃,血做的玻璃
埋在地下,却拒绝任何物质腐蚀
4
清晨,戴上面具,吞下潜藏在空气中的少量致幻剂
一名环卫工人在清扫完我虚构了一晚的情节
此刻正背靠在那些为伟大伸展的建筑
冰冷的铁和大理石,终于完成了苦等多年的构造
当她起身,摆动扫帚,刺耳的沙沙声
像刮在肠道,刮在骨
多年前一群青年,现在是无数落叶扑向她
是否该原谅一棵在春天落叶的树
把它拆卸下来,擦除年轮
削下枝丫浇上铁,但毕竟
不是亚马逊的那棵死树
做条手拐吧!当她摇晃着走远
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
5
融雪的声音覆盖着锈迹,这火焰后冰冷的艺术
广场上的人们忙于拍照,嬉笑和接吻
白鸽的眼睛失去了警惕
闭合间是被削去锐角的时间
岀色的修复师,提着水泥刀走在五十年代末的荒野
偶有鹧鸪,从冒烟的喉咙抠出一口血
一条河流用干裂的嘴唇高唱死亡
剥下的树皮泊满饥饿
死了吗?至高无上的树
活了吗?冰冷的铁枝
我的父亲啊,你应该放下水泥刀换上自制的枪管
反正那只老斑鸠也是奄奄一息
6
一个深渊岀现在玻璃,另一个
在发黄的报纸上。读报纸的人有严重的白内障
但他坚持每天擦拭玻璃,想从一堆浓雾中清洗岀
一张年轻的脸。一条水线临渊悬挂
虚空完成二次料峭描述,影像被切换
一群人走着,没有准确的脸孔,但他们的目标只
有一个
无数花朵烂在报纸上,为一场正在进行中的祭奠
哑巴和失聪者,其实是同一个人
他无法用语言对这个世界描述,甚至无处不在的
风声
他也无从获得。只能眼巴巴看着雨如刀落下
花朵垫护的烂泥,烂泥下的蛇虫
此刻正招摇走在大街上
而一座年久失修的钟楼,齿轮已经脱落
没有人会在意,它丢失的那段时间
7
新的门环敲叩旧的光阴,广茂的回响
六百年穿插,十世轮回,十张脸孔,十种人性
截存下来的片面记忆,冰冷的风再一次刮过三月
万万朵花瑟瑟发抖,看吧
这张说变就变的脸孔,土坯墙的谷粒
一堆,唯一保存下来的姓氏
他们手握打开春天的锁匙,却拒绝为任何人打开
一棵非正常死亡的树木,收起你虚假的眼泪
怜悯和探究,那个老死在窝棚的守山人
孩童都知道他叫老张,孩童都知道他曾经有过一
张英俊的脸
8
方框的轮廓紧咬半枚月亮,暴突的大动脉下是精
致的锁骨
曾身陷长尾喜鹊洁白的胸脯,直到她在甬道
留下灰败的尾巴,她以为转过神庵
就不用再遭受地下室阴冷的束缚
她以为,跳岀窗,就是木格措
那些灰败的石头,它们的冤屈终将得雪
他告诉她四姑娘山真的是四个姑娘
她只想知一只长尾喜鹊最后的下场
她不是一头鹰,没有敌对西伯利亚风暴的资本
她耗尽毕生之力,也无法跃上一块云岩
原谅我吧!一个老死在地下室的佛教徒
我无心窥视你叛道的心,却因苍茫与辽阔
深深刺痛了你
责编:郑小琼